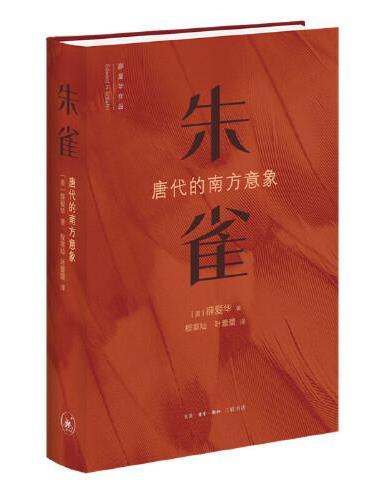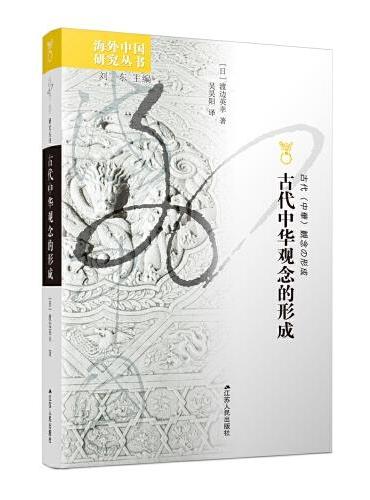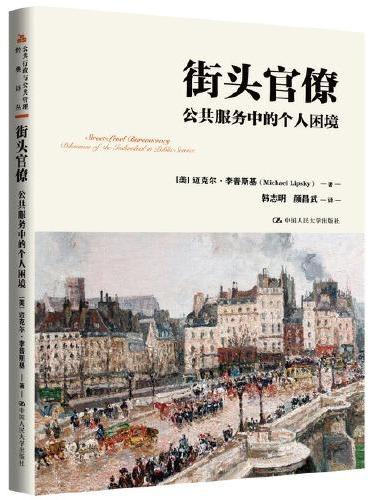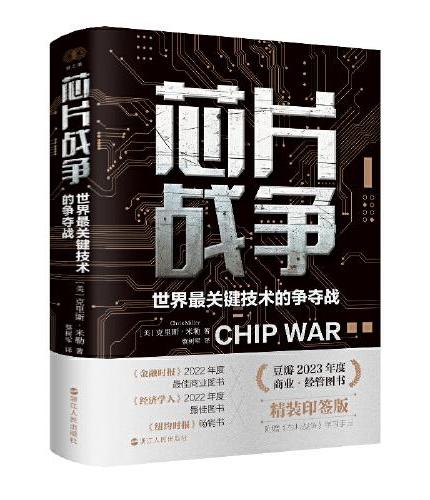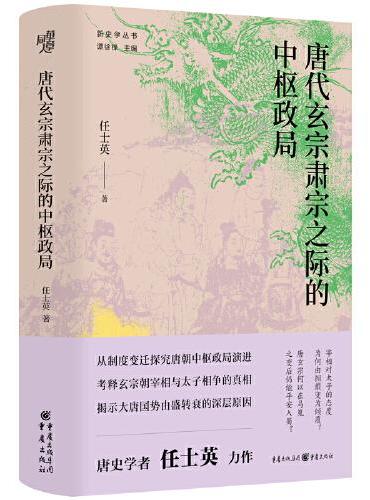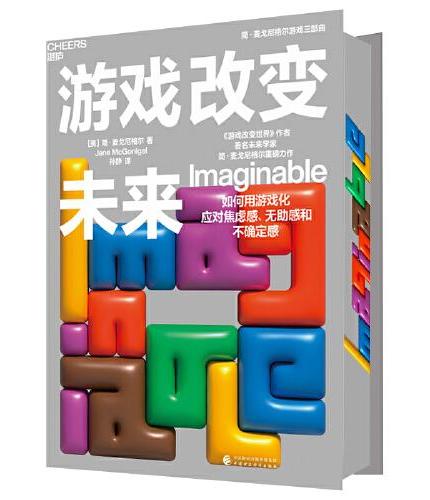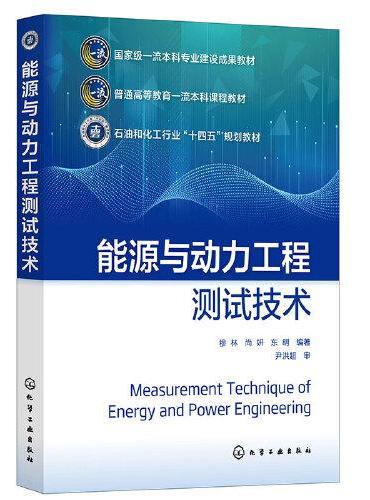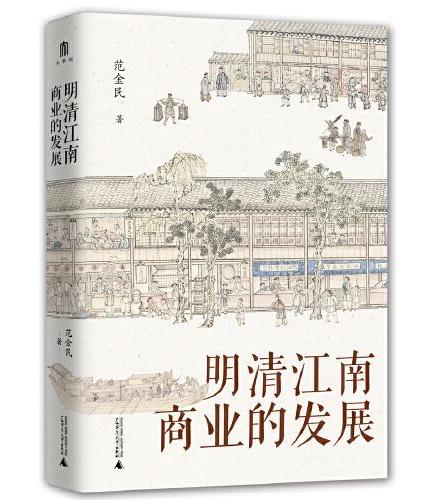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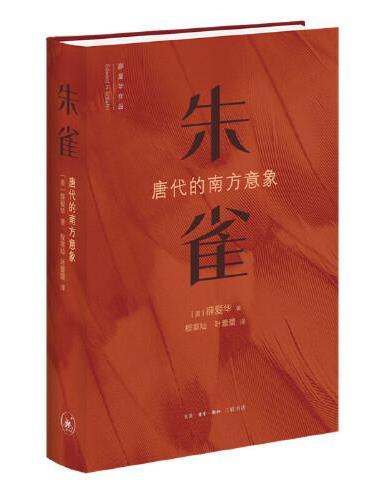
《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向
》
售價:HK$
1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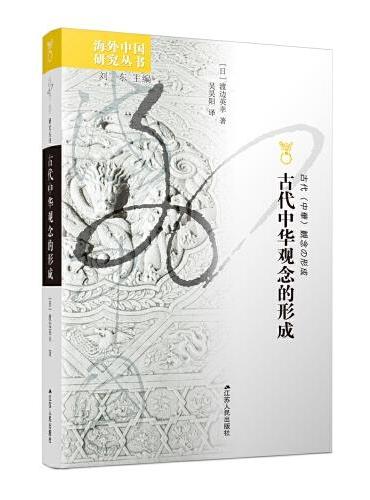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
》
售價:HK$
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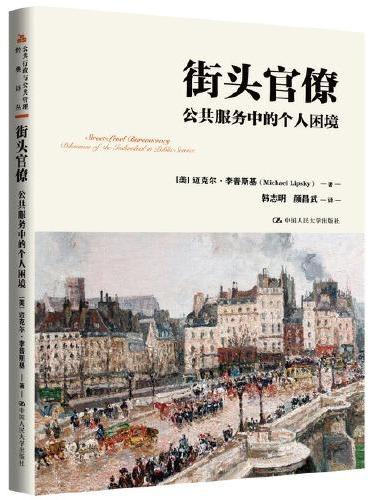
《
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中的个人困境(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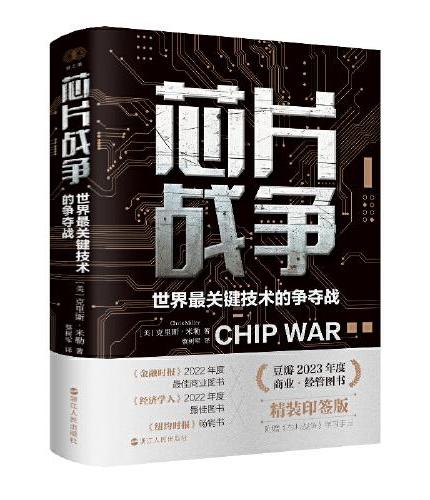
《
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
》
售價:HK$
1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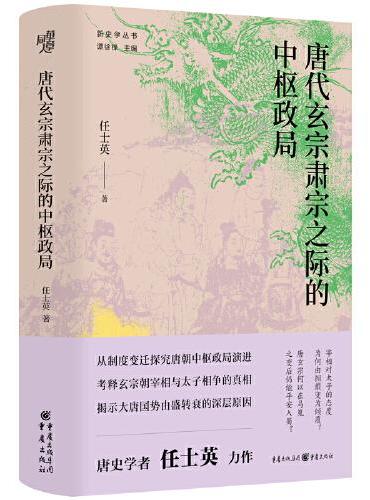
《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
售價:HK$
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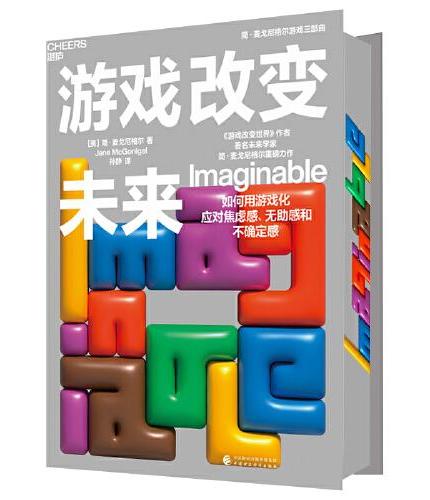
《
游戏改变未来
》
售價:HK$
1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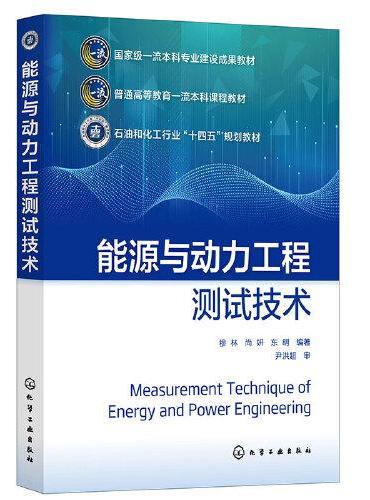
《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穆林)
》
售價:HK$
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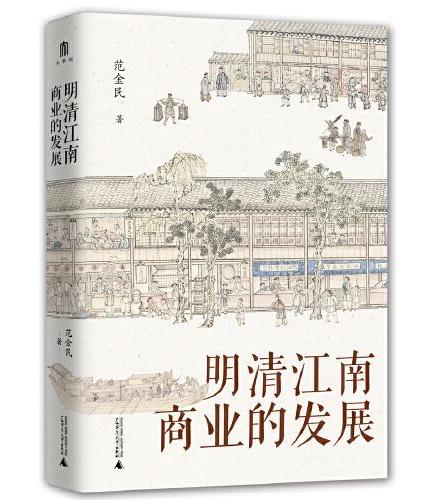
《
大学问·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
售價:HK$
106.8
|
| 編輯推薦: |
|
《奈良往东的来信》故事可读性强,文笔优美,内容治愈,充满正能量。不同于传统的爱情或经典网络小说的套路,以亲情、友情、家庭为主要对象,重拾生活中被我们忽略且理所当然接受的情感。
|
| 內容簡介: |
|
《奈良往东的来信》是一部治愈系的长篇小说。自幼年起便被迫漂泊在外的青年阿拓某天突然接到来自日本的家书,邀他回去参加继父葬礼。在几番犹豫下,他拖着已被医生诊断无药可救的身体回到了日本家中。至此,他踏上了一段寻找的旅程——寻找自己出生的意义、母亲抛下他自杀的原因。因为幼年时一直过着提心吊胆,寄人篱下、辗转多个国家的生活,阿拓的心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他悲观、厌世、厌食,对人生已无所恋,却在和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之子直树、浩矢重逢后,因为感受到浓浓的,他一直很渴望的亲情,而对往事释怀。
|
| 關於作者: |
|
木穆,目前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研究生,主修电影研究。曾获“99杯”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已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于报刊。“90后”文学界代表人物榜上有名(网络百科)。《奈良往东的来信》是她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
| 目錄:
|
第一章像摩根·弗里曼的老人和穿英式短裤的西装男孩1
第二章奈良往东的来信和饥肠辘辘的救济所21
第三章不能马虎的早餐和讲关西腔的日本人53
第四章尴尬的英文手册和居民区里的电影事务所79
第五章猫和不认识的少年和移民者的房屋115
第六章长刺的大魔王和像白天一样的黑夜149
第七章瘦骨嶙峋的事物和井底的毛驴183
第八章半夜里的妖怪和通风报信的联络员207
第九章撅着屁股的鸵鸟和偷自行车的人227
第十章注视过去的奇怪大人和鱼形花纹的短册247
第十一章临时搭建的空间站和烹调时的意图265
第十二章失去灰姑娘的小矮人和不准点菜的定食屋287
第十三章酋长的水槽和存在一日的密码307
第十四章『今日休整』的剧院和追捕野兔的白熊337
|
| 內容試閱:
|
像摩根·弗里曼的老人和穿英式短裤的西装男孩
第一章
眼前的老人看上去已经超过60岁,身着格子状的深灰色粗花呢西装,斜挎着撒哈拉黄色的皮质小包,有些拘谨地把头稍稍低下看着我。满头银色的短发沿着不同方向从他黝黑的皮肤里蹿将出来,淡棕色的斑点在他颧骨下方十分明显。他的眼睛不大,褐色的瞳仁在天生的黑皮肤里不太显眼,却不知是因为精神气十足的关系还是外面停机坪上的灯光已透过小窗渗透进来而使他的眼睛看起来闪闪发光。我想起了摩根·弗里曼,那个老喜欢在电影中扮演美国总统的黑人。尽管已在美国生活很久,至今我仍无法得心应手分辨黑人长相,或许在他们看来像我一样的亚洲人也是一样。我注视着他,思忖他打算多久开口说话,看他的样子是有话要说的。他用双手掌抚了抚衣服前襟,本已经平整的西装下摆经他一弄显得仿佛易碎起来,稍一折角就会生生掰下一块布片。
“我坐在这里不打紧吧?”他果然开口,他的手又强迫性地抚了抚衣角:“本来是在正中间的位置,学生娃娃定要同我换,说是不小心同同伴的座位分开,无论如何也想坐在一起。且还向我保证自己的位置紧邻窗边,是为旅行的最佳选择。”
“也许不是那么靠近,他说谎了吧?”我看了眼老人眼睛的方向,身着横条纹T恤衫的年轻人正同邻座打闹。我正坐在年轻人所说的紧邻窗边的位置把自己的黑色西装外套从身上脱下折好。但无疑出错的并不是我,我的机票上好端端印着是靠窗的座位。
“不碍事不碍事,在走廊一侧倒也方便。”他说着坐下来,把小包取下放在膝盖上。我继续翻着手上的杂志,里面有几页详细地介绍着大阪的住宿和交通状况。
“说来好笑,这么大岁数了却是第一次坐飞机。一开始连登机口都找错了呢,一直等在去迪拜的飞机门口。”老人盼着交谈般把头转向我的方向。第一次坐飞机的人好像都觉得整整这一天都被人品头论脚——应该几点到机场,在哪里办理行李托运,去哪个登机口,座椅该怎么调节,如何招呼坐在旁边的人或是怎么向空中小姐要阿司匹林——环节诸多的过程难免让人萌生如果一环扣错会给当天的行程带来多大的阻塞。实际上是多虑了,毕竟飞机只是冰冷巨大的机械器物,不会对它肚子里盛满的物体进行逐个打分,以此评断谁是能到达目的地的,而谁又不能。
“如果起飞时觉得难受的话,请不必客气地使用这个。”我拿出随身的苹果味口香糖递给老人。
“真是不好意思,我就不客气了。”他拿出一片打开,将糖片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您是回国探亲吗?还是……?”他端详着我的脸,犹豫着问道。任谁都会这么想的吧?毕竟我是黄色面孔黑头发的人,怎么看都像是要回到太平洋上的小岛,以前的生活也该是吃着白米饭且在新年时有着烦琐的礼节和仪式。
“不是的,”我边说边解开衬衣最上方的扣子,飞机上的冷气好像没怎么运转一样,“或许算探亲吧,但已经是美国公民,回国恐怕算不上。”
“原来是这样啊。感觉上以为您会是日本人,彬彬有礼的。”
“被人这样说过,或许是因为长相的关系,觉得头脑好,也懂礼貌。就像贴了标记一样。”
“实际上不是吗?”
“倒不至于。”
“对吧?给与您这副相貌的神灵定有它的考虑,在我看来就像在我的人种里依然多少带有先祖的习惯,您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副面孔背后的基因吧。”
“是吗?”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鼻梁不高,嘴唇也不算厚,皮肤嘛,多少有点干燥,但也算细腻,是同周围的欧美人有本质的区别。
接下来好一段时间里老人都没有再说话。他歪着头跟着再度拿起杂志的我一同阅读起来。书上的介绍内容有一部分是英文,有一部分却是日文。
“可看得懂日文?”老人问道。
“懂一些。小时候在日本生活过几年,大学又选修过东亚研究。跟着上过一学期的日语课。”我盯着书中大阪湾的图片,没有抬头。
“很是便利呀,不像我老头子一个人,不会说这样复杂的语言,日文自然也不识一个,想必又要招惹儿子厌烦了。”说罢,他自嘲地笑了笑。
“您是去探望儿子的吗?他在那里工作?”
“在一家做电脑的公司上班,前几年公司调职过去的。本来是可以留在巴尔的摩,但他一意孤行想出远门。偏要粗着脖子同我争论,好不容易回家吃一次晚餐,两人就这么针锋相对地浪费了。”他无奈地摇摇头,“还是因为他母亲过于宠爱他,凡事都顺着他,到现在,他想做什么时,势必不会再听旁人劝说。好在终于要结婚了,上个月发来的请柬,说无论如何让我去参加。”
“您太太不和您一同去吗?”
“在儿子上高中时就去世了,一直都是一个人来着。”
“我很抱歉。”
“没关系的,能有人说起也算是不错的纪念。我还没老到糊涂得记不起的程度,可喜可贺啊。”
“您儿子一定很高兴。”
“是啊。您呢?您到日本去做什么?”
“我吗?”我若有所思地用右手挠了挠头。老人转向过道那侧,向站在尽头的空中小姐招手示意。穿着蓝色套装的空中小姐注意到他,款款走了过来。蓝色衣裙在走动时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他问道。空中小姐点点头,随即走开。不一会儿, 空中小姐端着一个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又返回来,老人接过水,冲她感激地一笑。在这过程中我什么话也没说,静静地看着老人喝水。
老人小口小口地喝了大半杯水,喝水的样子让我想起大学时一时兴起养在宿舍里的热带鱼。热带鱼的鱼缸是从生物实验室里搬回来的,饲料也是从生物系的朋友那里弄来的小型水蚤,小鱼长得很快。
“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口渴,身体的各个器官看来都真的到极限了。”老人把水杯拿在手上,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
“还是把乘务员叫过来的好,飞机起飞前最好不要用小桌子。”我指指站在走道尽头的空中小姐。飞机还没有起飞,我看看左手腕上的表,已经超过一点点预定起飞的时间。
空中小姐过来收走了杯子。五分钟以后,一家三口的亚洲人出现在最前排的座椅处。看似父亲的男人背着一个红灰相间的旅行背包,正在不停地向乘客们鞠躬道歉,而旁边的女人抱着只有三岁左右的儿子也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怀中的孩子倒是什么也不知道,正用手拽着女人绾到耳后的头发。因为坐在靠近机尾的位置,我并不能很完整地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不过,看来就是因为这一家人迟到,飞机稍稍延迟了出发。
“那么,要起飞了。”老人有些期待地摆弄好安全带。老人似乎已经忘记自己刚才提出的问题。
飞机上升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一股力量将我牢牢往后压去。至今为止我搭乘过很多次飞机,大部分时候是直升机。螺旋桨刮起巨大的、人为的风,我埋着头紧跟着前面的人蹲下身小心翼翼前行。直升机总是直直地起飞又直直降落,每到降落时地面会出现水一样的旋涡涟漪,在沙尘天时尤为明显。涟漪一圈圈荡开,我感觉自己连同整个直升机都将被涟漪吞噬。我细胞里的每一个分子、记忆、至今为止交过的女友、最喜欢的季节被沙群挤碎又重新整合,粗糙又痛苦的部分变得光洁圆滑,幸福又快乐的部分却怎么也找不见踪影。想必是此过程中混进普通的沙群,一起流向没有止境的山脊了。如今我固执地乘上完全不同的飞机——原理和起飞方法都不一样——飞机倾斜地穿插进漆黑的夜空,速度均匀。它明明爬升出新的高度,我却感觉自己慢慢下沉。
“每次去旅行都会忘了本来的目的。你看,比如说上次我去看自由女神像,心里想着要由衷地领略崇高的精神,要敬佩地瞻仰。可是当我真的到了那里,我最关注的是哪艘游轮坐起来更为舒适、视野更好;见到水兴奋不已,甚至想捧上一捧带回家;还有同其他游客攀比似的拍照。最后的结果是拿回一堆连焦都没对好的杂乱照片,上面很少看见人影。如果有,也是别人,从没照到自己。”女孩的声音在耳边低语,“但是回家就不一样。从没有偏离过目的。”
我没有动作,但耳朵却在灵敏地捕捉风一般倏忽而过的声音。
“您需要些什么呢?”另一个比刚才的女孩更成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全神贯注,“我是说消夜。”空中小姐正站在老人和我面前,两手交叉摆在身前,背微微躬起。老人也转过头看着她。
“啊,不需要的,谢谢。”我礼貌地回答。
“真的不要吗?距离晚餐已经很久了。”空中小姐走后老人转过来问我,“我倒是习惯睡前吃点东西。听说做的梦也会变得美味。”
我笑了笑。老人接着说:“到了大阪以后就能品尝到日本美食了吧?儿子常常提起自己在那边大饱口福的事。太太也是日本人,想必果真体会到了地道的东西。”
“我这个人啊,是这样觉得,如果出发到一个新目的地,感觉人生无论几次都能重新开始。”他已经拿到空中小姐送过来的火鸡肉三明治,正在打开外面包的锡纸,“虽然已经行将就木,却总认为一旦到达另一个地方,尝到另一种食物,同另一种人谈起另一个话题,问候方式和语言习惯都随之更新,会让我像隔日将去郊游的小孩般喜悦不已。”
我听着老人的话,看他把三明治大口大口地吃掉。中途他被一大块鸡肉噎住,他慌忙地拿起配送的橘子汁,呼噜呼噜地喝了下去。我突然觉得此时满脸皱纹的老人比起我更像是兴致勃勃的年轻人,用全部力量换取愉悦的人生。我陷进飞机座椅里,看见自己年轻的一部分从体内脱离,变成透明的媒介物质飘在空中。四周的人呼吸时就吸进去一点。他们每吸进去一点,我就更加衰老一些。最后我变成一具空壳,用假意的年轻外貌蒙骗人心。
夜沉得重重压向整个机舱。不久前还存在的人声被厚厚的夜幕掩盖住。身旁的老人业已熟睡,均匀的呼吸声在我耳边飘忽不定地游荡。我歪过头看见老人微微偏向过道、在飞机平稳的气流中轻轻摇晃的脑袋。虽看不清脸,但想必是睡得十分安宁。我转回自己座位的方向,行李架的底座静静地守在微弱的黑暗间。老人细小的鼻息声从左侧传来,我拉了拉覆盖在自己身上的毯子,柔软的,还带着自己的体温,手感很像刚刚出炉的鸡蛋糕,总觉得握住边缘的手掌都沾满甜腻。
但就是无法入睡。怎样都无法入睡。倒不至于因为换了地方而无法入睡,还没娇气到那种地步;生平也算辗转过许多地方,木质床板也好,软和的床垫也好,就连锈迹斑斑的黄铜支架床——一翻身就会引起“咯吱咯吱”的呻吟声——和硬邦邦、凉冰冰的睡袋也是体会过。周遭安静得不像话,除了偶尔传来一两声咳嗽和起身去厕所的走动以外,这里是天然培养睡意的大作坊。梦从这里被等候着的睡神收割,接着挽成绵密的细丝线,织成睡神五色的彩衣。而也正是这安静惊扰了我的睡眠。
再没有飞机不间断起飞降落的轰鸣,也没有BP机每隔两三小时的紧急呼叫,因为疼痛而竭尽全力的怒吼呻吟也都不见,这里平静得像是世间从未有过暴力。但是暴力确实存在。我曾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的愤怒中整夜清醒,身穿灰色的训练衫坐在休息室里打着已经过时的电子游戏。画面上肌肉纠结的大块头连续用膝盖撞击对手的下巴,对手喷出像素一样的血块,然后游戏结束。值班的医生端着从餐厅拿来的消夜坐在沙发上看着我玩,末了总会拍拍我的肩膀,象征性地劝我早点休息。
我望向窗外黏稠的黑色夜空。风的痕迹在墨色的背景里被消除。我正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前行,却意外地感受不到任何阻力。铁制的机器外壳让我产生安全的错觉,好像我的旅途无懈可击。实际上我忘记自己正身在几万米以上的高空,底下除了薄薄的铁皮,只有连一块小石头都承载不起的空气。
女孩正是坐在这样浓郁的夜色里。两脚垂在机翼边缘,随着忽高忽低的星星们不规则地摆动。她上身穿着作业时的偏灰色的橄榄绿的短袖衫,下身还是迷彩长裤,战斗帽的帽檐微微偏离正中,脚上的军靴鞋带散开,看起来颇为随意。她用手抚摸着怀里的小猫,猫是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随处可见的品种。猫看起来不过一岁左右,尾巴却已粗得堪比粗麻绳。此时我才算看见风的痕迹。它们削过她和猫不规则的边缘——不是传统意义上去掉某一部分的“削”,而是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颜色就会变淡一点。猫从女孩手里挣脱,沿着机翼落落大方地跑来跑去,丝毫不担心底下并不是陆地。后来猫跑到我正往外看的窗口处,也不知怎么就坐在同窗口齐平的高度。它“呜噜呜噜”地从胸腔里发出沉闷的低吼,时而抬起前爪用粉色的小舌头舔舐上面的绒毛。女孩还坐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握住机翼边缘,偏过头看着猫,和我。
“天要亮了。”她这么对我说。也可能是对猫说。也可能是对任何一个我看不见的物体说。毕竟这里是天空之上,我并不清楚超越人类生存高度的地方会有什么有违常规的事情。所以我从不抵赖天空之城的存在,也不否认似人类的生物长着翅膀。
但我还是朝她点点头。她对我笑了。是对我笑。因为她正看着我。不是猫,不是其他人。她的目光如炬,我能感受到它们覆盖在我身体表面的温度。猫转过身又跑向她。她抱住它,站起身。风的痕迹更加明显。她的颜色淡得要同周围墨蓝的天空融为一体。
“再见。”她说。
再见。我闭上眼睛。恍惚间听见她一跃而下时同空气碰撞的轻响。
这是我第一次做梦,在我从军队退伍以后。在短暂的飞机上的睡眠中,我梦见自己竟变成一个老人。走路的样子和现在并无二致,相反还要精神许多。头发被剪得很短,黑白灰糅成一团,像无数人踩过的混乱不堪的草地。我还穿着那件在军队时的灰色训练衫和黑色的短裤,跑步的时候只要被车光一照,军队的字样就会反射出白光。牙齿一颗没少,但也说不定是假牙,并没走近去看,远远对着老去的自己点了点头算是招呼。健康得很哟。我这样想着。年老的自己朝着年轻的自己缓缓走过来,他走得很慢,很用心,似乎在数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走了很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走了很久都没有缩短我们的间隔。随后在他身边渐渐出现其他的人,像嘉年华的游行队伍一般。他们穿着各色的服装,有人演奏着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应该是很多人,也许是一个交响乐团也说不定。演奏风格我从未听过——自认为听过许多版本,现在所听却全然叫不出名。他们像墨团般环绕在自己周围,花花绿绿,配上音乐甚为壮观。可是无一例外地都看不清脸,不知道谁与我为伍,也不知道我同谁为善。他们就这样朝着我走来,年老的我也许是笑着,但笑着并不能揭示问题——我从小就只会笑,傻笑,苦笑,大笑,抿嘴笑,笑是我唯一的天赋,并不是感受到愉快或欣喜,只是不知道如何同别人打交道罢了,于是一概用笑掩饰,别人自无可挑剔。
后来一个蓝色的人翻转着跃身跳上年老的我的肩膀,然后另一个绿人跳上蓝人的肩膀,接着红人、白人、紫人、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像是马戏团里表演的叠罗汉一样,越垒越高地自我肩膀处延伸到云端遮住的天空。俨然巨大又绚丽的墓碑,年老的我被埋在最最底端,却依然步伐坚定地用同样的速度朝我走来。白天换作黑夜,黑夜替代白天,他从日走向夜,走向我。
梦到这里结束。我醒来时没有流汗,没有心悸,没有任何噩梦留下的后遗症,因为说到底我也不懂我应该怎样感受这样的梦,就像我对已经发生过的很多事都失去了正确的感知能力。我无法评断自己。能体会早晨5点肚子的饥饿感,半梦半醒间似乎听到厨房有人问要不要烤吐司,接着扑鼻的香气绕过房间几道弯准确钻到蜷成一团的我的鼻子里,那时才算清醒过来。套上扔在床脚的连帽衣去厨房,确定空无一人,碗碟还是昨晚丢弃在水池的形状。我无法得知我在期待什么,也无法下定义自己是不是患了心理疾病。唯一清楚的是记忆犹新的饥饿感,生理机能是我仅存的、正确的感知。我靠器官、肢体、大脑运作如常,心脏除去提供血液循环和“扑扑”跳动的物理作用,再不存在感性认知里的所思所想。有一处针尖般的寒意梗在我心脏正中的血管,它在逐渐扩大,大到水煮蛋的大小,无味又顺滑地拽住颤动的神经纤维。现在它保持住这种冻住的姿态,将来势必还将扩展下去,说不定会连我整个人都冻成博物馆展出的冰雕也有可能,下面摆放好标签——“廉价处理”。
窗外依旧维持着女孩道别时的深墨蓝色。梦中时间无论多漫长也只化为人间一瞬,倒也解释为何我会老去并在游行队伍中数日行走。梦绝不现实,不仅是时间上的考虑,我同时并不认同有人提起过梦的预知。真正的未来从不曾在梦中出现,那些经过装点、歪曲,早已变了模样的所谓“今夜所见未来”不过是自我安慰时的臆想。梦里的过去也不再是过去。偏差颇大的事实和再不存在的人物时而客串“过去的梦”的演出。我躺在床上,眼睛闭上却看着梦里进进出出的再不可能出现的人向我招呼,问候近来情况,陌生一些的同我握手,亲密一些的同我拥抱。我曾混淆季节,在喀布尔1降下几厘米厚松糕般的白雪中同朋友穿着夏威夷衬衣坐在木制走廊上的野餐桌上抽大小王。这些梦中出现的好似发生过的过去礼貌地敲开我的大脑里管理记忆的门,彬彬有礼的、不带有好奇窥视房间里的目光,吐字清晰地说:“日子煞是艰辛,先生至少让他在梦里认为回到过去罢。”管理记忆的细胞先生也粗心不已,认为人和事和地点上大致吻合便批准这似是而非的奇妙体验。
所以人以为梦便是现实的延伸,有时甚至是现实,有时同是未来。
我转头凝视窗外,云层厚重。是不是云都不太清楚。在那样的视野情况下唯一明白的是坐在机舱里的自身。好歹有些微光线正一笔一画地描出自己的轮廓,紧接着老人的轮廓,再是座椅奇特的弯曲和柔软的颜色,最后是由近及远的乘客和空中小姐。他们看不见光线,他们在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我伸出左手手掌,低下头仔细观摩手中的纹路。倘若不是这光线,想必这些像被谁随意涂画般的痕迹不会清晰得如此毕现,甚至消失了也未尝不可,说不定这个世界是因为有光才得以存在,不然身陷混沌黑暗中的我们何以知晓自身形状和行为。道德、伦理、哲学、艺术,如此诸多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物都不会有发展空间,因为我们连自身是否真实存在都未可知,只是像是黑暗中一团独立的思维,一个想法,一缕灵魂。看不见的肉体就像从未存在,每每陷入黑暗我就会这样想。人类,也许那时候不会被叫作“人类”,会发起一场确认躯体容器的革命,往他人身上泼白色颜料,说到黑,白正好是其反义。但未曾考虑在浓郁的黑暗中尚不存在光的反射或折射,白色自然也无用武之地,就是这样吧?那么实际说来,我们并不能为此时此刻的自身而感到踏实和安全。谁也没办法确定我们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唯有光。如此想来不难明白太阳的用意,也不难明白现代人建立“不夜之城”或在世界每个角落大造灯具的用意。
突然间我手间静静停留的纹路开始褪色。先是变淡的肤色。接着是飞机地毯的颜色,再然后脚下地面如遇水溶解般逐一退去,溶去的颜色掺杂进底下闪烁不定的城市街道。街道似被烙煎饼用的格子锅狠狠压过,彼此间错落地留下平滑的分割。醒在凌晨的街灯被针线牵引,沿着街道边角追逐曾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窃窃私语。我低头望去,十指紧紧掐住座椅扶手。我心下明白脚底那如风光片中被摄像机一扫而过的广袤世界地心引力般将我往下吸附,恨不得纵身一跃,同女孩和猫一样。它在等待我的应答。待我唤醒在长久夜晚中沉睡的灵魂。我知道只有此时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才向我展示了它的全貌——不再从摩天大楼的高度、便利店的形状或其他片面而细微的视角去观摩,同毕加索曾作出的沃拉尔的肖像般,过去时光的碎片也从各地赶来拼贴在我脚下。
我竟像变色龙般参透了周围个中事物的表皮。我已将自己融于夜色,我可能也已把整架飞机,连同它的乘客——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变作了静静浮于城市夜空的巨大变色龙,四下景色无不从它尚不能称为鼻子的小孔到它微微扬起的螺旋形盘卷的尾部流淌出来。
“一周后来取可好?”
年轻男人的声音让我的右耳隐隐作痛。我转过头,如果还能称之为“头”,看见脸上长有雀斑的棕色头发的男孩用手指挠挠耳背。连日浸在雨中阴沉的街道正透过橱窗恶狠狠地瞪视明亮的室内。裁缝用的卷尺四处散开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间。一台缝纫桌上还留有用来测量衣服长度的直尺和粉笔。西服布料压在直尺底下,是深墨色的,布料看起来很薄,很柔软。一排衣架在我的两点钟方向,上面挂着不算多的几套做好的西装。西装笔挺挺的,比胡桃夹子里的锡兵站得还直。
“您看,您要求得这么急切,可我们也不是什么魔法师。”男孩身着白色长袖衬衣和黑色马甲,下着黑色凉爽呢面料的、像英国小学生一样的短裤,西装外套搭在右手胳膊上还没来得及放下,“就算您开店前就在门口等着,可是您之前还有其他客人。这不像是新产品发售前商店门口排队进场,您排在今天第一个您就一定能买到东西。况且就像太阳周期一般规律,做好一套西服也需要必要的过程和时间。最快,您也得给我们四天时间。
“您总不能盼着我们挥一挥直尺,您要的西服就从布料里跳出来吧?”男孩用职业的口吻稍嫌不耐烦地说道,眉头微微挤到一处却还保有职业性的礼貌。他另一只手中还端着从星巴克买来的咖啡。
“您说呢?”他定定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我的手掌纹路又变得固定起来,身上穿着一件同这里气氛毫不相符的蓝色T恤衫,胸前写着“I AM A DOC.”1。我匆忙向男孩点头。男孩表情稍有松缓。
“老师还没来,他来了我会告诉他的。”男孩说。
“那就拜托您了。”我朝他微微点下头。他早已转过身,挥了挥手中的咖啡,算是示意听见我说的话。他熟练地把扔在一处置物柜上的卷尺挂在自己脖子上,像医生挂着听诊器一般。
我走出西装店,门在我身后清脆地撞上门框。门内右上角装着铜质的小铃铛,不论人离去还是进入都会丁零作响。既省去进来之人打招呼的麻烦,也省去店内之人忽视客人的可能。
屋外是巴尔的摩都少见的阴雨连绵的夏天。西装店位于距离芒特弗农广场不远的一条较为清闲的小街道上。站在这里还能看见广场上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女孩说,握着她的步枪,“就觉得这句话特别地道。说实话不懂这么高深的道理。但总觉得好像被人批准了一样。在军队里待久了,要是没人说‘嘿,不错,你就放手干吧’这样的话总觉得不自在。虽然不清楚到底是哪个起草人想出来的句子,总的来说它向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件事——不必在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用自己的方法追求一样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都不为过——就想这么做来着。”
我点点头,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女孩。周围如小丘般倾斜的坡道上停放有几辆保养极佳的汽车。地面水洼沉积,我埋下头,模糊的水影照出无法分辨的面容。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瘦了很多,胡子也没有刮尽,头发似乎该整理一下,油腻腻的像扔在垃圾桶里的剩菜。眼窝深陷,像皮肤后有块状态极佳的磁铁将之深深吸进。鼻子上沾了块不知是什么的东西,用小指将它刮下。胸前衣襟上还有一个墨水点,也许是写什么的时候弄上去的。怪不得西装店的男孩看我的眼神多少有责备之意——西装可不是随便给这样的人穿的——或许心中这样想也不一定。
雨还在下。早晨的街道上行人不算太多,雨无意间就区分出有事可做和无事可做之人。我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忙碌、勤劳又刻苦的人的一分子。若不是顾及离开前没有合适的服装,大不会在这样下雨的早晨穿过几个街区到这里来。
我将离开这个国家。我看着水洼倒影中的自己。雨虽不大,却已然密密麻麻洒在我的头发、肩膀和胸前襟上。像是不均匀落在糕饼上的糖粉。即便是夏季,我依然觉得冷飕飕的。而这场雨丝毫没为中断夏季正该黏稠的暑气而感到抱歉,兀自从上周三一直下到现在。上周三,似乎就是那时候的事情。那天当我回到在内港租住的小公寓时,发现自己的行李被人全部扔在公寓楼门口的垃圾箱旁。总共是一个灰红相间的登山用背包,一个棕白色的运动挎包,一口袋书籍和CD,还有一幅从学美术的大学生手上买来的玛格利特的《红色模型》的临摹画。画中青灰色的靴子脚承受不了细细密密的糖粉雨,流出泪来。画纸变得凹凸不平,一道道细痕切开画面的连贯性。
我站在街对面。短短的、不到10秒能走完的距离,没有车,没有行人,没有狗。我却似被锁住般,静静盯视那堆像被人强暴般、四分五裂、肚肠流出的行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