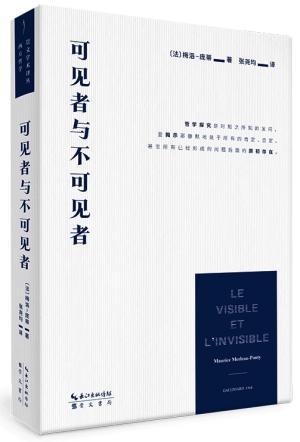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如何找到想做的事(珍藏版)
》
售價:HK$
75.9

《
征服和平:从启蒙运动到欧洲联盟
》
售價:HK$
140.8

《
利剑:导弹武器装备科普图解
》
售價:HK$
108.9

《
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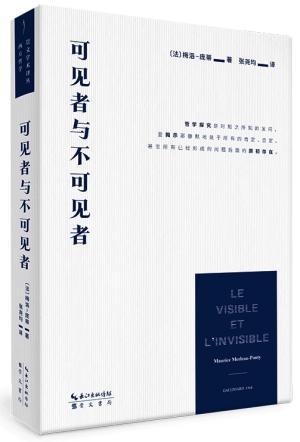
《
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梅洛-庞蒂文集”第9卷《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全新译本)
》
售價:HK$
74.8

《
启功谈诗词
》
售價:HK$
59.4

《
镰仓幕府与外来冲击:蒙古袭来与日本历史的转型
》
售價:HK$
107.8

《
企鹅海盗史
》
售價:HK$
97.9
|
| 編輯推薦: |
他是世人眼中天纵奇才的“谪仙人”
却在理想与现实的割裂中蹉跎一生
盛唐时代的浪漫之梦,不能到达的理想之境
诗仙李白,凡人李白
如凤凰现世又飞入天际,闪耀又无奈悲凉的传奇人生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为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写的一部人物评传。李白是家喻户晓的诗仙,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其人一生步履不停,浪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李白的生平为轴,以其经典诗文为枝蔓,钩沉轶闻逸事,完整再现天才诗人不平凡的诗意人生,勾勒其自由不羁的精神轨迹。全书行文诗传结合,对李白的人生历程、写作过程、思想嬗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解读,做到了以诗证人、以人解诗,既有传之严谨,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也有文之才情。
|
| 關於作者: |
|
韩潇,1993年9月生,汉族,陕西安康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诗歌史、诗律学、文体学、文学与政治关系等,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学系讲师。
|
| 目錄:
|
第一讲
诗酒谪仙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诗坛明星
第二讲
乡关何处 ——诗仙可不是外国人
第三讲
书剑童年 ——小天才的养成计划
第四讲
仗剑去国——西南天地飞起的大鹏
第五讲
桃花流水——从长江头到长江尾的漫游
第六讲
竹马青梅——那些关于青春与爱情的故事
第七讲
定居安陆——大鹏栖息的第一棵梧桐树
第八讲
蜜月生活——诗仙与盛唐的“最美时光”
第九讲
极目楚天——广阔天地,能否大有作为?
第十讲
初入长安——第一次“进京赶考”前后
第十一讲
问道中原——西方不亮东方亮,做官不成去求仙
第十二讲
移家东鲁——另立山头,再建新家
第十三讲
大鹏振翅——人还是要有理想,万一实现了呢?
第十四讲
天上人间——诗仙亲历的那些“宫闱秘事”
第十五讲
金井梧桐——多少长叹,空随一阵风
第十六讲
风歇时下——做官之难,难于上青天
第十七讲
痛饮狂歌——喝不完的酒与唱不完的歌
第十八讲
青崖白鹿——奉旨“公费旅游”到底快不快乐?
第十九讲
凤去台空——没有了梧桐,凤凰该往何处去?
第二十讲
寒夜孤灯——眼看他楼塌了
第二十一讲
塞上烽烟——“扫平狼烟”与“虎口脱险”
第二十二讲
大雾横江——惹不起,好在躲得起
第二十三讲
高楼醉卧——唐代的高级应援是什么样子?
第二十四讲
好入名山——做个唐代旅游博主也挺好
第二十五讲
古风凛凛——“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第二十六讲
风波骤起——盛衰巨变中的一念天堂
第二十七讲
梦断江湖——大鹏从此折了双翼
第二十八讲
秋霜落木——大起大落的人生总有一样的终点
第二十九讲
力尽中天——何处才有最皎洁的明月?
第三十讲
大雅千春——两条人生路中走出的崭新天地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我们青年群体中近年来流行一个“宇宙”的概念,大概是指一个与现实世界相映射、交互,同时
又自成体系的时空范畴,比如历史悠久的“古希腊神话宇宙”“《西游》《封神》宇宙”,时下风靡的
“漫威英雄宇宙”“金庸武侠宇宙”,以及走在科技最前沿的“元宇宙”等等。这么说来,盛唐诗坛乃
至盛唐这样一个文化时代其实也足以构成一个“宇宙”,因为它群星璀璨、成就斐然、包容开放、交
互多元,我姑且称之为“盛唐文化宇宙”吧。
从“宇”的空间视野来讲,盛唐文化的沃土连缀着宫苑台阁、都邑市井、田园江湖、关山塞漠;从“宙”的时间维度来看,盛唐文化的朝暮伴随着千载难逢的盛世与百年一遇的灾变。这浩荡江天与盛衰骤变中孕育和成长的盛唐文化群星们,更是在漫漫中华文明史上散发着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而这其中,李白和杜甫无疑是最光彩夺目的两颗巨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有走进李白、杜甫的世界,才能真正走近“盛唐文化宇宙”的中心。
盛唐始于公元 712 年,玄宗从睿宗手中接过皇权,盛唐的青春脉搏开始跃动,这一年杜甫在河南
巩县笔架山下降临人间;公元 762 年,李白在安徽当涂高唱《临终歌》羽化飞仙,同年玄宗与肃宗也双双晏驾,苟延残喘中的黄金时代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也就是说,盛唐的五十年,恰好是李白与杜甫同屏于人世间的五十年,这多少有些历史的偶然,但我们依然可以说,盛唐就是李白和杜甫的时代:他们的“运动足迹”拼合起来,正好构成一幅幅员辽阔的大唐版图;他们的“朋友圈”联动起来,正好拉出一个风云际会的明星群组;他们的“相册”编辑起来,正是半个世纪家国天下的阴晴云雨;他们的“心情”连缀起来,又正是一代芸芸生命的离合悲欢。凡此种种,无一不浓缩着“盛唐文化宇宙”的辉煌绚烂。
而细说起来,李白和杜甫的生命重心和人生轨迹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前者走的是一条“天阶歧途”,后者则经历了一场“盛世逆旅”。
李白的“天阶”有两个含义或者说两个归宿——一个通向真的天上,是得道成仙、大化自然;一个则通向人间的“天上”,是做帝王师、清一四海。而在李白心目中,这却是“殊途同归”,他既舍不得天上,也放不下人间,以至于忽视了这本就是一条“歧途”。故而,纵然有着极高的理想、极佳的才华、极好的机遇,李白也终因错过了太多路口,而没能真正登上“天阶”。
杜甫与“盛世”则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他的出生伴随着盛世的开启,他的成长沐浴着盛世的春风,他的“中年危机”恰逢盛世的崩坏,他的“青春回忆”满是对盛世的怀恋。然而,正如短暂盛世之于漫长历史的稍纵即逝,杜甫的人生也终究不过是一场“逆旅”,纠结在天命、人事、治乱、盛衰之间,被时光洪流裹挟着匆匆前进,且行且自珍惜。
无论“天阶歧途”还是“盛世逆旅”,对于当事人而言,都不是完美的、如愿的人生,但所幸这一切都发生在“盛唐文化宇宙”当中,天地时空中洋溢着的文化的尤其是诗的力量,弥补了一切现实的缺憾,并化两段“失意”的人生为“诗意”的传奇。
第二十五讲 古风凛凛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一、何谓“古风”?
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隐居于敬亭山的岁月,是李白晚年最为平静、安稳、幸福的一段生活,也是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反思人生和时代的一段时光。在敬亭山上,他写下了很多回忆性较强的诗篇,其中最为精心结撰的一组诗,也是李白在诗学意义上真正的“扛鼎之作”,便是《古风五十九首》。
为什么说《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在诗学意义上的“扛鼎之作”?它何以在李白“车载斗量”般的名篇佳作中脱颖而出?比之《蜀道难》《将进酒》这样更为我们熟知的代表作,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先从“古风”这个概念入手,弄明白这两个字在诗体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相比于“古风”,大家更熟悉的一个概念是“古体”。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通俗一点说是一种包含关系,即所有的“古风诗”都是“古体诗”,但不一定所有的“古体诗”都是“古风诗”。也就是说,“古体”是“古风”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古体”与“近体”是相对的,用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近体诗就是格律诗,那么不符合近体格律的诗都可以叫做“古体诗”。但是,杜甫写的那些拗体律诗,打破了近体格律,它们算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这些在近体格律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情况下写出的、与如今的近体格律稍有出入的诗,算古体诗还是近体诗?
可见,“古体”与“近体”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字句、对偶、声律、平仄、押韵等格律上,也体现在诗歌风格上,古体相对质朴、平淡、流畅,近体则相对精丽、警策、跳跃。这是两者内在诗学原理的区别,而格律只是为了符合这样的原理与追求而形成的具体外在表现。因而要给一首诗定性,还是要看它的本质。上述例子中的诗作,虽然形式不完全符合近体格律,但从本质来讲,它们都是遵循近体诗的创作原理而写成的,因而都是近体诗。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近体诗的诗学原理与追求,其实早在齐梁时期的“永明体”中就初露端倪了,沈约提出的所谓“四声八病”就是那个时期的诗歌格律。但“四声八病”与唐代的平仄格律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有的规则存在明显冲突,那么按照前面给出的定义,齐梁以后的很多与唐代律诗平仄规范格格不入的诗歌,算是近体诗吗?其实,最为科学的观点是打破这种“古近二分”的固有观念,认识到齐梁新体诗不同于汉魏古体、唐宋近体的特殊性。
但在唐代,的确有很多诗人是将这些作品也当近体诗看的,最典型的就是“复古诗学家”们。比如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他们打出的旗号就是反对齐梁以来的新体,所复的古是更为久远的汉魏以上之古,所以《古风五十九首》作为“复古诗学”的代表作,其中的“古”指的正是汉魏以上之古。汉魏以上之古都包括什么呢:《诗经》《楚辞》——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还有“建安风骨”——这是中国文人诗的真正开端,所以从“古”这个角度来讲,这组诗的着眼点和定位是非常高的!
说完了“古”再来说“风”,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它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古老的诗歌文体——《诗经》中有“国风”;一般认识中,“国风”之“风”是风俗、民歌的意思,但这种认识多是宋代以后形成的,在汉唐诗学背景下,这里的“风”大多是教化、讽喻的含义,也就是所谓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同时也是“风”的第二层含义;第三层含义便是“风骨”,按照《文心雕龙》的论述,“风”与“骨”其实是两个概念,后者更侧重内在的精神品质,前者则更侧重整体的艺术氛围和风格特征,当然这二者又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
那么《古风五十九首》的“风”究竟是哪种含义呢?我认为三者都有——在艺术上,它追求一种古典、雅正的风格和品质;在现实意义上,他强调发挥诗歌的教化和讽喻功能;而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诗经》的“国风”就是其最好的标准和范式之一。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风”的三重含义,那么最贴切的应当是“风雅”。
综上所述,“古风”就是汉魏以上之“古”与风雅之“风”,这也是李白这组作品的定位,体现了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与艺术追求。总的来说,一首诗如果能称得上有“古风”,至少要符合以下三大特点:第一是在主旨思想上崇尚王道教化、圣贤经典,无论是表达的观点还是所用的典故都要符合诗教正统之道;第二是在艺术风格上以典雅为务,在意象、素材的选择和情景、诗境的营造方面都尽量追求古朴;第三是在诗学传统上,继承《诗经》《楚辞》和“建安风骨”这一脉的理论和创作风格,追求风雅、兴寄、文质彬彬。
以这样严格的标准来看,古体诗中能够称得上“古风”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但这才是李白心中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就连《蜀道难》《将进酒》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远不可及。
二、“复古诗学”的总纲
李白这一组汇集一生心血的巨作,其第一首是全部五十九首的总纲,也是唐代“复古诗学”的重要纲领性著作: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开篇第一句,李白就开宗明义地给出了“复古诗学”的标准、背景与目的:“大雅”是古典诗文的最高标准。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古代地位最高的文学经典,它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又以“雅”的地位最高,是周王朝的王室音乐。而“雅”又分“大雅”“小雅”,以“大雅”地位为高,它建立在周王朝礼乐文明、天下大同的政治背景之上,宣扬的是王道教化,歌颂的是天子威仪,风格最为典雅庄重,是历代推崇的“诗中之诗”,也是唐代“复古诗学”所标榜的典范;但是,自西周灭亡,随着政局的变动、世道的沦丧,“大雅”之音便不再有新创,一直到李白所处的盛唐都久久沉沦,故而才需要有人来复兴它;而“复古诗学”者的目的,自然是要复兴“大雅正声”,更进一步说,就是再现圣人礼乐、王道教化、天下大同,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李白的文学理想和政治理想是相通的。接下来两段,他对以上论点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先用十二句解释“大雅久不作”的具体内涵,这是李白对于诗歌发展史的一个完整回顾,有着重要的价值: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王风”是《诗经》中“十五国风”的一部分,主要是春秋时期,在西周王畿地区流行起来的诗歌,体现了王化之地的士人遭遇丧乱之后的困顿与失意,反映出李白对春秋时期政教和文化的整体认知,认为“雅”乐寝、“风”声作,已经是正声沦丧的开端。而到了战国,情况则愈演愈烈,无休止的兵戈战乱成为了时代的主调,各国之间龙虎相斗,最终由无文的暴秦之国实现了统一。由于国家上下一片动荡,这段时间内,《诗经》这样的雅乐正声自然不闻于世,而饱含哀怨之情、忧国忧民之思的《楚辞》应运而生。到了汉代,新的大一统帝国再度推崇儒道,也短暂出现过一段文学的复兴。以扬雄、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以“润色鸿业”的文字激荡起新的波澜,开创了流传甚广的诗赋体式,虽然其后兴亡代变,文学的发展也几经转折,但整体上再也没有回到“大雅”时代那样文质彬彬的典范状态。尤其是“建安风骨”的绝唱以后,晋宋南朝以来的诗文,都是华而不实、文胜于质、过于绮丽而无足可观的。
总结起来,这一段集中论述了三大观点:在李白看来,此前历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趋势是整体下行的;文学的下行衰退,与政治的兴亡变化密切相关;眼前的文学现状是不甚可观、亟待改善的。正是基于这三点认识,李白在接下来十句诗中提出了他的复古宗旨,详细论述了在盛唐实现诗歌复古的可行性: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圣代”是指李白所处的唐代,“元古”指“大雅”的时代——西周。李白说“圣代复元古”是有现实依据的,唐代在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重新确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编修了《五经正义》,比如明确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比如依据周礼修订了“贞观礼”“开元礼”等礼仪制度,这些都是“圣代复元古”的具体体现。同时君王提倡无为而治,又给群臣们留下了大展身手的空间,这让李白认为诗歌复古同样有了充分的现实政治基础。在休明之世的鼓舞下,各地人才应时而动,鱼跃龙门,各显其能,在盛唐的璀璨星空中熠熠生辉,发散着文质相协的光芒,这是李白心中诗学复古的人才基础。而身为人才中的佼佼者,李白对于自己的定位也非常高,他要成为像孔子一样的“删述之人”。孔子删《诗经》,为后来的从文者确立了万世不更的典范,李白同样要在唐代重建文学规范,使得它的光辉泽被后世、闪耀千春。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他也将像孔子一样,于“获麟”之际绝笔,不再著述。“获麟”是春秋中的典故:鲁哀公打猎时猎到一只麒麟,孔子听闻十分感慨,因为麒麟是神兽,只出现在盛世,哀公之世并非盛世却有麒麟出现,且被捕获,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寓意吉凶失序、天下将乱。这个典故与李白常常感叹的“凤去台空”其本质是相同的,李白经历了开元盛世,又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丧乱,便认准了眼下正是行删述之事、立千秋之功的大好时机。这正是他创作《古风五十九首》的直接目的。
通过这一首诗,我们了解到了李白对于文学创作功用的认识。他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在文学传统上,他是孔子“诗教说”的坚定拥护者,甚至有以“当代孔子”自居的雄心壮志,但同时李白也创作了很多抒写性灵的作品,这又怎么解释呢?其实理解起来并不难,因为文学的样貌是多变的,在李白心中,“诗教”之文与“性灵”有着清晰的界限,他既推崇文学的教化功能,也不否认文学的娱兴作用,只是看待二者有高低、主次之分罢了。而毫无疑问,《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诗歌创作的主业,是其一生心血的结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