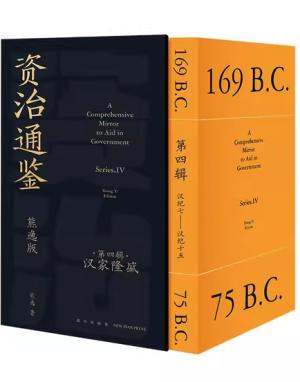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漫画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55.2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59.8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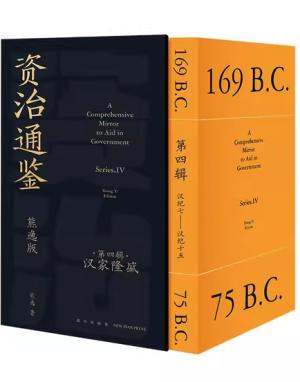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58.9
|
| 內容簡介: |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
| 關於作者: |
自序
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FoedorDostoevskY,1821—1881在《群魔》的扉页上引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的一段话:“刚巧在不远之处,正有一大群猪在饲食。群鬼就要求耶稣准许它们进到猪群里,耶稣答应了。群鬼就离开了那人,投入猪群去。那群猪忽然冲下悬崖,掉进湖里统统淹死了。“陀氏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当时俄罗斯混乱的道德与社会状况是否准确,一向是有争论的,但这个“魔鬼附体”的比喻却使人联想到人类历史上某些疯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魔鬼”作为一种客体的意象制约了主体的理性,同时它又是通过主体的非理性的疯狂行为来完成一种灾难的创举。关于这样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诗人疯狂的因素,基督教经典与陀氏小说里称之为“魔鬼附体”,而在文学史上,则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现象:thedaimonic,根据比较直接的理解,可以把它译作“恶魔性”。我们从陀氏引用的圣经故事里还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这个词: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某种拯救的含义,因为当魔鬼附在猪的身上疯狂地跳下河里,那个被魔鬼纠缠的人却获得了拯救。我的理解“恶魔性”主要体现在猪疯狂冲下悬崖这一刹那,它意味着,这种恶魔性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神的意志,大破坏中包含了大创造的意图。
如果联系到20世纪的世界性现实环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魔性的忧虑非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至今还闪烁着先知的光彩。它的现实依据完全不同于以前几个世纪。
……
|
| 目錄:
|
自序
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
试论张炜的《外省书》与《能不忆蜀葵》中的恶魔性因素
从巴赫金的民间理论看《兄弟》的民间叙事
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
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
“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试论《生死疲劳》的民间叙事(之一)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试论《生死疲劳》的民间叙事(之二)
作者简介
著述年表
|
| 內容試閱:
|
自序
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FoedorDostoevskY,1821—1881在《群魔》的扉页上引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的一段话:“刚巧在不远之处,正有一大群猪在饲食。群鬼就要求耶稣准许它们进到猪群里,耶稣答应了。群鬼就离开了那人,投入猪群去。那群猪忽然冲下悬崖,掉进湖里统统淹死了。“陀氏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当时俄罗斯混乱的道德与社会状况是否准确,一向是有争论的,但这个“魔鬼附体”的比喻却使人联想到人类历史上某些疯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魔鬼”作为一种客体的意象制约了主体的理性,同时它又是通过主体的非理性的疯狂行为来完成一种灾难的创举。关于这样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诗人疯狂的因素,基督教经典与陀氏小说里称之为“魔鬼附体”,而在文学史上,则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现象:thedaimonic,根据比较直接的理解,可以把它译作“恶魔性”。我们从陀氏引用的圣经故事里还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这个词: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某种拯救的含义,因为当魔鬼附在猪的身上疯狂地跳下河里,那个被魔鬼纠缠的人却获得了拯救。我的理解“恶魔性”主要体现在猪疯狂冲下悬崖这一刹那,它意味着,这种恶魔性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神的意志,大破坏中包含了大创造的意图。
如果联系到20世纪的世界性现实环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魔性的忧虑非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至今还闪烁着先知的光彩。它的现实依据完全不同于以前几个世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