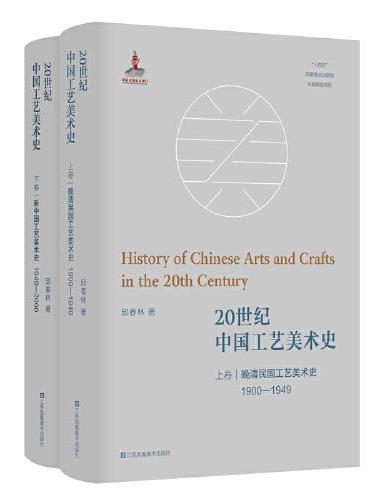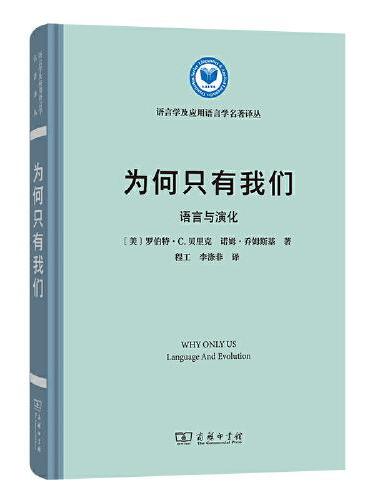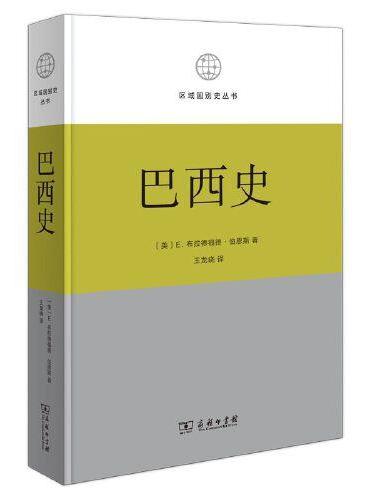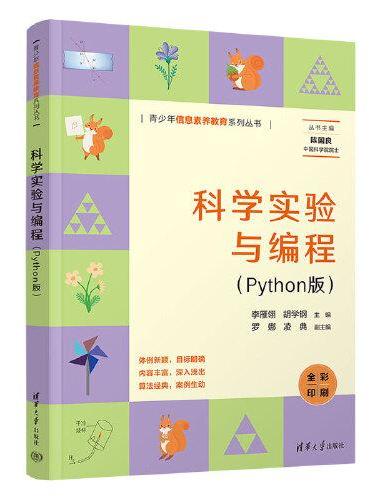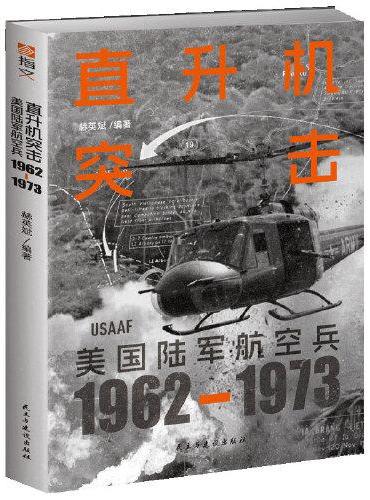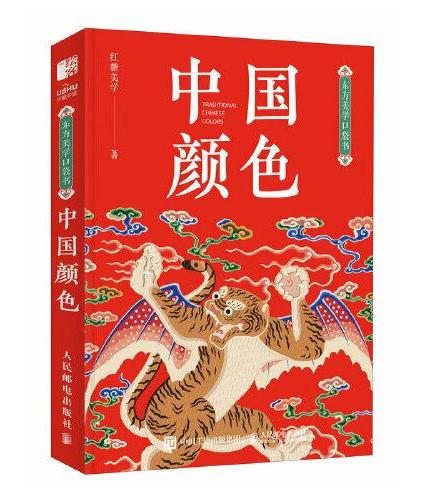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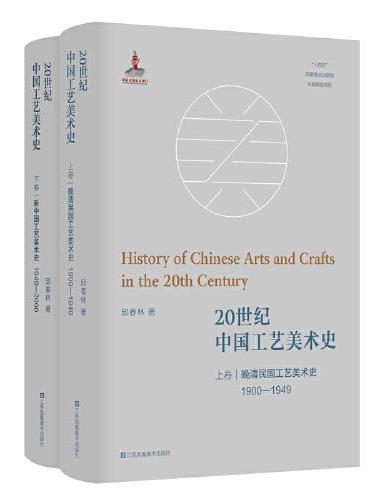
《
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下卷)
》
售價:HK$
5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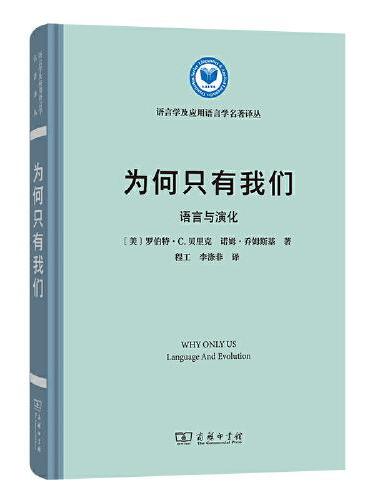
《
为何只有我们:语言与演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著译丛)
》
售價:HK$
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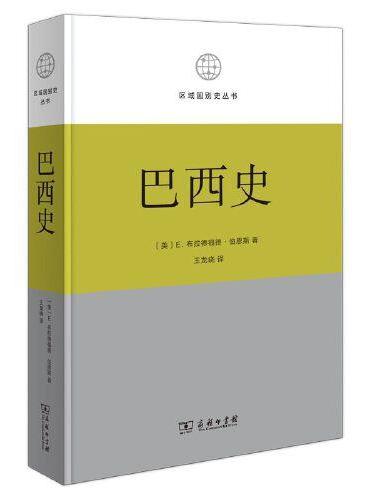
《
巴西史(区域国别史丛书)
》
售價:HK$
1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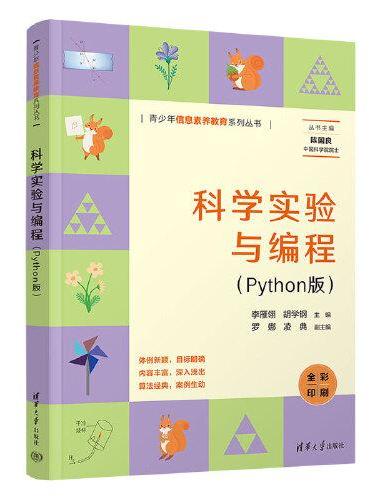
《
科学实验与编程(Python版)
》
售價:HK$
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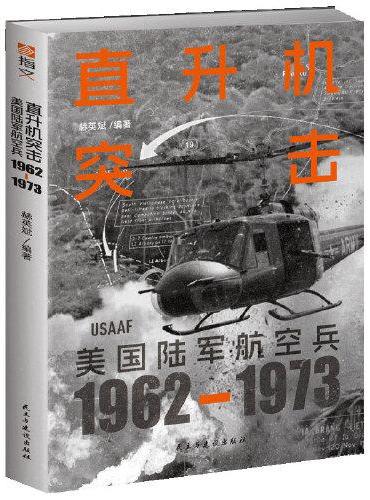
《
直升机突击:美国陆军航空兵:1962—1973
》
售價:HK$
167.8

《
元代丝绸之路史论稿
》
售價:HK$
1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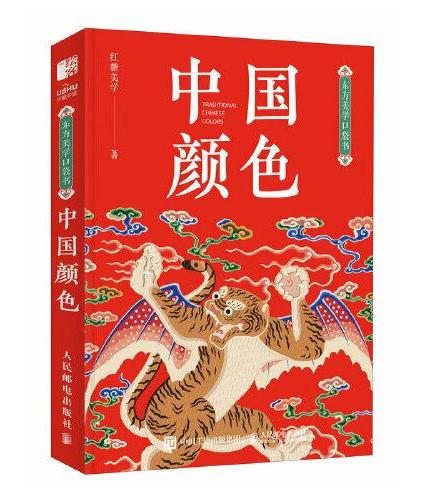
《
东方美学口袋书 中国颜色
》
售價:HK$
47.8

《
直到河流尽头
》
售價:HK$
42.0
|
| 編輯推薦: |
潜伏与反潜伏,从兄弟情深到举枪相向,土匪版《潜伏》
本故事源于作者意外得到的一份档案残卷
将悬疑、推理进行到底,疯狂榨干你的想象力
天涯、猫扑热帖,网络点击超过2000万次
多方力量角逐,高手与高手大斗智
两代人三十年,苦苦追寻一个惊天秘密
|
| 內容簡介: |
|
一场熊熊烈火,使卅街档案馆的绝密卷宗重见天日。1946年,在平息了国民党及残余日本关东军发动的暴乱之后,报信的火麟食盒被人劫走。从此,神秘事件接连涌现:狐仙堂的诡异符咒,被撕碎的刀疤人,庞大的地下要塞,以及被屠杀的剃发黑斤人……究竟食盒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使得与食盒有关的人全都离奇身亡?几十年前的谜案缘何与现代人的人生际遇紧密相连?谜团层出不穷,分析层层递进,误导接二连三,看本书怎样将悬疑、推理进行到底,疯狂榨干你的想象力!
|
| 關於作者: |
|
叶遁,本名夏润秋,吉林通化人。关于本书的创作源于多年前购买的一份真实档案残卷,册中记录的内容光怪陆离,神秘莫测。作者在瞠目结舌之余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将个中谜团逐一解开,才有了这本书。该书在天涯、猫扑等网站连载时,受到无数粉丝的热烈追捧,至今总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
|
| 目錄:
|
楔子 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第一章 冰面之下
第二章 查魔坟
第三章 蒸发的刀疤人
第四章 就地成灰
第五章 绺门迷雾
第六章 裘四当家
第七章 秦队长的左手
第八章 野鬼山魈
第九章 黑枪!黑枪!
第十章 震江龙之死
第十一章 剃发黑斤人
第十二章 黄三和花舌子
第十三章 飞鹰堡之谜
第十四章 叶西岭!叶西岭!
第十五章 如履薄冰
第十六章 翻手为云
第十七章 覆手为雨
第十八章 老印的往事
第十九章 档案管理员的秘密
第二十章 遍地无人
第二十一章 后山柞林
第二十二章 震江龙和王老疙瘩
第二十三章 一触即发
第二十四章 遍地枪火
第二十五章 柜子里的秘密
第二十六章 魔鬼要塞
第二十七章 生死一线
第二十八章 天罡路号院
第二十九章 口令!口令!
第三十章 火麟食盒
第三十一章 蛇足
|
| 內容試閱:
|
楔子
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如果不是三十多年前那场熊熊烈火,恐怕我最不相信的,就是这篇故事的第一句话。
今天,我最后一次走进卅街档案馆,在掸落这些绝密卷宗上厚厚的积尘之后,我在它们面前站了好一阵子。阳光透过斑驳的窗玻璃照进来,刺鼻的尘土飘荡在我的周围,还有一些粘在我稀疏的胡须上。我伸出手指挨个抚摸这些打了多年交道的卷宗,它们被历史涂满了褶皱,就像我的老伙计惨不忍睹的面颊。
我太想念我的老伙计啦!要不是我的老伙计,我这半辈子或许平淡无奇,而这些诡异莫测的神秘事件就不会书写在这里。你问我都是什么神秘事件?嗨!简直太多了,比如:第五号卷宗里的“纸人割头颅”事件、第十二号卷宗里的“鸭绿江水啸”事件、第三十号卷宗里的“古刹石佛异变”事件、第五十五号卷宗里的“生寒镜和胎盘”事件……
现在想起来,我似乎还能看到卷宗里当事人的恐惧、战栗、惊慌和绝望,它们时常让我在睡梦中冷汗连连;而当事人在那些激荡的岁月里所表现出的欢喜、坚强和希望,在这个世界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它们将长久地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处,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好啦好啦,我唠叨起来就没完没了,那个跟我交接的年轻人正不耐烦地等着我呢,我得把卅街档案馆的钥匙给他——他看起来那么朝气蓬勃,而我三十年前,就是在他的这个年纪……
第一份卷宗:火麟食盒事件
这份卷宗封面的基本信息如下:
中共通化专区五人小组调查案卷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冯健
编号(18)第(1)册
本卷共(2)册本册共(89)页
自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起至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止
立卷单位:通化专区某军工厂
注:其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冯健”及其他数字均为毛笔写就,余为黑色印刷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市发生了一场震惊全省的火灾。作为这场灾难的亲历者,至今我还心有余悸。而正是因为这场罕见的火灾,才使我得到了上面的这份绝密卷宗。
这场大火是由卅街尽头的西山火葬场引起的,火势一路蔓延直至街口档案馆。当时是清晨,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浓烟滚滚的卅街,现场指挥员请求我们务必把所有的卷宗抢救出来,我现在还能记起他带着哭腔的喊话:“这些可都是鲜活的历史啊!”
那个年代人心还没有坏掉,大伙儿干什么都是实打实,所以这些“鲜活的历史”得以保存至今,我们的确功不可没。
搬出的卷宗被要求放在一辆大卡车上,由于火灾现场非常混乱,负责运送这批卷宗的司机急忙掉头就开走了。事后我才发现,被遗落的那份就在我的脚边。
关于这份卷宗,除了开篇罗列的基本信息之外,促使我翻看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卷宗封面鲜红的“慎”字阴文印章。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卅街档案馆所有带“慎”字阴文印章的卷宗背后都隐藏着惊心动魄的……恐怖!
这份卷宗是1956年“肃反”时期一个叫冯健的解放军老兵的交代材料。由于那个时代明显的意识形态充斥在字里行间,所以我在转述时对个别无关紧要的词句进行了删减,同时也对整份卷宗进行了适当的润色。另外,为了便于阅读,我人为地将卷宗分成了若干章节并配以标题。所以,在请求读者对我擅自做主予以原谅的同时,我想郑重地说上一句:请注意,你们看到的仅仅是个故事。
以下就是冯健在解放战争期间关于“失踪”问题的供词——也就是说,我们的叙述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章
冰面之下
我叫冯健,1945年秋随部队入关,我们是第一批挺进东北的八路军。
在我军接管通化城半年以后,也就是1946年大年初二那天晚上,国民党地下组织伙同残余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一场武装暴乱。暴乱被我军平息以后,郝班长带领我们去清除日伪军尸首。那天有零下四十多度,通化城的百姓用“嘎嘎冷”来形容这样的天气。我是南方人,之所以能经受得起那样的冰天雪地,完全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
日本人的尸首铺天盖地。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整整十四年的压迫和奴役,让老百姓恨透了这伙禽兽不如的侵略者。他们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这些负隅顽抗的暴乱分子身上,加之他们生活本来就很贫困,所以一千多具尸首上的衣物基本被剥得精光——手表、钢笔、戒指,凡是值钱的东西统统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嘴巴里的金牙都被薅了出来。
郝班长带领我们赶到的时候,裸尸已经被成群结队的野狗咬得不成样子,像被切开的红萝卜,嘎嘎冷的酷寒中,在尸首上是见不到血的。那么,这千余具尸首如何处理?
拉到荒山野外埋掉肯定不切实际,寒冬腊月冻土层达一米以下,工作量太大;火化更是行不通,当时老百姓连冬天取暖的燃料都无法保证,又怎么能浪费在这些死人身上;最后上级不得已做了一个决定:水葬。
水葬日本人尸首这件事在通化城不是秘密,当时生活在那里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组织上不妨去问问他们。
由于当时人手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发动当地的百姓们帮忙,把尸首装进牛车马车,割开江面厚厚的冰层投到冰窟窿里。
说起来似乎挺简单,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足足干了一天。特别是砸冰层的工作,酷寒使得冰面隆起了连绵起伏的冰包,人站在上面双脚不但要吃住劲,手上的尖镐也得抡圆了刨才行,不然根本刨不动。我们班的小赵年龄比我小,他没什么经验,还没活动好身子就去抡尖镐,结果没刨两下胳膊就给弄脱臼了。幸亏郝班长曾经干过几天救护兵,按摩了一会儿才给他复位。
就在水葬工作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桩怪事。
当时我和小赵正准备把最后一车尸首塞进冰窟窿,赶车的吴老蔫也帮着我们忙活。整整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就连郝班长这样的东北大汉都有些疲沓,更别说我和小赵了。吴老蔫把一具尸首扔进冰窟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分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一看烟卷就知道是日本人的,于是便问他从尸首上弄了多少东西。吴老蔫憨厚地笑了笑说:“不少咧!还有三盒日本罐头。”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我的脚下突然重重地晃了两晃;小赵下盘不稳猛地跌了个大跟头。接着,冰层之下传来了一阵“嘎啦啦”的摩擦声,像是金属之类的硬物贴在江面移动。小赵卧在冰面上一脸惊慌地看着郝班长,意思是在问郝班长这是怎么回事。郝班长起脚跺向冰面,几下过后刺耳的摩擦声居然消失了。郝班长把小赵拉起来:“估摸着是尸首太多堵住了。”他指着江桥下的一个冰窟窿说,“往那里塞吧。赶紧弄完咱们好回去吃饭,天快黑了。”
吴老蔫拉过马缰,对我们说:“八路军同志,你们先把烟抽完缓缓劲头,我把马车先赶到江桥下面,这样能省把力气。”
吴老蔫往江桥的方向赶着马车。起初那匹黑马还往前走,但是距离江桥下的冰窟窿十米左右的时候,它却在原地打起了转转,马蹄子磕得冰碴横飞,摇着头不停地嘶叫,任吴老蔫怎么抽打它都不肯再向前一步——黑马似乎非常恐惧江桥下的那个冰窟窿。
天色越来越暗,我和小赵赶紧扔了烟头过去帮忙。小赵拉着马缰,我在后面推着车,吴老蔫坐在日本人的尸首上挥动着马鞭,但是即便这样,黑马依旧不肯走动。我回身观察,这才看到黑马浑身不停地抖动,鼻孔里冒着白花花的粗气。我心里泛起了嘀咕,忙问吴老蔫:“这牲口是不是病了?”
“算啦算啦!就这么一旮瘩远,别折腾了。”郝班长把两具冻得像木头的尸首从车上拽下来,然后扯着它们走向江桥下的冰窟窿。
我们把整车的尸首搬到冰窟窿旁边之后,开始往江水里投掷。
那天实在是太冷了,溅起的水珠粘到裤腿上就挂冰花。小赵塞入一具尸首后正要回身的时候,不料“啪叽”一声跌在冰面上。他的小半个身子瞬间就滑入了冰窟窿里,而且还在不断地下坠。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小赵哇哇乱叫,两根胳膊冲着我拼命地挥动着。我连忙扑倒在地拉住了他。我本想拉他上来,扯了几把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些异想天开——冰窟窿里似乎有种强大的吸力,连我都在跟着小赵一起往里滑。
郝班长毕竟经验丰富,他抄起吴老蔫手里的马鞭麻利地绑在小赵的腕子上,在吴老蔫的配合下,小赵的身子才一点点浮上水面。我能感觉出来,小赵的脚下有“东西”,不然就凭他的体重,根本不会连我都拉不住。随着小赵的身子慢慢地被拉上来,那个“东西”也浮出了江面——居然是一只惨白惨白的手!
老北风呼啸刮过,一些细碎的冰碴打得我睁不开眼。这种景象在南方是见不到的,它常常让我想起那些炮火连天的战役中飞扬的弹片。
吴老蔫被这只从冰窟窿里伸出的手吓坏了,他起脚用力地蹬踢,但是这只瘆人的手像是镶在小赵的脚踝上一样,居然纹丝不动。郝班长制止了吴老蔫:“别踹啦!让我来吧。”郝班长把这几根不甘心的手指全部掰折,小赵的腿这才被解放出来。郝班长说:“没想到还有一个活口,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扛冻啦!”
小赵见那只残破的手沉入江水之后才破涕为笑:“我还以为是冰下的水鬼要抓我呐!”
郝班长说:“别胡咧咧!还有最后这一撮了,赶紧弄吧。”
就在我们把剩余的尸首处理完毕,正向马车走去的时候,那匹黑马像是发了疯一般在冰面上狂奔起来。由于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它身上,根本没有发现江桥下冰窟窿起了异样。等到刺耳的摩擦声再次响起时,从冰窟窿那边延伸出来的裂缝瞬间便到了脚下。整个冰面凶猛地震动了一阵儿,我们已经身在江中了。
那真是彻骨的冰冷,我几乎被弄懵了,分不清东南西北一个劲儿在水里扑腾。碎裂的冰块撞着我的脸颊,我能感觉到它们在我裸露的皮肤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这时候,在浮动的碎冰之下,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撑了上来,紧接着又沉了下去,它一上一下很有节奏地涌动着,直奔着我的方向游过来。我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不停地呼喊着郝班长,几乎就在那东西快要顶到我的屁股上时,郝班长和吴老蔫合力把我扯了上来。
冰层还在“咔咔”地碎裂。我们四个逃上江岸时,浑身上下已经挂满了冰甲。
江中的黑物还在上下波动,“嘎啦啦”的摩擦声搅得我全身发痒。由于天色的原因,我们根本看不清黑物究竟是什么东西。郝班长哆嗦着胳膊拉起枪栓,对着它放了一枪,“嘡”的一声,闪过一道火星。我知道子弹肯定是迸飞了。小赵也看出来了,他战战兢兢地问郝班长:“怎么连子弹都打不透,会是啥玩意儿?”
郝班长也有些茫然:“真是怪事!对了,刚刚那匹黑马好像……”
吴老蔫听到郝班长说起黑马,扯了扯郝班长的衣角:“八路军同志,有些话,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郝班长说:“咱们都是老乡,有啥话说就是咧!”
吴老蔫咽下一口唾沫,指着江中的黑物异常恐惧地说:“它——是这江里的水鬼!在这旮瘩好些年咧,不少人都让它祸害死了,去年俺家隔壁的杜老八……”
“水鬼?”小赵弹出一嗓子打断了吴老蔫。他紧紧地薅住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指哆嗦得乒乒乓乓。
吴老蔫瞄了一眼郝班长,继续说:“这江的上游有条蝲蛄河,原来就是一汪子水。后来不知怎么的,河水突然涨了起来,岸边的乡亲们经常看到有个像黑锅底儿的大壳子在水里边游荡,特别是下大暴雨的时候,那玩意儿保准出来透透气。说起来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有个远房亲戚叫二黑子,是远近闻名的大胆子,他不信邪,非要弄明白那个黑糊糊的大壳子是啥玩意儿,结果就死在蝲蛄河里了,连个尸首都没找到……”
小赵迫不及待地追问道:“那后来弄清楚那个大壳子是啥玩意儿了吗?”
吴老蔫用袖口抹了一把挂在嘴唇上的鼻涕:“二黑子他们屯子里有个识文断字的老秀才,屯子里头有啥红喜白丧的事儿都去问他。老秀才说这个大壳子名字叫做鳖龙,是河神水鬼一类的东西,那是万万不能碰的!”他指了指江面,继续说:“要不然刚才咋连子弹都打不透它!”
我问吴老蔫:“那这个什么鳖龙怎么又从蝲蛄河跑到这条江里了?”
吴老蔫说:“都是那老秀才出的馊主意!他吩咐屯子里的乡亲们给那玩意儿盖了一座仙家楼,说是有了镇物它就不会再兴风作浪了。后来,鳖龙就顺水跑到这条江里啦。”他指着不远处的荒草丛,继续说:“鳖龙来到这条江以后,这儿的人也盖起了一座仙家楼,就在那旮瘩。可是它还是隔三差五就要人命,这些年在江里摸鱼抓虾的人已经死了几十口子!”
“都别扯犊子啦!都啥年月了还信这些玩意儿!”郝班长有些不耐烦,他对吴老蔫说,“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的马车了?再不去追它就尥没影了。”
郝班长话音刚落,我便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踢踏的声响,黑马居然沿着江岸向我们的方向跑了过来。吴老蔫咧嘴笑着说:“这畜生还算有良心,我没白疼它!”
江岸较多碎石,黑马在奔跑时马车被震得叮当乱响。只是我从响声里判断,这些撞击不仅仅来自马车本身,车上似乎还多了些东西!
由于全城的搜捕工作还在持续,那些未落网的暴乱分子有可能潜伏在任何一个角落,他们身处暗处不得不多加提防。于是我赶紧拉起了枪栓。吴老蔫上前两步扯过马缰,还没等马车停稳,“嘭”的一响从上面摔下一个人来。我警觉地举起手中的步枪,戳住他的身子喊道:“谁?举起手来!”
郝班长和小赵俯身查看,只见这人穿了一件粗布棉衣,上面七零八落地割开了好些口子,裸露的棉絮上粘着一块块血痂,像是刚刚经历过一番打斗。他睁开眼睛的速度极慢,当看到我们身上穿的军装时,却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然后他把搂在怀里的一个包袱交到郝班长手中说:“不要……打开它!去石人沟交给,交给警备连秦队长。十万火急!”
我一听他说“警备连秦队长”,心里琢磨应该是自己人,便准备和小赵一起把他扶起来。但是他的眼睛在掠过破裂的冰面之后,突然重重地喘了一声,暴凸的眼球里塞满了战栗!这时,我看到一股鲜血由他嘴里迸出,同鲜血一块迸出来的还有两个字:“鬼!鬼!”
小赵一把将这个人扔在我怀里,踉踉跄跄地跑到郝班长身边,他带着哭腔说:“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他说,他说那个东西是鬼,是鬼哇!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郝班长没有理会小赵的哀求,他用手探了探这个人的鼻息,摇头说道:“死了。”
江风呜呜地吹,没了命地往皮肉下面的骨头里楔,湿透的棉衣像铁皮一样跟着江风变本加厉地摧残着身子。我再去观察破冰的江面,那个黑物似乎正在缓缓下沉,原本汹涌的波动平息了许多。我问郝班长:“现在怎么办?”
郝班长把那个包袱拿过来,待解开外边的两层粗布之后,我看到了一只食盒。食盒的做工甚是讲究,虽然天色较暗,我还是看清了食盒表面的图案:一只踩着流火的麒麟。我去掀火麟食盒的盖子,郝班长一把按住我的手:“别动!”他转脸对小赵和吴老蔫说,“你们把尸首拉回城里交给警备连,我估摸着这个人是咱们的同志;我和小冯去石人沟送东西。”
吴老蔫哧溜哧溜地抽搭着鼻涕,他指着我和郝班长身上冰甲般的棉衣说:“八路军同志,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这样赶路,怕是走不出二里地就得活活冻死。这时节的老北风比石头还硬,再结实的身子骨也架不住它的折腾。”
说起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江桥之上“嘎楞楞”停住了一辆卡车。有人推开车门冲着我们喊话:“是老郝吧?别的班都收工了,你们咋还没整完?要是弄完了赶紧上来,我捎你们一段。”
我从声音里听出这是后勤部的周班长,于是连忙回话道:“周班长,我和郝班长掉进冰窟窿里了,你车上装的是什么?要是有棉衣棉裤先借我们两件。”
周班长在卡车后头捣鼓了一会儿,扔下两套军用棉衣,嘴里连连嘟囔:“麻溜儿换上跟我上车,再耽搁这破车该熄火啦!”
郝班长冲着他摆摆手:“老周,你先回去吧,我们还得再忙活一阵。”
周班长关上车门时不忘嘱咐道:“记得回去到我那里登记。”说话间,汽车“突突”地开走了。
郝班长赶紧让吴老蔫和小赵并起身子搪着凛冽的老北风,我们这才换上了干爽的棉衣。
就这样,我和郝班长带着火麟食盒前往石人沟。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此后竟然会发生那么多离奇而诡异的事情,虽然我有幸在灾难中逃过一劫,但是这段经历足以刻骨铭心。
石人沟距离城区较远,若是走大路需要花费近两个小时,那里曾经有座日本人开设的矿业所,隶属东边道炼铁会社。郝班长为了节省时间,决定抄近路尽快赶去。我们在江边的小路上马不停蹄,由于全城的戒严还没有解除,许多老百姓都被要求夜间不得外出,所以沿路我们只碰到了三名负责警戒的同志。在向他们说明情况之后,我和郝班长继续赶赴石人沟。
路上我一直都在琢磨冰面之下的那个黑物,吴老蔫说那个东西是鳖龙;而刚刚死掉的人喊了两声“鬼”,从他死亡时的表情来看,似乎从前就知道这个黑物;还有那匹狂奔暴走的黑马,也好像事先就知道冰面要破裂……我越想越觉得蹊跷,便忍不住问郝班长:“你说那个黑物不会真的是‘脏’东西吧?”
郝班长义正词严地说:“冯健同志,你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八路军战士咋能……”
郝班长话还没有讲完,便“噔”的一声停住了脚步。他表情惊恐地盯着前方,原本张开的嘴巴“啪叽”一声紧紧闭了起来。顺着他慢慢伸出的胳膊,我看到就在不远处有两团飘忽的长影。我第一时间就判断它们绝对不是人——因为这两团黑影几乎是耸在路面之上的,高度少说也有三米,怎么会有三米多高的人呢?!
我真是吓透了!刚刚冰面之下的黑物带来的恐惧还没有消减,这回又碰到了两团巨型长影,由不得我往别的地方想。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向组织坦白,那一刻我确实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我愿意接受广大群众的批评,并请求组织处理。
我和郝班长立在风中,各自屏住呼吸观察那两团长影,它们飘荡的速度不快不慢,每次前移都横向着晃上两晃,像极了我南方老家无常殿里的黑白二爷。我捅了捅郝班长,指着脚下说:“班长,是底下的两位爷。”
我能看出郝班长在犹豫,他说话支支吾吾:“那啥……那个啥,你咋知道?”
我说:“城里一下子死了上千口鬼子,这些家伙人生地不熟,阴曹地府里还不派人帮它们认认路?”
郝班长点点头“嗯”了一声,却又马上瞪了瞪我:“差点让你小子给带沟里去!”他把火麟食盒交到我手上,拉起了枪栓,“不管它们是啥玩意儿,咱们都不能再耽搁了。一会儿要是有啥情况,你带着火麟食盒先走。记住,这是命令。”
我和郝班长带着满腔惶恐向两团长影靠拢。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的鞋底几乎是贴着地皮蹭过去的。在距离它们一百米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些异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两团长影的下端——“吱呦”、“吱呦”、“吱呦”……每发出一声这样的响动,长影上方就跟着晃上两晃。我的心里泛起嘀咕,难道阴曹地府的黑白二爷行路也会发出声音?
郝班长听了一阵“吱呦”声后,吧嗒着眼睛看了看我,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俯下身来观察覆着冰的路面,我也跟着他蹲下了身子。路面上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孔洞,它们应该是被一种尖利的器物戳开的,一些小块的冰碴散落在一旁。郝班长捡起冰碴反复端详了一番,又在路面的几个孔洞之间比量了几下,这才说道:“小冯,我知道它们是啥玩意儿了。”
我既紧张又兴奋地问道:“啥玩意儿?”
郝班长收起步枪,突然冷笑了一声:“就是你说的黑白二爷。”
第二章
查魔坟
听到郝班长这么说,我的心脏差点从胸膛里蹿出去。要知道郝班长平日里极少跟我们开玩笑,总是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所以他的这句话让我深信不疑。
就在这个时候,“吱呦”声却一下子消失了,两团长影居然停在了路面。它们叽喳了两句之后,咯咯的笑声传了过来。由于距离稍远,它们叽喳的内容却听不真切。火光瞬间闪烁在它们之间,停了几秒钟又灭掉了。
我问郝班长:“它们,它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郝班长说:“发现个屁!瞧你吓得那个德行。它们是黑白二爷不假,不过是踩着高跷的黑白二爷。”
我不解地问道:“踩着高跷的黑白二爷?”
郝班长并不理会我,大步流星地向它们走去,边走边喊道:“你们两个咋回事,黑灯瞎火的搁这儿晃悠啥呢,不知道全城都在戒严吗?”
我赶紧追着郝班长来到他们身边,这才发现两个身穿长袍的老乡正在抽着烟,他们每人的脚下各踩着一副一米左右的高跷——难怪覆着冰的路面会被戳出那么多孔洞!
他们看到我和郝班长身上的军装之后,一脸歉意地说:“八路军同志,俺们俩是在城里扭大秧歌的。这不刚刚灭了小鬼子的暴乱嘛,大伙都想乐呵乐呵。蹦跶了一天有些疲沓,高跷死沉死沉的,扛着太费劲……”
郝班长嘱咐了他们两句,让他们尽快赶回自己的家里,又询问了一下石人沟的方向。
他们指着江岸不远处说:“那旮瘩就是俺们村,顺着村子一直走就到石人沟咧。不过这么走有些绕远。”其中一个人吧嗒了两口烟,又说:“近路也有,你们翻过南头的查魔坟再走三里地就到了。只不过,查魔坟……”
我见他有些犹豫,连忙问道:“查魔坟怎么啦?”
他“吱呦”一声把扔掉的烟头踩灭,说:“查魔坟是片乱葬岗子,树林子里有百十来座坟茔地。在那里走夜路得小心着点,千万不要被蒙了眼。”
郝班长蹙了蹙眉头:“知道了,你们赶紧回家吧。”他揉了揉肚子,又说:“老乡,不知道你们身上带没带啥吃食?弄了一天鬼子的尸首,到现在连口饭还没吃上,有点顶不住。”
“有!有!”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布袋,“还剩下几块苞米面贴饼子,你们都拿去吧,反正俺们也快到家了。”
郝班长谢过他们之后,转身奔着查魔坟的山头走去。我提着火麟食盒紧跟着他。刚走出去十几米远,便听见他们从背后喊道:“八路军同志,记着啊,千万别给蒙了眼!”
由于我是南方人,有时候经常会被这里的方言搞得不知所云,比如“瘪犊子”和“埋汰”这两个词,要不是郝班长告诉我它们的意思,我自己根本就猜不出来。于是我问他:“刚刚那两位老乡说什么别给蒙了眼,到底是什么意思?”
郝班长“嗨”了一声:“这些玩意儿,都是老百姓瞎琢磨出来的东西,说是夜里走进坟茔地会碰到‘挡’。‘挡’是一副看不见摸不着的棺材板子,把你弄进去,四面八方黑糊糊的,不就是给蒙了眼嘛。”
我说:“那不就是鬼撞墙?”
郝班长说:“反正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的玩意儿,刚才你还说啥黑白二爷呢,结果咋样?还不是两个清清白白的大活人。”
我还想再从他嘴里套出一些关于“挡”的段子,将将张开嘴巴,他就把一块苞米面贴饼子塞了过来:“赶紧整两口吧,不然一会儿你连提食盒的劲头都没啦。”
玉米面贴饼子扎得嗓子眼吱呀乱叫,我赶紧从路边抠下一块残冰含在嘴里。饼渣子倒是都咽下去了,可是舌头却被凉得麻酥了。翻过一道灌木矮坡,一片稀疏的黑松林出现在我们面前,松林之下,鼓起的小土包星罗棋布。这些小土包与南方的坟墓大相径庭,全部都没有立墓碑。在我南方的老家,那些没有立墓碑的坟多半被理解为孤魂野鬼。我就曾经听父亲讲过,这些孤魂野鬼常会伺机向过路人要“小钱”,特别是那些身体孱弱的妇孺,所以小时候他是不允许我去这种地方的。
有了先前根深蒂固的禁止,我开始有些迟疑,原本嘴巴里的麻酥也炸满了全身。郝班长看出了我的犹豫,他咧着嘴一脸不屑地说:“德行!还没进去你就吓破了胆,这要进去你他娘不哈喇出尿才怪。”
这些坟墓大半都被残雪枯枝覆盖。通化城百姓的习俗是岁末年初上坟,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家里的男丁穿戴整齐来到坟前焚烧冥纸。我四下观察了一番,发现大多的坟头都有冥纸的余烬,但是有那么十几座却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坟顶冒出雪外的稀疏杂草都没有清理。我问郝班长:“这些没有冥钱收的不会都是孤魂野鬼吧?”
郝班长说:“唉!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活人都顾不来,还哪有心思管死人!”
我们沿着坟与坟之间的空隙七扭八拐,走着走着,郝班长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指着脚边的一座坟说:“不对啊!你快来看这座坟……”
我蹲下身子左瞧右瞅,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我说:“班长,你怎么也变得疑神疑鬼啦?”
郝班长摇头说:“不是,不是,这座坟——咱们刚刚走过。”
一阵猛烈的老北风呼啸扑过,林子里的松木顿时发出啪啪的脆裂声。
我的身子惊起一个寒战,腾地站起身来撤回到郝班长身边。我说:“你的意思是咱们刚刚走过,现在又走回来了?啊!”我没等郝班长回答便尖叫了一声,“咱们现在会不会已经,已经转进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棺材板子里啦?就是你说的那个‘挡’……”
郝班长扫了两眼无比阴森的黑松林,凛冽的老北风似乎停在了这里,拼命地绕在我们周围叫嚣个不停。我感觉全身糊满深寒,它们不仅仅来自摇动不止的松树,更多的是来自那些狭小的坟头。我见郝班长一直不搭话,心里开始七上八下,于是便追问道:“咱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给蒙了眼,是不是?”
郝班长说:“不至于。天有些阴沉,加上这旮瘩又没有路,黑灯瞎火的难免会转悠回来。待会儿再走的时候记着点方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