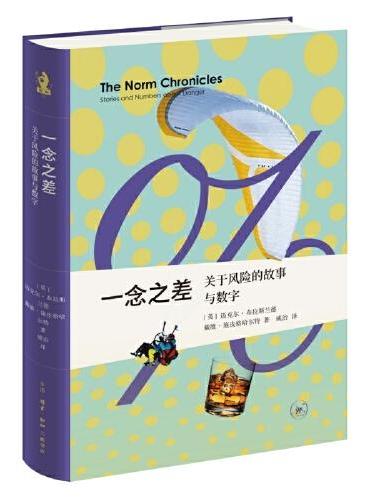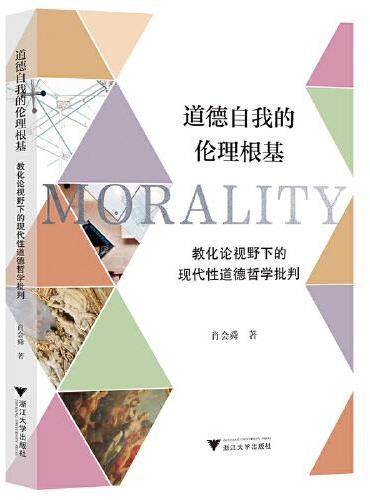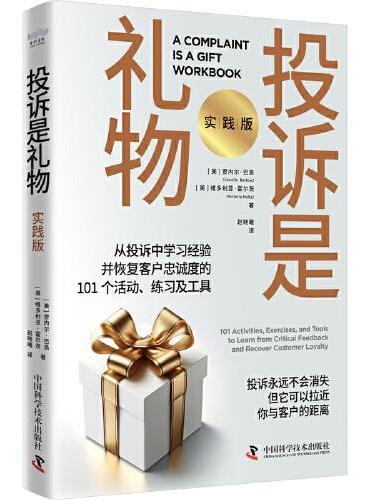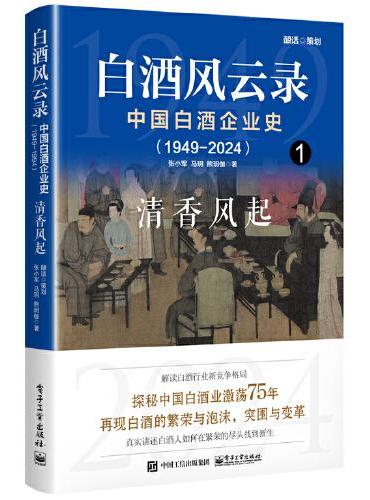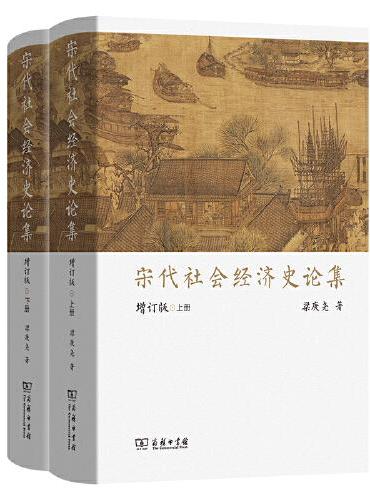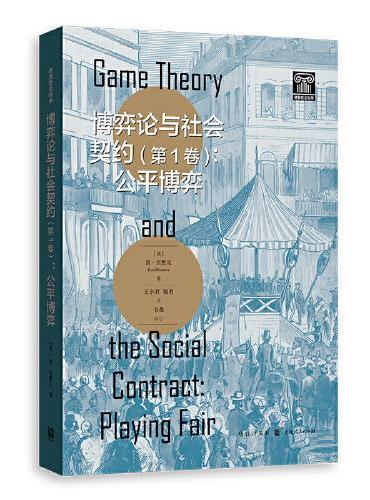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小学生C++趣味编程从入门到精通 青少年软件编程等级考试(C语言)学习用书
》
售價:HK$
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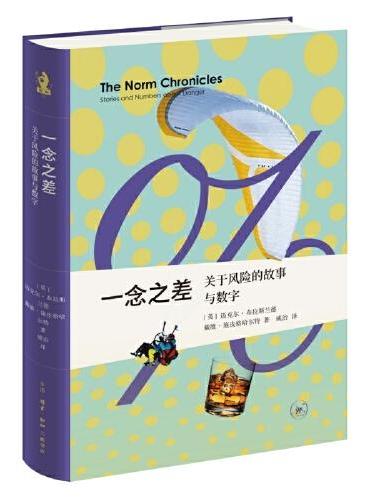
《
新知文库精选·一念之差:关于风险的故事与数字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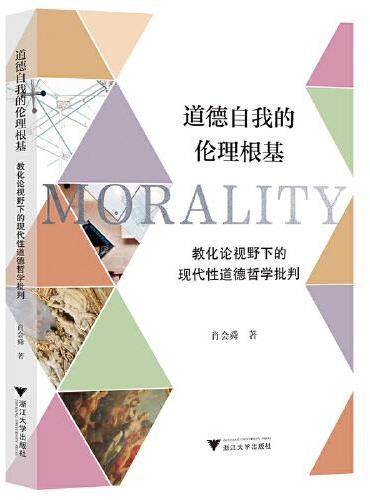
《
道德自我的伦理根基——教化论视野下的现代性道德哲学批判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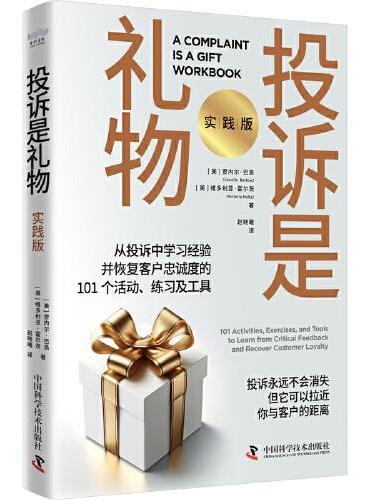
《
投诉是礼物:从投诉中学习经验并恢复客户忠诚度的101个活动、练习及工具(实践版)
》
售價:HK$
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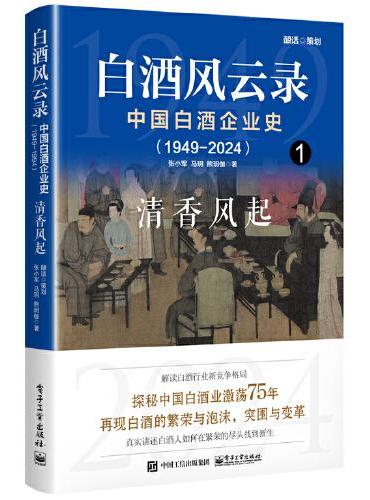
《
白酒风云录 中国白酒企业史(1949-2024):清香风起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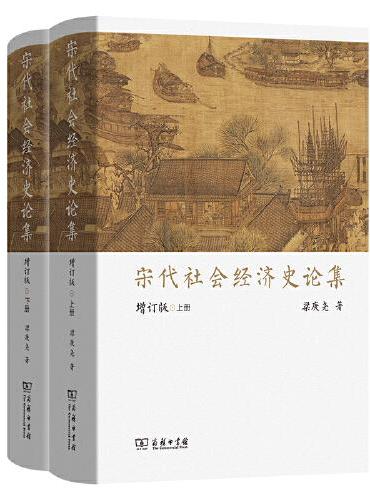
《
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增订版)(上下册)
》
售價:HK$
3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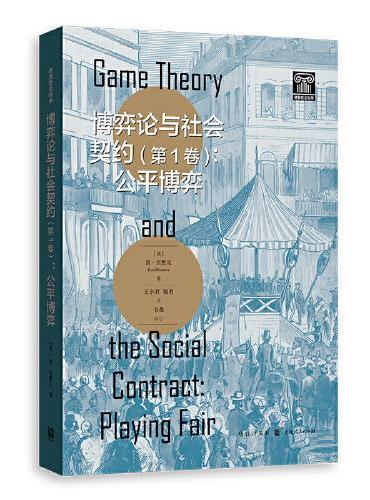
《
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公平博弈
》
售價:HK$
124.2

《
海外中国研究·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
》
售價:HK$
101.2
|
| 編輯推薦: |
张笑天:《东北生死场》以极其传奇的故事,记下了东北人生存、生活的各种场景,读后让人极其感动并难忘。走进“东北生死场”其实也是走进了大东北苍凉的惊心动魄文化记忆。
冯骥才:曹保明先生是东北著名的文化学者,田野考察是他的强项。他写过许多狩猎、捕鱼、打狼、淘金、老作坊等著作,都是田野文化的上品……
|
| 內容簡介: |
|
寻觅地域最神奇之所在,尽在茫茫东北黑土之上,一户闯关东之家来东北寻找生活的出路,却突然发现了自然和生活的奥秘,于是几代人开始了一个无有尽头的追求与梦想。俄国人的狡诈,日本人的狠毒,淘金人的神秘,老二哥的奇特,伪警察的古怪,沦陷区百姓的活法,还有土匪和老烧锅的种种内幕,演绎出一个又一个从来无人所知的故事。小家联系着历史的更迭,传奇行走印证着朝代的变迁,仿佛让人走进了生命与历史的遥远尽头……
|
| 關於作者: |
|
中国著名作家,世界知名的东北文化学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他的大量作品记录和描写了东北生活传奇,几十年来致力于抢救挖掘东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
| 目錄:
|
第一章 你不叫我活
第二章 神泉
第三章 狐仙保佑
第四章 东北少女
第五章 以死抗拆
第六章 死囚
第七章 借头
第八章 本是仇家又结朋
第九章 客栈里的女人
第十章 去头宴
第十一章 露西亚屋
第十二章 小琴和伊万
第十三章 跨国官司
第十四章 日本人来了
第十五章 你死我活
第十六章 神秘的消失
第十七章 女匪驮龙
第十八章 死场
第十九章 新主人
第二十章 头牌
第二十一章 义匪
第二十二章 东北响马
第二十三章 绑票
第二十四章 血匣子
第二十五章 花儿出墙
第二十六章 警长和妓女
第二十七章 1941年的圣旨
第二十八章 东北长寿秘境
第二十九章 老二哥出场
第三十章 小民
第三十一章 恶警
第三十二章 狗日的世道
第三十三章 伊通花落
第三十四章 换血
第三十五章 劫法车
第三十六章 他是东北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你不叫我活
在一般人眼里,提起东北,就是大风大雪,老北风在雪壳里打旋,江河冰冻,野鸡一片片冻死,头扎在雪壳子里,屁股露在外头,村屯人冻得咝咝哈哈的,一大早出去捡。可是如果说热,东北这地方热起来也叫人够受……
这不,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仲夏,春头子一收尾,大伙儿还没感到北方的春意和夏凉,热辣辣的日头就照开了。春起在化雪的荒地上种上种子,小苗刚长起半尺多高,老天就开晴了。这是一种干热闷烦的日子。每天焰腾腾一轮白日,晒得地皮起卷儿。关东驿道上的浮土像热锅里刚刚炒出的面,一脚踩上去直烫脚面子,这种旱天热土最难受的就是种地的。
这日一早,在关东腹地,在伊秃(契丹语,汹涌的河水)河北岸一个叫乌卡拉浩特(蒙语,即宽城子)的地方,从屯子里走出一老一少。这老的年岁约在五十左右,一根长辫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少的约在二十左右,也是一根长辫子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手里牵着驴的缰绳。他们动作长相一模一样,俨然一对父子。真是一对父子。这老的叫齐雨亭,儿子叫齐子升,他们是这窝棚屯的地户。
爹送子出了屯口来在土道旁,他打个遮阳抬头看了看天上毒毒的日头,对儿子交代说:“你快去快回。大伙儿等着写裱呢。”
儿子答应一声,骑上驴就上路了。
老爹望着驴儿扬起的尘土消失在远方,打了个唉声,这才转身进了屯。
原来,自从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灭明起,清王朝便推行了封禁政策,把东北和长白山的大片土地和山林划为“龙兴之地”,不许人采伐和开垦,又因蒙古族参加清王朝的反明战争有功,便把伊通河西北的大片土地封给了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作为领地,并修了一条柳条边,“边外”定为蒙公的游牧地,不准开垦,后来又修了一条“新边”,把其中的一部分划为清王朝的官地,定为朝廷的围场,而乌卡拉浩特一带就成了朝廷和蒙王公都可管可不管的地方。但是,清王朝的封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蒙古王公的抵制,于是早在几十年前,柳条边以西郭尔罗斯前旗恭格喇布坦王爷违背清政府的禁令,私下招募大批来自山东、直隶的流民前来垦荒,使得乌卡拉浩特一带的农垦面积不断扩大,后来竟然扩展到蒙公游牧地和朝廷围场的中间俗称“夹荒”地带,这就是今天的“窝棚屯”一带。
由于一片一片的窝棚就像雨后地面冒出的蘑菇不断地在北方的荒原上漫延,蒙公恭格喇布坦王爷觉得有利可图,便派出负责管地租的“租子柜”王爷按“窝棚”纳税,只要有一伙或一户闯关东来的流民在这儿搭起窝棚安下家,烟囱一冒烟儿,他便领着兵丁来给你造册丈地,收租纳税。可是由于流民和地户也搞不清哪片是蒙公的哪片是朝廷的,因此经常发生垦荒地户刚刚把租子交给蒙公的租子柜王爷,可这边朝廷的税官又来收地税之事。农户真是叫苦连天。所以有如齐雨亭一家,在此搭了些个临时的或较长期的窝棚,手里掐着蒙王公给开的“开垦令”,等着朝廷税官来验收拨地耕种。
窝棚是东北民间特有的一种房子,往往是四根棍子搭成“人”字形架,上面用青草一披,抹上泥皮,靠一侧留门,一侧挖窗,里面砌上卧入地下半尺深的火炕,人们往里一住,也照样生儿育女。但在这种地方生活,冬冷夏热,潮湿难耐。可如今,更难的是老天大旱。这不,一大早,齐雨亭就按照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派儿子去河东的张家纸坊取黄裱纸,回来好叠裱、写裱、烧裱,以求雨。
这窝棚屯处已住了上百户流民,都是闯关东从关内来的人家。屯户窝棚中间是一处挺大的场子,显得宽绰眼亮;场子中间高高地立着一根旗杆,上面飘着一面黄色的锦旗,上书“窝棚屯”三个大字。
旗杆周围的空场子上,一些不怕晒的小孩们光着屁股在玩耍。
他们玩着“老鹰抓小鸡”。一边喊着:
一把火,两把火,
太阳出来晒晒我,
哈哈哈!
在生活中,孩子们总是远离苦难。这不是,今天是五月十三;五月初五端阳节大人给他们编的小风轮,用木杆儿穿的草龙,还有装上香草的香荷包,他们用红线拴上挂在脖子上;还有的手里拿着一小绺艾蒿或小葫芦,有的捧着粽子边吃边玩。而各家的窝棚门口的荫凉处,却坐着三三两两的愁眉苦脸的闯关东流民。
“哎,皇爷稳坐江山!可咱们……”一个坐在窝棚口处的老汉,从嘴里拔出烟杆,望着在屯子场地上玩的孩子,说道:“这些荒,开是开起来啦!可心里老没底。你倒是说清楚,哪儿是蒙古王爷‘租子柜’的,哪儿是皇爷的边!”
另一个靠在窝棚门栅上的老汉,噗嗤一笑,说:“老哥,他们也是说不明白。说明白谁不说?头年,朝阳堡子硬抗荒租,不是让朝廷给打死八十多口子?唉,听天由命吧!”先前那老者抹了一把脸上干热的汗泥说道:“是疖子早晚出头。等着瞧吧!咱这叫几百屯户人的命啊……”
这时,求雨秧歌队开过来了。这种民间的土秧歌是按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组建起来,平时赶在红白喜事或年节出演。而每年求雨活动,则必须出演。按求雨仪式要求,秧歌由二十几个小生荒子(小伙子)组成,他们先由两个小伙子抬着一条草龙,对着龙嘴处有四个小伙子抬着一张桌子,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猪头,一左一右还点着两根大蜡烛。一伙喇叭吹鼓手,手握家伙,随时准备开奏。
这时节,齐子升已来到张家纸坊。掌柜的张大纸匠是在开春就按着徐老三的旨意,把屯子里求雨用的黄裱纸晒好,见了齐子升,张纸匠问:“你爹可好?”
“还好。就是愁哇……”
掌柜的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告诉你爹!”
子升点点头。又说:“都那么说。可朝廷一日不来认准,大伙儿心里就都没准。这可比天旱还要紧!”
张纸匠让小打帮着把黄裱纸抬到驴身上,说:“快回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齐子升说:“纸钱到老秋一块算吧!不能总白取你的。”
张纸匠说:“不用记算啦。这就算我也在‘求雨’。你告诉徐三爷,记上就中。另外,还有啥需要帮的,就知一声。咱一个纸匠,也没啥能水,就是用几张关东老纸呗!”
纸坊的伙计们都送上路口。齐子升又牵着驴儿踏上了土道。
一进屯子,一帮孩子们就抢着喊:“黄裱纸来啦——!黄裱纸来啦——!”
不用通知,各家的人都走出来帮忙。那往往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帮着卸纸,有的帮着叠裱。接着是写裱。
写裱,则要窝棚屯中公认为有“文水”的金大秀才来写。他也是从中原闯关东来的,祖籍河北乐亭。据说祖上三代当过文案。他也晋过公试,没有考上,但大家也称他为“秀才”。金秀才写得一手好字。但求雨的黄裱上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内容,往往就是“龙王来”、“龙王好”、“阿弥陀佛”等等便行。接着就是求雨仪式,称为“烧裱”。
这时,全屯的男人都集中起来,一律脱去上衣,挽起裤腿,打着赤脚,排队走在前边。其中由一位“仪式”执事,手拿黄裱,他喊一声阿弥陀佛,大家都跟着喊。声音哭样的,很苦很低沉。每走到一个屯口、道口、桥边处,就“烧裱”,然后祭者齐刷刷跪下,向老天三行三拜,高喊求雨。这时,跟在队伍后边的秧歌就要把猪头和龙王牌位摆在前面,然后开扭。
秧歌都是传统的内容,什么花扇、推车、高脚子,还有老达子和老蒯抽烟等等,很是热闹。而求雨的人众后面,是一串孩子们跟着跑跑闹闹的。
队伍从窝棚屯出发,直奔伊秃河口处的龙母庙。说来颇有意味。在早,在河的岸边上不知是何年何月,有人在此处建了座“龙母庙”,据说,龙母就是秃尾巴老李的生身之母。说老早年以前,山东文登府有一户人家,姓李,这一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可是从生下来就带着一条尾巴。李老爷子很生气,总也看不上这个孩子。可是当娘的受不了,再说什么也是自己的骨肉啊。
这一天,趁当家的出去铲地的空儿,娘就搂过孩子给他喂奶。
孩子好久没吃娘的奶了,一见娘亲,就卧在娘的怀里,尾巴缠着娘吃开了。
谁知就在这时,爹爹铲地回来了。
他隔着窗户一看,吃奶就吃奶呗,还用尾巴缠着你娘,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放下锄头,进了外屋就抄了一把菜刀。当时,儿子光顾吃奶,也没注意爹冲了进来,只听“当”的一声,儿子的尾巴被剁下一节。
儿子大叫一声,从窗户跳出去,只觉着身子一重,双脚腾空就化成了一条巨龙。这时天空顿时阴黑起来,接着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大雨。老爹一看,儿子原来是一条龙,也吓得扔掉菜刀跪在了地上。
可是,龙儿围着他家的房子转了三圈儿,然后一直往北,来到了吉林的松花江上。后来,母亲捧着儿子的一节尾巴追到了东北。她死后,人们就在这儿给她盖上一座“龙母庙”,每年来祭奠她,并管她的龙儿叫“秃尾巴老李”。据说今天在山东还有一句话,叫“雹子不打文登”,是说秃尾巴老李回文登看娘。一到求雨的季节,这窝棚屯一带的人就到这儿来求雨,这已成了这一带人的习惯。
来在龙母庙前,秧歌队打开了场子。
齐雨亭和几位老人上前烧裱。当纸烟徐徐升起时,全屯人都跪了下来。
这时,齐雨亭领着喊:
求龙母,开开恩,
来片云彩让天阴;
小孩们则喊:
老天爷,
快下雨,
包子馒头都给你!
秧歌开始。什么舞龙,跑旱船,跑驴,串花阵,小燕钻云,真是热闹隆重极了。然后,队伍返回屯。
大家返回窝棚屯,并不能立即散去,因为还有一顿求雨饭,那就是,要由屯子里的大户人家将猪头带回去,用大锅炖上,然后款待所有参加求雨仪式的人们。所以求雨这一天,往往也成为农家最热闹的一天。按着窝棚屯的规俗,猪头被送到举办这次祭雨道场的齐雨亭家,由他家来操执。
齐家于是就开始操备这顿餐食,又抱柴禾又涮锅。外面的场子旗杆下,秧歌队的道具都堆在那里,一些孩子们围在那里边玩边看,求雨的人众都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老天,等着开饭。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不好了!朝廷的税官来查验‘开垦令’来了!你们看那是什么?”
这一喊,屯子里的所有人都静下来,大家齐向远方望去。
人们往东南一望,就见远处的荒地上朦朦胧胧地腾起了一片烟尘,还有“哒哒”的马蹄声,那是一些马匹疾速地朝窝棚屯这边奔来。
马蹄击打着垦荒地户的心,尘土飘飞起来,遮住了天空的太阳,人们吓得跌倒爬起地四散奔回自己的窝棚,转眼间窝棚屯场子上就空空的了。
不一会儿,三十几个骑马的人就来到窝棚屯的空地上。为首的一个官人模样的大汉从马上跳下来,对手下的一个人说:“去,把窝棚屯大爷给我叫来!”立刻有人“喳”地回了一声走了。其余的人给这人放下一个马凳,头上撑开遮阳的紫缎罗伞,在他面前摊开一条长桌,三册厚厚的账本和一个红漆的算盘“啪”地就摔在桌子上……
这时,朝廷的收租税兵已押着窝棚屯大爷和几个户里屯头快步走了过来。
窝棚屯的屯爷是徐老三,那年已七十二岁。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坎肩,一部雪白的山羊胡子飘洒在晒得紫黑的胸前。徐老三本名徐宝忠,祖籍河北沧州,家里开过镖局,因给一家大烧锅当护院“院心”不幸被人放火烧了酒作坊而倾家荡产,不得不领着儿子闯关东来窝棚屯落脚,又被众人推举为“屯大爷”,掌管着乌卡拉浩特窝棚屯几百户地户的身家性命。
见了朝廷税官,徐老三抱拳施礼,跨前一步说:“不知官爷光临屯堡,老三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这次朝廷吉林将军派来的税官姓胡名奎,此人本是朝廷武官之后,因精通一些拳脚,平时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现在有朝廷公务在身前来收缴地租便更是飞扬跋扈,他瞪了一眼徐老三命账官打开地册说:“老头,又有多少新来地户?”
徐老三说:“回秉老爷,二十四户。”
胡奎说:“让各窝棚把地租算齐。”
徐老三说:“什么地租?”
“私入本地租种夹荒地地租。”
徐老三说:“胡爷,这二十四户地租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就被蒙公‘租子柜’收走了,我们闯关东开荒的都不易,也不能种一块地交两次租子呀……”
胡奎也不回徐老三的话,只是命账官加在一起算总账看看。那账官手托算盘噼噼啪啪一阵细打,唱道:“二十四户总地租白银贰万伍仟肆佰两陆文……!”
徐老三又顺怀里摸出一张二十四地户交蒙公租子柜地租的开垦令纳单双手托给胡奎说:“这里已有如实清单,请官爷过目!”
胡奎伸手夺过纳租单,看也不看,“喳喳”几下把那纳单撕个粉碎,向空中一扬骂道:“大胆!我奉朝廷乌拉衙门前来收缴地租,我不管你交给谁,首先你得交给吉林乌拉租税!你如有意抗租,我就平了你这窝棚屯!并把你押到朝廷过堂!”
徐老三不动声色,又和言细语地说:“胡爷,农人种地又都不易,就是纳租,也得等到了秋天,粮豆下来,卖粮纳租如何?”
胡奎早已不耐烦了。他“啪”的一拳砸在桌子上,那张账桌“哗啦”一下子碎在地上。胡奎怒声喝道:“把这老家伙给我捆起来……”
立刻上来几个清兵把徐老三捆个结结实实。徐老三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交你双份租子!”胡奎说:“那我就先打死你。”说完他一拳下去,打在老汉的后背上,徐老三大嘴一张“哗哗”地顺嘴里喷吐出两口鲜血……这时窝棚屯里突然响起“铛铛”的锣声,胡奎惊恐地向四外一望,只见有上百条汉子,一个个光着膀子,手里握着二尺钩子、镐头、铁锹什么的农具嗷嗷地喊叫着朝这边涌来。
这真是作贼遇上打杠子(也是贼)的了。原来,那些求雨的秧歌队,人也没散,现在一看,官兵把人逼到这个份上了,就围了上来。
齐雨亭一见事态要大,就暗中嘱咐儿子:“快去纸坊搬人马来。大家集中,人多也势众!”儿子急忙去了。
见人马围上来,徐老三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突然对大家说:“慢!”
大伙儿顺势停下来。
徐老三对胡奎说:“胡爷!现在你改变主意还赶趟,不然后果可不好收拾!咱农人前两年也闹过。”
胡奎说:“老三,你想犯上?”
“庄稼人,被逼无奈!”
“你想作乱?”
“是为了土地……”
胡奎说:“都给我退下!”
可是,窝棚屯的男女老少都不动。一个个拿着钩杆铁棒,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官兵。
胡奎一看,垦荒户们不撤,于是心中发乱发慌。但是,他表面上强硬。
胡奎自作镇静地说:“不要慌!这帮不要命的蛮荒地户,竟然敢抗上作乱,给我往死里打!”说完,他把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儿,一口叼住辫梢儿,说:“上!”
官兵们打押百姓平时就早已是家常便饭,现在听到了胡奎的命令,一个个操起刀棒直向窝棚屯的地户们劈来。
欺人已欺到家门口来了。徐老三再也不能犹豫了。他对齐雨亭等乡亲们喊:“打吧!乡亲们。不然咱该吃亏啦!……”
他的话一出口,垦户们疯了一样上来了。
其实,这些穷苦的地户们从出了山海关那一刻起,他们就早已把“脑袋瓜子”别在了裤腰沿子上了,生死对这些走死存亡的“流民”来说已不是重要的了,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种点地,吃饱饭。如今,这一点点最起码的人生之要求也不能达到,他们还怕什么呢?还惧谁呢?于是,在徐老三一声令下之后,他们操着家什,扑进官兵之中就对打起来。
窝棚屯的女人和孩子们也参加了。
是啊,男人们已拼上了,上吧。于是,女人们也操起木棒什么的,小孩们拿土疙瘩、土块子,也打官兵。
可是,这些官兵个个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对付这些农人,那是绰绰有余。就在百姓有些招架不住时,齐子升领着的乡下纸匠们赶来了。农人们又从地上爬起来,一个个红了眼似的和官兵厮打起来,拼着老命厮打起来,在旱天热土的荒原上,乌卡拉浩特的土地上腾飞起尘烟和血光,一片刀具相撞的格斗声震耳欲聋。那些清兵虽平时训练有素,但眼下也渐渐架不住红了眼的上百农户,恶斗从头午直打到下晌,清兵拖着十几个伤号撤离了窝棚屯,屯大爷徐老三也被众人抬回了窝棚。
第二章神泉
这天夜里,窝棚屯十分不平静。
家家都有被官兵打伤的伤号,哭声、呻吟声、叫骂声从一处处低矮的屋子里传出来。
月亮,从伊秃河上升起来,高高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之上,把清冷之光洒向了这苦难的北荒屯子。
在中间一处窝棚的土炕上,屯大爷徐老三脸色纸白地躺在那里,他大口地喝完一碗黑糊糊的汤药,然后把碗放在炕沿上,对一直站在一旁的儿子徐长友说:“去,快去把你齐大叔找来……他外号‘齐大算计’,我得和他好好算计算计日后!”
儿子出去了。
齐大算计就是齐雨亭。他本是河北永宁府人,两年多以前结伙闯关东来这伊秃河北岸落脚垦荒,早已属于蒙公租子柜的地户。说他“算计”,是指“会过”。其实农人谁不会过,只不过他“会过”已到了“出奇”的地步。据说那年他从关里家出发,娘给他煮了一只咸鸭蛋让他路上带着吃。他从二月二出发,每天用席篾棍儿抠一块就饭,从二月二直到秋天的八月十五这天才露出蛋黄来!
不知此事真假,从此地户都叫他齐大算计。其实他人善良、刚直、有计谋。
这时,儿子领着齐雨亭走进屋来。只见他的胳膊已经错环反背着,左胳膊弯处一段白骨已支出肉皮之外,疼得直咧嘴。这还是下晌齐雨亭因见屯大爷徐老三被捆,情急之下便领着众地户一起挥动铁棒和官兵格斗,由于他出手专门打清兵的马腿骨,这才打跑了清兵,救下徐老三,可他自己因此也受了重伤。
“三爷,疼吗?”齐雨亭问候着。
徐老三说:“你咋样?”
齐雨亭说:“这不,支支着,就是回不去。”
这时徐老三说:“儿呀!你快扶我坐起来……”然后又对齐雨亭说:“你转过身去。”
齐雨亭不知何故,乖乖地刚刚转过身去,就觉得脑后飞来一股凉风,接着一只手掐住了他的左胳膊,他只觉得胳膊一阵麻痛,又听“咔叭”一响,折骨已经对上。
齐雨亭惊讶地说:“三爷!你还会接骨?”
徐老三说:“我何止会接骨。你看着……”只见他从一个小匣里摸出一个小瓶,里面是黄黄的一下子水,他拧开瓶盖,一股浓浓的酒味儿飘飞出来。他用指甲在里边沾一点儿,在齐雨亭的伤胳膊上一抹又一撸,转眼间红肿顿消。
齐雨亭惊奇地说:“这是真的么?”
徐老三问:“如何?”
齐雨亭说:“奇了。这是什么神水?”
徐老三的儿子徐长友说:“这不是什么神水,这是俺爹在早在人家大烧锅护院时,跟人家烧锅掌柜学着酿成的一种‘酒母’。酿此酒,必须有绝招……”
老爹说:“有绝招,还要有绝水,一般的泉子不行。雨亭啊,这瓶药酒就留给你吧。以后这边的事,你就多照顾了!”
齐雨亭说:“三爷,你们……”
徐老三说:“我就是找你来核计核计后事。”
“后事?”
“对呀。雨亭啊,你想想,官兵这次没收去租税,他们能善罢甘休吗?定然还会来找窝棚屯的麻烦。所以我想今夜我就领这二十四户没有垦荒令的人走。这样把麻烦也带走了。”
“走哪儿去呢?”齐雨亭担心地回问。
“往北,往蒙王公租地的地界那边挪一挪。那边有个叫乌兰塔拉的地方,有我以前来闯关东的一个本家,我们投靠他去。”说着,徐老三就让儿子快收拾东西。
齐雨亭心下感动,他“噗通”就在炕沿前跪下啦:“三爷,这一途多保重!”
徐老三下了炕,也动情地说:“我命大,死不了!”
听说徐老三要走,各处窝棚的人众都出来相送,那二十四户也要随徐三爷一起出发。大家在屯中央的旗杆底下抱头痛哭,互相安慰告别。之后,徐三爷领着这伙人在月光照耀之下,往北方走去了。
一晃,十来个年头过去了。
这期间朝廷已在伊秃河上源的洛家哨一个叫长春堡的地方建了长春厅,就是为着处理地户和蒙人“租子柜”之间的矛盾,也为着解决地户垦民和朝廷收租人的纠纷。但这个长春厅衙门离着窝棚屯太远,有一回,衙门来俩差役,押着齐雨亭去府衙“对地账”,来来去去走上两天,而且道路泥泞,不便行走。而远离长春厅府衙的乌卡拉浩特一带却渐渐地多起了住户。
这一是因为,自从徐老三这儿的垦地户和官兵为“夹荒”决斗,事儿闹得不小,徐老三走后,朝廷又来过几次强收地租,可是胡奎一直没有露面,领人“闹事”的徐老三也蹽了,双方“当事人”都不在。二是这期间,朝廷和地户之间如矛盾日渐加剧,清廷也怕引起更多人众的反对,于是便下令暂缓处理“夹荒”地租事宜,这样,乌卡拉浩特一带的垦民地户便暂时平静地种起夹荒地来。
这一年初夏至老秋,老天又是闷热。
这日晌午,就是北方民间所称的秋傻子那种时候,齐雨亭正领着儿子在开荒翻秋垄。爹在前边,儿子齐子升在后,由于庄稼棵子和荒草都挺茂盛,不一会儿,儿子就看不着爹的影了。在前头抡镐开荒的齐雨亭举镐刨着刨着,突然“咕咚”一下子,掉进一个水洞子里去了。
齐雨亭一惊一吓,高声喊叫:“子升!快救爹……”
话没说完,那水洞子的水已淹了他的脖。
儿子一听爹喊救命,扔下镐头撒腿就往前边跑,边跑边喊:“在哪儿!在哪儿!”
可是,几句话没说完,他自觉得脚下一陷,也落进去了。原来,这儿是一处暗泉子,水深不知底,因有树木和草丛的遮掩,加上草皮上风刮来的一些浮土一掩,平时不易被人发现。
儿子落入水中,本能地抓住水洞子边上的蒿草,想去拉爹,谁知一看,爹不但没事儿,还脱掉了破布衫儿,在水里连游带洗呢。并说:“小子!先别上去,咱爷俩泡一会儿吧。挺凉快。怎么,我觉得身上的烂疤一挨这水,咋就一点儿也不痒了呢……”
原来,由于乌卡拉浩特窝棚屯一带的人常年住在又湿又潮的窝棚里,加上开荒种地蚊虫叮咬,许多人身上都长了一层层的癞,白天太阳一晒或汗水一浸,浑身发痒,又火辣辣地疼。可是这种病,一没钱请大夫,二没有特疗药,平时痒极了,垦户们就抹锅底灰。
儿子也热一天了。这一落水,浑身的暑热顷刻间消失了。方才他听爹这么一说,也有同感地说:“爹,这水怪呀……”
爹说:“咋个怪法?”
儿子说:“我浑身的脓疤,一点儿也不疼了。”
爹多年走南闯北,经多见广,预感到他们遇上宝水了。他猛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对儿子说:“小子,你往水底扎个猛子探探,看看是不是有泉眼。我咋总觉着这水往起涌呢……”
“好!”
儿子答应一声,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约摸过了半袋烟的工夫,儿子齐子升嘴里吐着水泡浮上来,连连叫道:“爹!这里有个大泉眼,水像开锅似的,咕嘟咕嘟往上冒,而且清亮透顶。我从底下往上瞅,连太阳光和树影都看得一清二楚。”
“真吗?”
“嗯哪!”
“小子,该着咱们老齐家祖坟上冒青烟啦。我看这是个好兆头。”
爹儿二人洗够了,爬上来,又用蒿草和树枝子草皮子把泉眼盖起来了。
一连三天,爷俩开荒干活累了,就跳进这洞泉眼里洗澡,浸泡,还拎回一罐子回家……
接着,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几天之后,爷俩身上的烂疤脓疮就像泡沫一样,先是去疼,然后发白,接着一层层自然脱去,而且不疼不痒,毫无感觉,从前的烂处随着便长出了光滑的皮肉。爹大吃一惊,说:“小子,这是一眼能治病的泉子。干脆,咱们把窝铺搬到这儿来吧!”
几天之后,齐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眼泉的边上支架起一个窝棚,全家人搬过来住下了。
话说老齐家发现了“神泉”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传俩俩传仨,七十二个传十八,不久便一下子在乌卡拉浩特一带传开了。窝棚屯的许多垦户往往也不惜走上十里二十里的专门上这儿来洗澡,有的干脆也搭个窝棚搬到离泉子不远的地方住下。于是不到一年的工夫,泉子周围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屯落,人称齐家窝棚。
这其实就是宽城子今长春头道沟长白路以南,黑水路以东一带地界。
为了让乡里乡亲的生活和使用泉水更方便,齐家爷俩一商量,干脆挖出一个池子,引些水给垦荒户们洗澡和饮用。儿子心眼好使,加上那年秋天夹荒地庄稼又大丰收,齐家院子里堆满了金黄的大豆,儿子就和爹商量,有这么好的泉子,咱们还种什么地了,东北的老乡和闯关东来的人都喜欢吃豆腐,不如开上一个豆腐坊,专门做豆腐……
爹听儿子一说,连连点头说:“小子,爹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爷俩立刻动手,现脱坯、垒院套,又去南大望买来二盘水磨,去蒙古草原挑来两头上好的小黑走驴,买来十几口大缸什么的,赶到冬天打完场一上冻,“齐家豆腐坊”便开始拉磨了。这齐家豆腐坊一开工就与众不同,大院套门口的一棵老歪脖子树上挂着一片豆腐包布子,离老远就能看见,走近了,又能从那布子上面嗅到浓浓的豆腐的酸香味儿,这就像齐家豆腐作坊的“幌子”一样,又像一面黑土地上高高飘起的旗子,在向世人昭示着那千百年来闯关东之人的中原子孙已经在北方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安营扎寨了。
齐家豆腐一下子在“夹荒”出了名。
无论是大豆腐还是干豆腐,筋道、肉头、好吃。吃上就上瘾。
这是咋回事呢?吃一回想二回?这豆腐里掺什么“仙药”了吗?
常常有蒙公“租子柜”的大车千方百里地赶来,就是为了称上几斤“齐家豆腐坊”的豆腐,好回去炖肉过年。
每天早上,齐子升早早地起来,摸黑把驴套上,两盘水磨开始拉豆子。等他把一大锅浆子烧开,老爹再扎上围裙,开始“撇缸”和“过包”……
豆腐坊这行当撇缸和过包都是技术活儿。豆腐老了嫩了,全靠这两道工序的手艺。由于这爷俩精通做豆腐之道,那浆水浓度、火候都掌握得十分地道,常常是豆腐还没出锅,门口的土道上各屯子、窝棚的人早都等在那儿了。
更有人认为吃上一顿齐家豆腐坊的豆腐就是孝敬老爹老娘的举动;常常有这样的事,头三五天就有屯邻的乡亲赶来“订货”说:“来两板大豆腐。后天早上用。”
“办喜事?”
“不是,是俺娘过大寿……”
还有人起早贪黑地赶到齐家豆腐坊,为的是舀上一葫芦瓢热浆子,用棉袄一捂,快着端回家去给生病的老人喝。
往往说:“爷爷,快喝。”
“什么药?”
“不是。这是齐家豆腐坊的热浆子。”
“快!快给我。”
于是,有病的老人往往接过葫芦瓢“咕咚咕咚”喝起来。只要喝了齐家豆腐坊的热浆子,生病之人转眼之间,万病皆无。
人们也感到惊奇,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年,这一带的垦户们还都不知道,以为齐家的豆腐里边掺什么灵丹妙药了呢。其实,就连齐雨亭和儿子齐子升也不完全明白,这一切皆因这眼泉的水奇特。
其实,当年宽城子(乌卡拉浩特)地下出现这泉子也并不奇怪。据史料记载,我国从前著称于天下的名泉有一百二十多处,分布于我国的几条主要地下水带上,其中不少泉子令人兴味盎然。比如四川广元县的龙门山上,有略受振动就马上蜷缩而且倒流的“含羞泉”;云南西部苍山云弄峰下,有蝴蝶于树上首尾相衔的“蝴蝶泉”;还有流于河南睢县城南地下的一眼“香水泉”;贵州安平县城西,有游人在泉边击掌,水中即跳水泡,而且粒粒水珠亮闪闪的泉子,人称“珍珠泉”。而宽城子出现的这眼泉子,便是这一百二十座名泉之一,当年土名叫“夹荒泉”。
这夹荒泉的主要特色在于其水质的特殊甘凉。从前,古生代的长春地块主要是石炭系和二迭系的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岩组成,经过古老的海西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劈理和断层构造裂隙十分发育,长期的风化带网状裂隙运动之后,形成了一处处基岩裂隙水泉,直接连通各个岩层导水洞,科学上称之为“富水带”,而民间老百姓则称为“水线”。齐雨亭爷俩发现的泉子,正是长春最典型的地下“水线”甘泉,内中含有锶、锌、铁、锰、钙、硒、锂等对人体有医疗作用的元素。且冬暖夏凉,口味纯正,水质良好,清澈透明,人洗了不但能治疗疙瘩、疖子、疮,人喝了还能治跑肚拉稀。
一晃又是十几年的光阴已经过去,齐家豆腐坊的生意已经做大,齐子升也娶妻生子,豆腐坊也由原先的窝棚改成了泥坯大户。而齐家窝棚这一带,又被人叫成齐家街了。
每天早上,从前的屯口,变成了街集。
天还没亮,一伙伙赶早集的人就从四面八方往这儿赶着。他们人背、马运、驴驮,把地里的新鲜时令蔬菜,什么豆角、香瓜、西瓜、角瓜、土豆、茄子、青椒、萝卜,新新鲜鲜,顶花带刺地运了来;还有各种粮食,包米、绿豆、大豆、小豆、云豆、荞麦、黄米,还有压好的各种面子,真是应有尽有。然后是占卧子。
占卧子,就是摆卖位置。
其实,大家都是“老熟人”,你在哪个位置上,他在哪儿挨着谁,都有数。一有谁没来,往往挨着的就捎话:“大辣椒媳妇坐月子啦。”别人会热情地问:“丫头?小子?……”“生个千金……”
还有的,来一位生客,往那儿一摆,说:“大爷大娘,给个方便。”这时如果有空位,大伙儿也会说:“放吧。大荒地,有地场。哪个屯的?”哪哪的,一说,都不远。
古语说,有人便有集,有屯便有市。而其实,有集人才越来越集中居住。集,就是大伙儿往一起聚,可能城镇、省市、县社,就是这么形成的。
这时候,长春县的县官毛了,他这衙门还设在洛家哨远离齐家集一带,大事小情也多有不便。于是,当时任长春县知事的张书翰便给上司修了一书,内称“署内地势洼下,每值夏令,淫雨辄浸入室内,潮湿之气终年蒸腾”。又说了,这儿不但远离集市,而且差役人员无法办公,甚至文卷、票据、存根等文档都无法储藏,请迁盖新府衙。
档室漏雨,本属人之常情,可这一“上奏”被准,可也就改变了历史。就在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府衙真的从长春堡(新立城)一带迁至大经路(今大经路小学)一带,也就是当年的乌卡拉浩特的中心街镇。
那时,齐家豆腐在集市上有固定“格子”,每天,齐家人用驴车拉上豆腐到了他的市段,早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候,“齐掌柜?豆腐热不热?俺娘把葱花酱都炸好了。”“喂,干豆腐带来没有?”“这一板可是俺订的。”对种种乡音,齐家人是一一答兑,个个让人乐意。
每天上一回集,家人便有一种长进,也仿佛对生活有了一种信心。这皆因这泉啊。
这年的正月初六。
刚刚过完大年,齐家还沉浸在大年的气氛之中。头晌,吃过了早饭,齐子升想,得过爹屋里,和他商量一下初七开碾子做豆腐的事。
一推门,看见爹正给乐毅像上香呢。
这乐毅,传说是豆腐作坊的祖师父。据说在从前有个孩子叫乐毅,对爹娘很孝顺。爹娘老了,牙口不好,吃不动饭食,他就用牙把豆子什么的磕碎,嚼烂,留给爹娘一点点地吃。有一回他要出远门,就给爹娘嚼了一桶豆浆子。谁知他走之后,爹娘反而舍不得吃,给他留在桶里,这些豆浆就都“发了”,偏巧一个邻居来借瓢舀卤水,用完后,娘把瓢又扔在了桶里。儿子回来后一看,喝!他嚼的豆子,都成了一块一块的。他舍不得扔,抹上点酱一吃,挺香。这就是豆腐的来历……
从此以后开豆腐坊的都供奉他。这叫“有祖而尊”。
齐子升也走上前来,拜过了“乐毅”老祖。说:“爹,按常规,咱们还是初七开磨?”
齐雨亭说:“子升你坐,爹和你商量个事。”
儿子子升坐在爹的火炕上。
齐雨亭点上一袋关东蛤蟆头老烟,狠狠地抽了一口,又把浓浓的白烟吐出去,问:“子升,你说咱家咋是越过越好?”
儿子愣了一下,说:“爹,还不是自从发现了这泉子。”
齐雨亭点点头。又问:“从前,咱这夹荒一带荒无人迹,可现在,屯子越来越多,大道上整日车马不断溜……”
儿子说:“还不是因为有了这泉子。”
“人一多,道一广,这不是,就在几年前,连宽城子衙门都搬过来了。”
“这都是奔这儿来的。”
“子升,兴许以后这里说不定还会变成啥样。所以我觉得……”
“你咋想的,说吧,爹!”
“咱光开豆腐坊?”
“那,还能干啥?”
“这泉子水这么好,光开一个豆腐坊,太白瞎了。再说,豆腐这玩艺,做出来只能现吃,又不能久留,还无法大量外运……”
儿子一下子明白了。爹是想再干点别的。
“爹,你是说使用这泉子,再开个别的买卖?”
“对。”
“泉水能开什么买卖?难道是想开个烧锅造酒不成?”
“对呀!子升。”老爹对儿子的聪明很是高兴,“你想想,这水别说是造酒,就现在舀上瓢一喝,都赶上头度老酒清凉甘甜了,别说再经过粮食一酿……”
儿子也乐了,说:“爹,这个主意好是好,可这酿酒不像做豆腐,没有像样的人指点,恐怕开不成烧锅。”
爹“嗯”了一声,却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齐雨亭说完就上了炕。
炕里放着一张老式炕琴。这还是娘活着的时候爹找邻窝棚屯的崔木匠给打的。自从娘于五年前过世后,子升娶妻自己在西屋过,爹就一个人守着这架老炕琴在东屋一个人住。东北的炕琴,松木红漆,贴着琉璃画,很古朴。
爹慢慢地摸到炕琴前,打开上面金黄发亮的老扁锁,从里面拎出一个红漆小匣来。原来这是娘的遗物,是她老人家的梳妆台。这还是闯关东那一年,奶奶的遗物,让爹背到了东北,爹娶娘时用着,如今爹还保留着。打开了已掉了一半漆色的梳妆台,爹从里面摸出一个刷着黄色油彩的小玻璃瓶来,问:“子升,你还记得它吗?”
“小瓶?”
子升接过爹手里的小瓶子,左看看,右看看,突然惊喜地说:“爹,这不是窝棚屯徐三爷从前送给你的吗?这里装的药酒,专治奇伤怪病……”
爹说:“是啊!一晃快二十年了。用完了药酒,这小瓶我又舍不得扔!”
“爹!你是说徐三爷从前给大烧锅护过院,咱们开烧锅找他帮帮忙,对不对?”
齐雨亭说:“小子,你一刻也别耽搁,明天就走,去请你徐三爷来帮助咱们开烧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