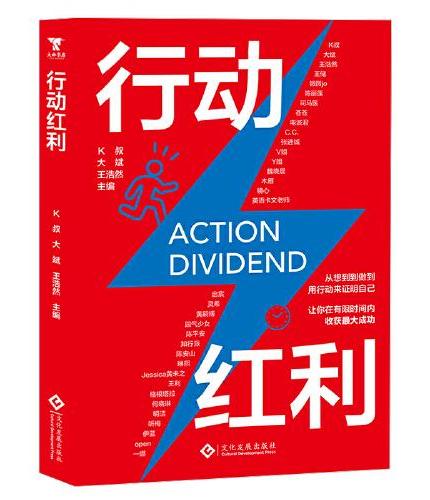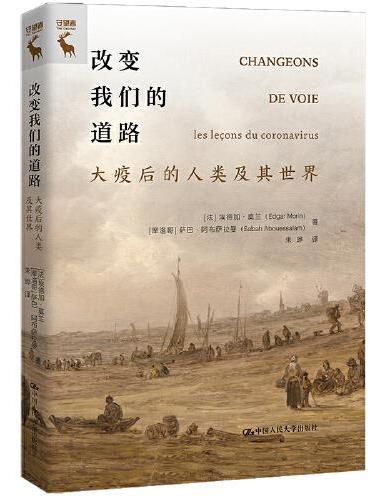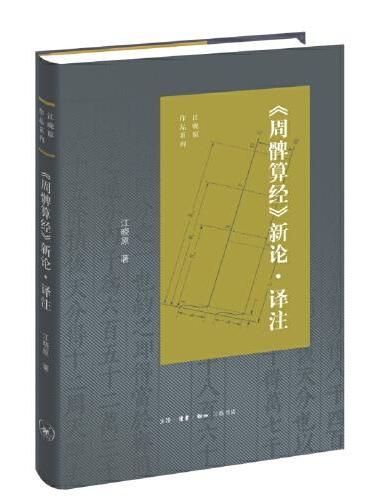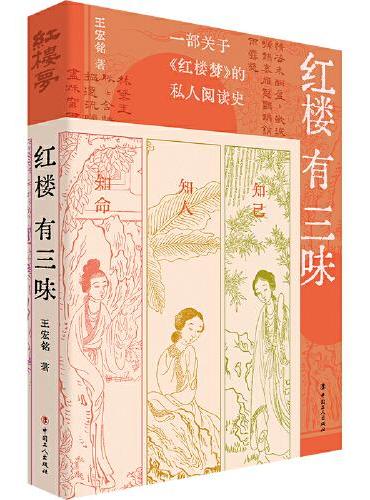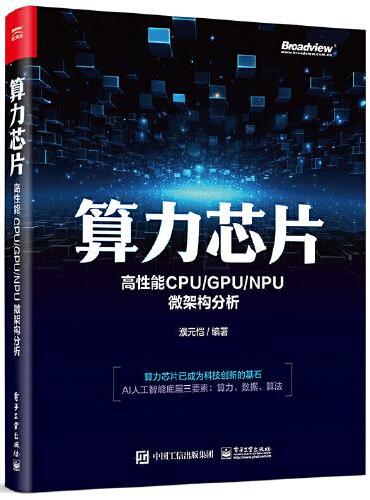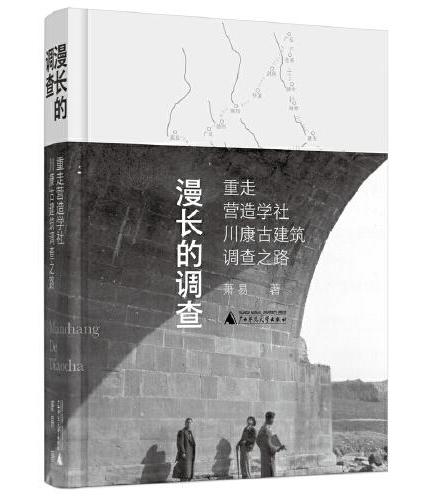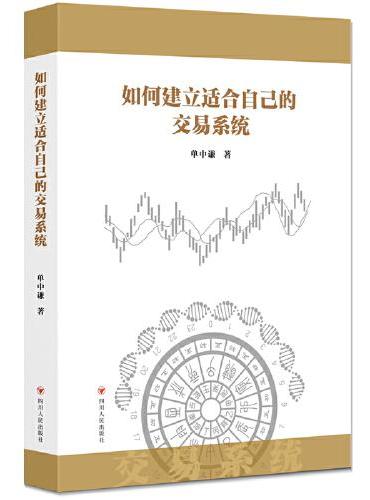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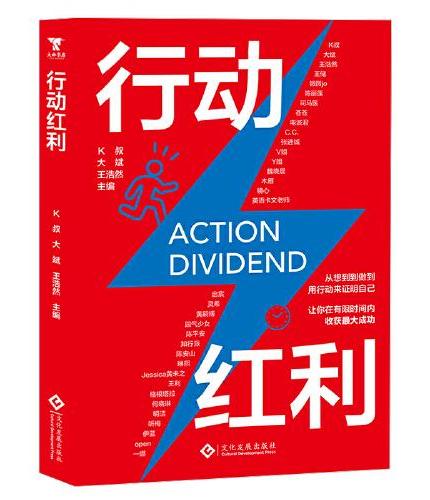
《
行动红利:用行动告别低效、摆脱拖延,享受人生的红利
》
售價:HK$
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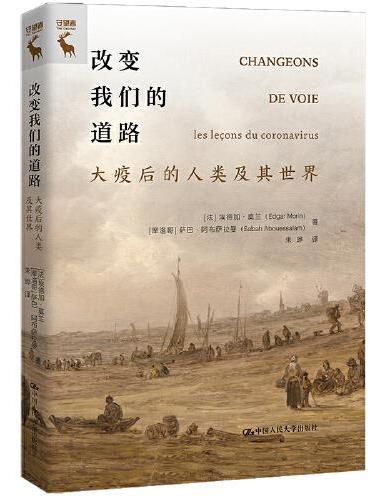
《
改变我们的道路——大疫后的人类及其世界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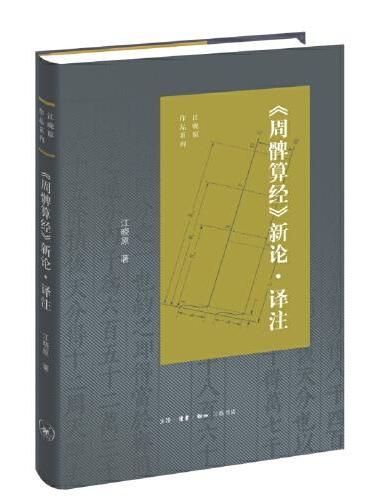
《
《周髀算经》新论·译注
》
售價:HK$
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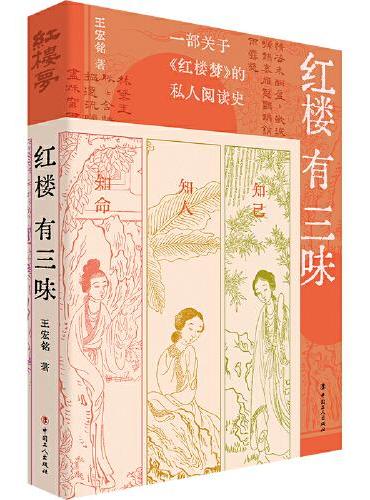
《
红楼有三味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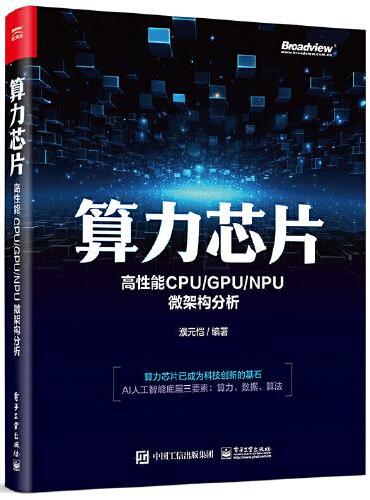
《
算力芯片——高性能 CPU/GPU/NPU 微架构分析
》
售價:HK$
14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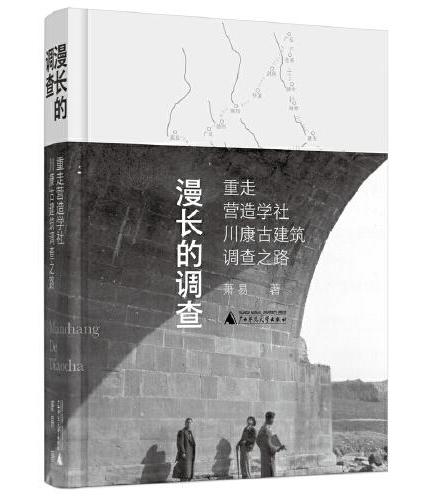
《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
售價:HK$
89.7

《
历史的温度1-7(典藏版套装全7册)
》
售價:HK$
68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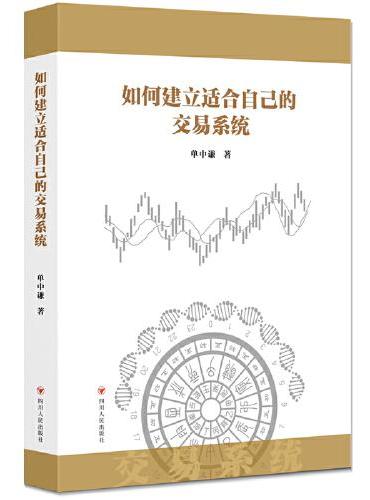
《
如何建立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一本金融初学者建立交易系统的实用工具书)
》
售價:HK$
66.7
|
| 編輯推薦: |
莫言、王蒙等十位文学大师和名家,从各自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方方面面,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
通过本书,读者既可以更多地了解每个作家,了解到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引领读者透过更多视角来领略文学的魅力和精神所在。
|
| 內容簡介: |
|
《文学大家谈》由莫言、王蒙、余华、贾平凹、周国平、苏童、韩少功、林少华、叶兆言、侯文咏,十位文学大家在“文化周末大讲坛”上的讲演记录组成。作家们轻松又不乏深度地侃侃而谈,聊的不仅是文学,也关乎文化时政和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是什么事,哪些人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让我们来一窥大师是如何养成的。
|
| 關於作者: |
莫言、王蒙、余华、贾平凹、周国平、苏童、韩少功、林少华、叶兆言、侯文咏等十位文学大师和名家,都是在各自的文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东莞市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成立于2007年1月,是文化周末系列工程之一。秉承“用声音传递文化,用文化丰富生活”的主题思想,大讲坛结合东莞本土文化现象及需求,采取单人演讲、双人对话、三人沙龙等不同形式,内容涵盖文学、音乐、影像、收藏鉴赏、城市文化等领域,为名家了解东莞和东莞市民亲近名家提供了途径。六年多来,大讲坛已成功举办五十多期,汇聚了国内及港台近百位知名文化名家,成为享誉广东珠三角地区的高端文化讲坛。
|
| 目錄:
|
文学大家谈
目录
| 王蒙
红楼梦中的政治
| 莫言
文学照进人生
| 叶兆言
被注定了的文学
| 余华
文学给了我什么
| 周国平
追寻教育的灵魂:人文精神与教育
| 贾平凹
文学文化漫谈
| 韩少功
生存、生活以及人文重建
| 苏童
一个人的战争:我的文学与电影
| 林少华
夜雨书灯——兼谈王小波、史铁生和村上春树
| 侯文咏
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
| 內容試閱:
|
文学照进人生——莫言
我和马尔克斯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对我这样称呼:“中国的马尔克斯——莫言。”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称呼,我就是中国的莫言,为什么要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当年大家这么说我很得意,这两年年龄大了,脾气也大了,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一点也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关系,这也是一种很尊敬的称呼,因为马尔克斯也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作家,我们读过他的书,也是他的弟子。有的人不愿意承认,有的人羞羞答答地承认,而我一直是非常坦率地承认,我曾经受过马尔克斯很深的影响。
北京有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合法出版的马尔克斯的书,以前都是属于盗版的。中国是1992年才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的,在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之前,外国出版中国作家的书是不需要和作家事先商量的,外国作家的书中国也是可以随便出版的。马尔克斯1973年来过一次中国,他看到书店里摆了很多自己的书,而他没有得到版税,他当时很愤怒,扬言在他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跟中国谈版权的问题。
但是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出版商也慢慢变得财大气粗。关于马尔克斯版权的问题,有很多出版商一直私下里和马尔克斯的经纪人联系,尽管马尔克斯要价非常高,但连老马这样曾发下了那样咬牙切齿的誓言的人也顶不住金钱的诱惑。据说那家出版公司以一百五十万美金买下了马尔克斯的版权,但是这家出版社的人对这个消息不否定也不承认,到底他们是用多少钱买下了一本书的版权,这也是一个谜,我们也不用探究。
我参加了《百年孤独》的首发式,其实当时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我知道去了以后必定要谈到自己和马尔克斯的关系,而谈这个关系时讲话的分寸很难把握,太谦卑也不太对,太狂妄也不对,很费周折。
我当时告诉记者们,我在2007年才认认真真地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2008年我受到邀请参加一个在日本开的国际笔会,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但对方说马尔克斯也会去,我就立刻说我去。我想日本人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了,但在受邀请的时候还没有把《百年孤独》读完,所以我就拿出了两个星期的时间,非常认真地从头读一遍。这本书以前我读了很多次,都是很随便地读,我发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需要从头到尾地读,这本书是随便哪一页都可以进入的,而且读完之后就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多少有名的作家,多少有名的作品都会有败笔。《百年孤独》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经典,它在中国读者和中国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跟《圣经》差不多了。但读完《百年孤独》,感觉最后两章已能明显看出作家的劲耗得差不多了,把这两章完全砍掉也不影响小说的完整。看了这本书也使我更加有信心,连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其作品也有虎头蛇尾,中国作家的作品有虎头蛇尾的情况也情有可原。
与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
我在1980年底听朋友讲《百年孤独》,然后就买了回来,读了前面两页就拍案而起,说“小说可以这样写,我怎么不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唤起了很多的童年记忆、时代记忆和乡村记忆。为什么马尔克斯在中国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他描绘的生活,表现拉美神奇大地的方式跟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中国作家自己的记忆是非常相似的。
当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拉美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是有师承的,他的师承是卡夫卡。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说马尔克斯当年在巴黎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也说了“他妈的,小说可以这样写!”的话。我想《百年孤独》的成功就是在于把欧洲和美国的文学手法,跟拉美大地的神奇现实结合起来,当然也加上了马尔克斯个人的创造,然后形成了震惊世界文坛的学者流派。
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触了《百年孤独》之后,走的道路肯定和马尔克斯当年学习卡夫卡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想到自己的生活,想到中国的现实。我们之所以没有像马尔克斯创造一个新的流派来,是个体的力量不够强大,我们没有在马尔克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发展,我们只是在依样画葫芦地把中国的素材套到魔幻主义的模式里面去,所以写来写去始终是二流的货色。
1987年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觉悟到这个问题,我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写的是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个“灼热的高炉”。我说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着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么也没剩下。中国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小说来,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占据文学的一席之地,就要远远地绕开这两个人。这几十年来,我就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这种特别风格化的作家,有一点像鸦片,一吸上以后,很容易上瘾,上瘾以后就对你产生一种巨大的诱惑。在写作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我要离他远一点”,但是不自觉地就会向他靠近,就像《百年孤独》里面描述的,吉普赛人拖着一个磁铁走过街道,吸了很多的铁钉、铁盖之类的东西,形成了一个破铜烂铁的队伍。可以形象地想一下,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作家就像跟在《百年孤独》这块巨大的磁铁下面的小铁块一样,跟着他走,要避开他非常有难度。
回顾一下我的两部小说,《球状闪电》和《金发婴儿》。《球状闪电》里面描述了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老头,每年往自己身上粘羽毛,希望自己飞上天去,这一看就是类似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这样一些不由自主地模仿,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我就强调这个就是我们村里面一个真实的人物,这个人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是看书看痴迷了,老是觉得自己已经得道成仙。但是不管我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形,我这样写了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里面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人物。《金发婴儿》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在叙事方面的高度自由,完全打破了时空的局限,可以把过去的事提前来写,把过去的事以后来写,但是这些叙事方式,也让人一眼就看到了简单的模仿。
在第二个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我就尽量地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开篇就使用了盲人演唱的民谣,然后在叙事上尽量用写实的方法。有很多非常生动的,非常令我入迷的,我亲身经历过的细节,都不得不忍痛割爱,因为你一旦写上,马上读者就会说你是学马尔克斯的。在写《红高粱》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篇的一句话写来写去都像《百年孤独》的开头,什么“多年之后,面对什么想起什么来了”,后来我直接用年月表示,“农历多少年多少月,我父亲跟着土匪打游击”。但是后来还是把马脚露出来了,还是把《百年孤独》的气息露出来了。语言的力量太大了,感觉是避开了,但是后来回头一看,还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味道在里面,要摆脱很难。所以我写《天堂蒜薹之歌》只好用民谣的方式开篇,用对话的形式开篇,你怎么看也不像《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了。
在以后几十年的写作过程当中,我的小说里面也出现了很多魔幻的情境,很多超现实的情境,但是写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标准,就是在《百年孤独》里面出现过的类似的情节就不再用了。一直到2005年写《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才彻底地放开了,我觉得我躲了马尔克斯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都没有写进去,现在索性就放开写一次,就把我脑子里面积累非常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是我用了东方的情节。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我觉得很多读者还是会认为我是在学习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是我这个时候超现实的写作,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已经有距离了。
到《蛙》的时候我退了一步,用没有读《百年孤独》之前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的形象,里面写了一个乡村医生,这样公正的读者和苛刻的批评家都不会再说《蛙》里面依然有《百年孤独》里面的东西了。因此我说“搏斗”了二十年,终于可以离开它了,同时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学习大师的精髓
我和马尔克斯的搏斗就是千方百计把我生活中有的、让我激动的东西舍弃掉,但是对于马尔克斯处理题材的方式,我们是要学的。
我们作家难免在小说里面写生、死、爱、性,我们总是处在一个平视的近距离的角度上,这样作家似乎直接地就让读者感受到跟小说里面的人物一样的感情,陷入各种各样的冲动和沮丧之中。但是马尔克斯小说里面描写的生死,描写的性爱,就好像是描写人的吃饭喝水那么自然。马尔克斯的角度是零度的,在描写的时候,他站在一个上帝的视角上,就仿佛我们在观看大树下面的两窝蚂蚁在争斗一样,蚂蚁自己痛苦得一塌糊涂,壮烈得一塌糊涂,但是作为比他们大许多的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感受。我觉得马尔克斯在描写人类种种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居高临下看蚂蚁,他的角度和情感控制地非常好,所以看了他的性爱描写读者不会有任何的冲动,看了他的生生死死也不会有强烈的情感的刺激。这样事件的广阔性出来了,人的命运感出来了,人对社会的循环的感觉出来了。这个东西是值得学的,而小的技巧是要避免的,我“搏斗”的时候就把表面性的小技巧去掉,学真正精髓的东西。
马尔克斯、福克纳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多影响的作家,还有卡夫卡、海明威、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实际上都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广泛的阅读,只有当我们知道人家已经写过什么样的小说,用过什么样的手法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否则我们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还是模仿了别人。只有在一个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才能够寻找到自己突破的一个方向,而且这种广泛的阅读实际上会慢慢地让你从中发现自我。
在初学写作的时候,模仿并不可怕,就像写书法的要临帖,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临帖的书法家越多,就越能够领略到书法的妙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个性。小说创作也是类似的,我们只有大量的阅读,了解我们的前人,或者是其他国外同时代的人已经创作出来的这种小说或者是其他的艺术作品,我们才能够决定自己创新的方向。
想学习外国作家,如果单从形式上着眼肯定是不对的,还是要看他们处理题材的方式。比如说魔幻现实主义是这样处理题材的:同样一个细节,他用非常夸张的手段,而情节的魔幻,是用极端写实的细节来证明的。它的所谓的魔幻情节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之上,然后再夸大。
阅读经典
关于年轻人应该如何阅读,这是一个老话题了,尽管我也说过很多次了,但我认为有必要重复。在当今时代,生活节奏很快,每一个人可支配的时间很少,如果碰到什么读什么,可能读了半天才发现是毫无用处的东西,所以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选取一些经典的作品来读。
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它们是经过了时间的淘洗,经过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才获得了经典的地位。不只年轻人要读经典,即便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人过五十也仍然要读。今年春节期间我在高密待了一个月,白天出去,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是我第三遍读这本书,这一次读和前两次读不一样,过去读得很盲目的地方,这次读出很强烈的感受,比如说娜塔莎变成一个非常臃肿的妇女的时候,过去我觉得托尔斯泰破坏了我心中的偶像,但现在觉得托尔斯泰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了不起;小儿子初上战场,他内心胆怯,但是在别人面前表现得自己无所畏惧,他写得太准确了;还有对那个俄罗斯将领的描写,太成功了,经过他这样一写,这个昏庸的,老是迷迷糊糊的老头子,却成了俄军的最高统帅。我觉得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特别是在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时候,我觉得毛主席的发明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里面全部都有。当时我就想毛主席是否也读过《战争与和平》,如果读过,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受到了巨大的启发,如果没有读过,就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觉得经典是耐读的,所以这种书要反复地读,当然别的书也不妨浏览一下,要把精读和粗读结合起来。
好人与坏人
在我写了几十年的小说当中,我觉得我一直就是走这样一个路线:把好人当坏人来写。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写《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这些历史小说、战争小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战争小说曾经是红色经典中最重要的品种,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都可以回忆那些作品的名字以及里面出现的光辉的形象。但是到了我们拿起笔的时候,就感到对这样的作品很不满足,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些人物都是扁平的,都是单一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一部作品里面似乎就是黑和白的对立,就是好和坏的矛盾,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也很少有中间人物,而且一度有人因为写中间人物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所以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第一步做的就是把好人当做“坏人”来写,就是把好人身上阴暗的一面,好人身上的七情六欲都表现出来,这个是对“文革”艺术风格的反叛。
《红高粱》里面反叛的一些人,像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很多人物形象,当时的人是接受不了的。他们说你写抗战,不写八路军新四军而写土匪,这个是政治态度的问题,你的立场站在哪里。这立刻让我联想到“文革”期间的东西,那时候《红高粱》这样的作品是饱受争议的,当然现在我们看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写土匪抗战没有问题,写妓女抗战没有问题,写国民党抗战也没有问题。
过去我们写国民党的军队也是丑化的方式,把坏人写得一无是处,不但道德败坏,容貌也非常的丑陋,这在电影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村里面也有很多当八路军的,也有很多当国军的。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才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军队,就是国军,而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游击队是不合法的。那时候我们村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要当兵,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穿的是美式军装,很漂亮;而八路军就是穿一个破棉袄,无论从装备、形象都是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念,跑到延安里面去了。
总而言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好人和坏人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有很多历史的偶然性。有的人本来是想去当国军的,结果在路上被八路军抓去抬担架,阴错阳差地当了八路军,后来成了战斗英雄,成了我军的干部;有的人本来是想当八路军,然后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成了英雄,这些现象比比皆是。在巨大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当中,在巨大的动乱当中,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每个人就像一枚落到大江大河里面的枯叶一样,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哪一朵浪花卷到哪里去。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存在于老百姓的记忆里面的,真正的历史是在民间的,真正的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是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里面的,所以在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战争的小说里面,用的是一种反叛的思想,和红色经典相比,是一种反向的叙事态度。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坏人当好人写。实际上就是把坏人身上“人”的那一部分表现出来。好人身上有七情六欲,坏人身上也有七情六欲。弟兄两个,老大当了八路,老二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就是由于两个人站的队伍不一样,成了敌对的双方,但是这两个弟兄给父母拜寿的时候或者是吊唁的时候掉出来的眼泪都是一样的,都是作为人之子在难过。不管哪一个阶层,都有共通的人性,这应该是我们的作家要刻力地描写和始终不能忘记的。
最近几年中国文学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外介绍,很多大学有对外翻译中心,国家也拿出了很多钱来扶植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但是有的作品翻译过去实际上是没有读者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作品的立场太过明确,这些作品并不是站在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和立场来进行描写的,而是站在一个相对的局限的角度上,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是非的观念来进行描写的,这就使文学丧失了普遍性。真正被世界读者接受的,真正变成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就是描写普遍人性的部分。
很多中国人没有去过俄罗斯、法国和其他国家,但是我们会被俄罗斯或者是苏联的小说所打动,我们会被西方的电影所感动,因为这些作品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表现了一种普遍的人性,表现出人类情感共同的部分。只有描写了普遍人性的作品,只有排除了狭隘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性的作品,才能够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以上这些我想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作家普遍的共识,大家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写作。我最近看了很多写反腐败的小说,都注意到了贪官身上残存的人性,小说也都描写了正面人物身上所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有的人在金钱前面被打倒了,变成了一个坏人;有的人在金钱面前摇晃了很多次,但是最终没有倒下去,那么他就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经受了一个考验。摇晃了很多次没有倒下去的官员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自我;那种摇晃了很多次,那种倒下去的官员,我们不能向他学习,但是我们会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甚至是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身上依然发现了自己。
好的小说就是能够让读者从中发现自我,他会看到小说里面的很多人物就是他自己。不管是正面的人物或者是反面的人物,他身上都包含了读者自身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如果引发不了读者的共鸣,这样的作品如何打动人心?无从谈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