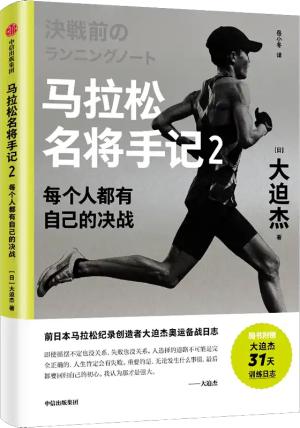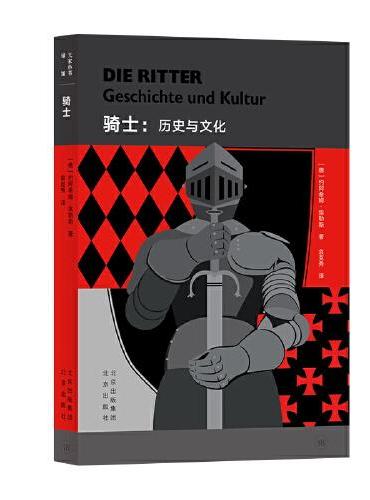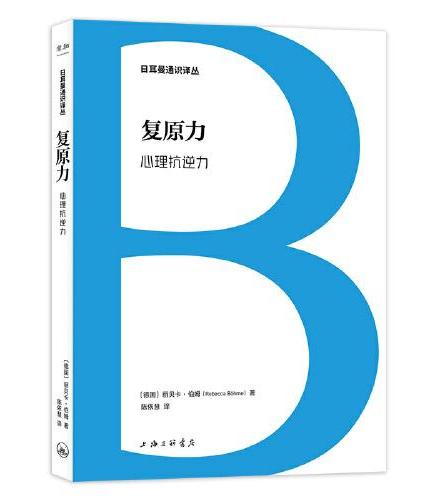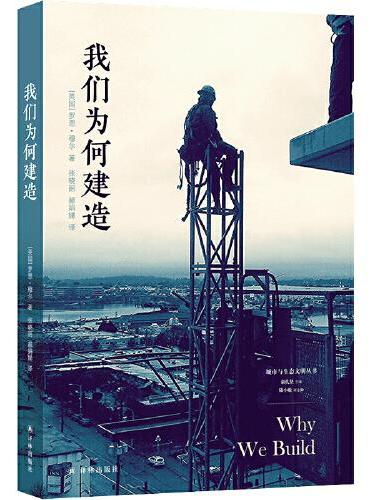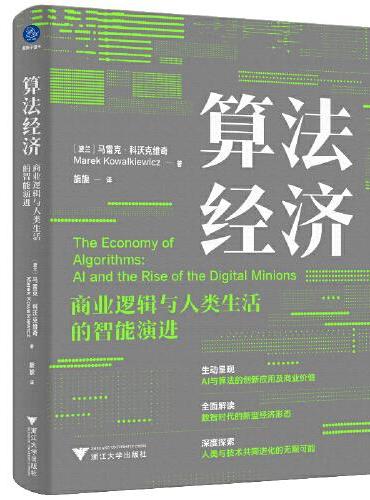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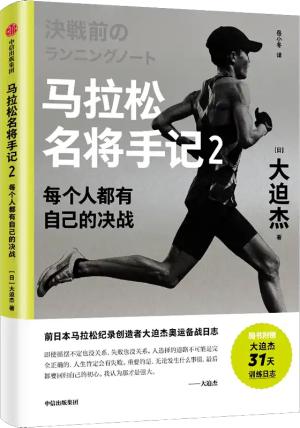
《
马拉松名将手记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战
》
售價:HK$
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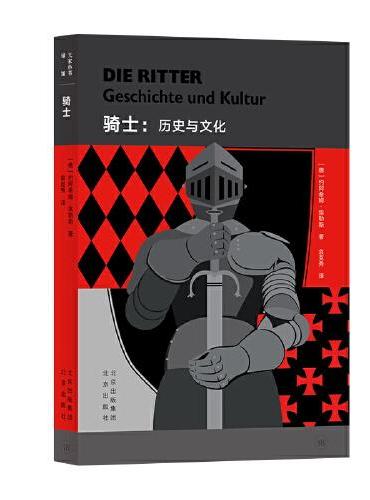
《
大家小书 译馆 骑士:历史与文化
》
售價:HK$
56.4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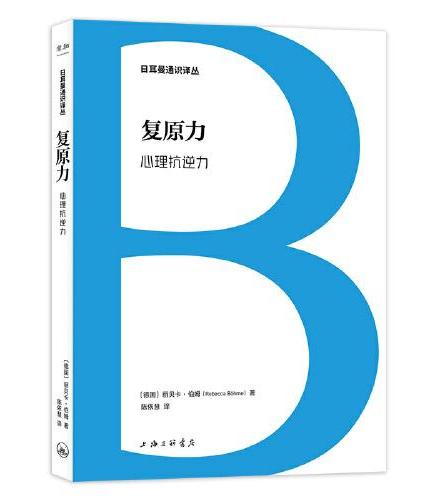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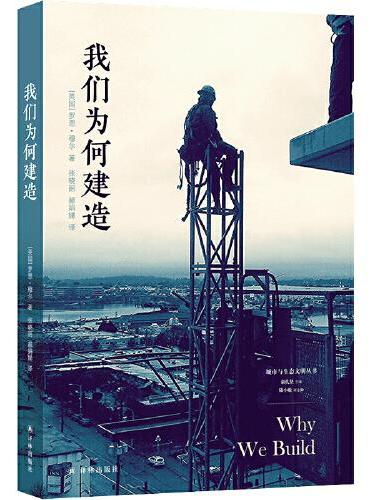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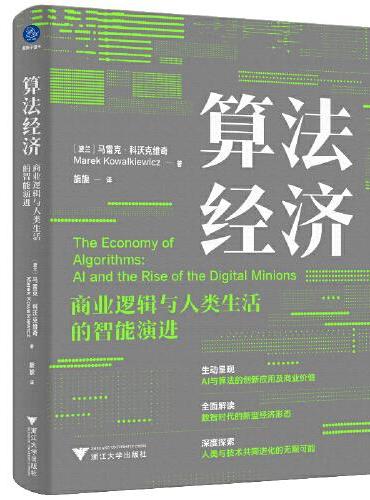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 編輯推薦: |
◎没有什么可以比生活中的点滴细碎的往事光影更能教诲人;
◎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父母亲筑的安宁小巢更能够滋养人的性灵;
◎唯有细敏的心灵能够捕捉花鸟草虫的韵味情致,能够懂得安宁起居生活中可以恒世的好味道。
◎十数幅清新淡雅的书画,好似闲闲道来的散文,
◎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禅在衣食住行中,散淡平凡的生活中也有人生大境界。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家王祥夫作品。
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吃饭穿衣亦有禅!
|
| 內容簡介: |
《衣食亦有禅》为随笔和国画的集合。王祥夫不仅仅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家。他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耳濡墨染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之道。他有专门的绘画老师,老师亦是一个具有古典文化情结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中,加之他的天性,他热爱市井,热爱饮食,热爱生活中注视到的点点滴滴美的享受。他说:人类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始终追寻美的过程。许多事物,只是当它们过去或消失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们的美来。他最经典的话是:古人除了击鼓鸣金地打仗,一般都很闲散。
就是这个闲散,充分地体现在了他的随笔和书画中。此闲散并非无事可做的庸庸碌碌。此闲散里有多少情趣和诙谐。生活本是细碎的桩桩件件日常构成,本书所书写的小事们哪一件里都盈漾着正在消逝,但是只要我们停下脚步,就能捉住的美好感受。
作者从玻璃琉璃写到沉香,从榴莲瓜子写到大酱。历史感、人文感,可以完全地在市井里寻见,只要你有一颗向美和够淡定素朴的生活之心。
|
| 關於作者: |
|
王祥夫,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赵树理文学奖、美国丹佛尔大学“最佳汉语小说翻译奖”等。辽宁省抚顺市人,现居山西大同,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乱世蝴蝶》、《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屠夫》,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西牛界旧事》、《城南诗篇》,散文集《杂七杂八》、《子夜随笔》等。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美、法、日、韩文在域外出版。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品文选刊》主编。
|
| 目錄:
|
胡同时光
玻璃
玻璃乐器
爬格子
案头
香与生活
民间香道
沉香的记忆
眼镜的事
关于伞
竹夫人
关于骆驼
八十年代的书店
看报纸
民间告示
随身口琴
手风琴与吉他
榴莲记
青梅煮酒
闲话瓜子
煮雪烹茶
德合堂杏子酒
说虾
吃烧鸡
吃肥肠
大筋
说大酱
夏天的味道
转市场
黄瓜酱油
绍兴酒
茄盒儿
三坊麻糖
芫荽鱼
说三叶
苦瓜生蚝
晋北饭食记
味道端午
先生姓朱
城墙植物
最完美的植物
再说竹子
1958年的麻雀
荷花记
草虫
纸上的房间
读画说大小
《腊梅珍禽图》的细节
大觉寺的玉兰
傅抱石先生
金农的梅花与字
且说陈老莲
台静农的梅花
乡村画匠
说八大山人
访徐渭故居
谁知道周瘦鹃的心情
毕竟是1951年
从画说到肥皂
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
宽堂冯先生
红湘妃
乐为纸奴
宝贝字典
夏日的蝉
庙宇与学校
民歌
关于闲章
启老一瞥
本色
|
| 內容試閱:
|
《衣食亦有禅》
胡同时光
里弄、胡同、巷子,这三者其实都一个意思。
在北方,没有叫“里弄”的,大多叫巷子,这个巷,那个巷。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宋时已经在叫巷了,或可能更早。胡同、巷子、里弄一般都交错在居民区,但也有把商店开在很窄的胡同里边的,但那些店一定也大不了,是小店,或买卖文具纸张,或买卖火柴蜡烛,更多的是买卖粮食,所以有“粮食胡同”。叫这个名字的胡同好像是各地都有,北京有,别处也有,还有就是“四眼井”这个胡同的名字,北京有,别处也不少。若考证起来,相信一定有意思。一条胡同里有四眼井?这比较少见,一般的情况是有一眼就足够了,除非大宅院非要坚持自己打井,如一条胡同里有十来户大人家,而且都要各自打井,一条胡同有十来口井,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粮食胡同”一定与卖粮有关,卖粮就得有粮店,粮店的样子现在许多人都不大清楚了,一进门,首先是粮柜,粮食都在木制的粮柜里放着,玉米面,一个柜;白面,一个柜;大米,一个柜;高粱面,又一个柜;小米,当然也要一个柜。当年还供应豆类,每人每月一两斤,多不了,黑豆、小豆、梅豆或绿豆,随你喜欢买哪种,豆子又得要一个柜。柜子后边就是面袋,都码得很高,直顶到房梁。白面码白面的,玉米面码玉米面的,大米码大米的,还有挂面,也一摞一摞码在那里。起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所有的家庭要吃饭就得去粮店买粮,家里要备有许多种面袋,放白面的,放大米的,放小米的,放玉米面的,放豆面的,大袋儿小袋儿各有各的用,也一定不能乱。我家有一个竹制的小孩儿车,当年母亲就经常推着它去买粮,一袋又一袋,买多少,哪一袋放什么粮哪一袋放什么豆子都不会出错。当时每月供应多少白面大米或粗粮都是有规定的,买白面的时候,你可以买挂面,买了挂面你就别想再买白面,就供应那么多。但你这个月没全部买完,粮店的人会给你存起来,想买的时候再买。粮店内部最特殊的景致应该是那几个从房顶吊下来的铁皮大漏斗,你把空面袋对着铁皮漏斗撑好了,负责称粮的就会把粮食从铁皮大漏斗给你倒在粮食口袋里。放粮食的木柜子到了晚上要打印子,一块大方木板,上边刻着字,要在面柜的面上一个挨着一个地打印子,这样一来,值夜的人就没法子打面柜子里粮食的念头,你要是去偷面,那面上的印子一乱,马上就会被发现。那块打印子的板子一定是要锁在一个地方,一般人拿不到手。究竟谁在保管那个印模子,不得而知。粮店还卖一种粮,就是土粮,是从粮店地上扫出来的粮食,里边也许什么都会有,白面、玉米面、小米、大米什么的,这种粮食也不是一般人都能买到的,必须是熟人。土粮买回去做什么,虽然被踩来踩去,但买回去还是一个字,吃!
有一年,我们胡同的粮店忽然运来了大批的玉米,是那种整玉米粒,运来,也不进店,都码在胡同外边的路边,一条路的两边都码满了,从西门外一直码到了火车站。第二天,粮食部门的人来了,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玉米粒都直接倒在了水泥路面上,人们这才知道是要在道上晒玉米。这一晒就晒了好长时间,下雨的时候就有人出来把玉米再堆起来,天晴了再摊开,至今人们也不明白那是在做什么?那些玉米后来是不是又都给磨成面供应给了人们?或者是千里迢迢地去支援了非洲,但起码有一点是,不会去支援了美国。
许多胡同现在都消失了,许多胡同的名字到现在只是记忆中的事。但也有有心人,在废墟样的拆迁工地上到处跑,到处拍照,到处收集胡同牌子。朋友给我看他收藏的胡同牌子,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粮食胡同”这块牌,蓝地白字,洋铁皮搪瓷,亮闪闪的,一点儿都没有生锈,想必当年挂在胡同口该是多么的醒目,现在却只有被收藏在私人家里,这真是让人怀念,让人多少还有那么点伤感。虽然我们现在吃粮方便多了,不用排队,不用拿粮本儿,不用再找人买从粮店地上扫起来的土粮。日子像是好了,但我们的心情为什么却总是不那么舒坦?为什么我们不舒坦?为什么我们总是还要怀念?这也许也是一种动力?
这当然也是一种动力!
玻璃
紫砂器不单只是宜兴有,但说到紫砂就离不开宜兴。
到了宜兴,可以说是遍地紫砂,有人想买紫砂壶,但转了一天都没有收获,再转一天,还是没有收获,因为紫砂太多,让他看花了眼。我喝茶不怎么用紫砂,朋友送的几把壶平时都摆在那里,有时候也会用来冲一壶随便什么茶,也就那么随便喝喝。紫砂壶要长久地用才会精神焕发,总不用,放在那里,会渐渐失去神采。紫砂花盆种花不错,但紫砂不宜做餐具,用紫砂汽锅做汽锅鸡,鸡好吃,锅可不好看,油头油脸。印象中,云南昆明的汽锅鸡最好,为什么?不知道。鸡小且嫩,香气扑鼻。要二两酒,把鸡先吃完,再来一碗白米饭打发鸡汤,鸡汤最好再热一下,放些整片整片的薄荷叶子在里边,味道很是特殊。好像是,在云南昆明,吃什么都要放些薄荷,要不,真不知道那么多的薄荷怎么打发?
说到喝茶,我以为还是以玻璃器为好。无论红茶绿茶,只要一泡在玻璃杯里,茶的颜色便会格外焕发。玻璃是从国外传来,据说是威尼斯人首先发明,一两千年前或更早,在中国,玻璃器贵比黄金。常见的汉代“蜻蜓眼”珠子,入土既久,一旦出土,珠光宝气光怪陆离真是有说不出的好看。说到“陆离”二字,其实就是“琉璃”。少时读屈原《离骚》,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当时还不懂“陆离”是什么意思。收藏界习惯把不透明的玻璃叫“琉璃”,透明的玻璃叫“玻璃”。南北朝时期的玻璃器大多都是舶来品,到了唐代大概还是如此,但要是看法门寺出土的那具微绿玻璃托盏,我想那应该是我们本土所产,《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酒肆盛酒用玻璃器,可见玻璃器在宋代的普及程度,但玻璃器终不如瓷器结实,磕磕碰碰,动辄碎裂。吾乡大同曾出土北魏时期的波斯玻璃碗,学术界多以为当时是用来饮茶的,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虽已大开,但我却以为用这样的玻璃器做茶具不大可能,因为其遇热容易裂璺。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散文《美的存在与发现》,写到了玻璃器:“成排玻璃杯摆在那里,恍如一队整装待发的阵列,玻璃杯都是倒扣,就是说杯底朝天,有的叠扣了两三层,大大小小,杯靠杯地并成一堆结晶体,晨光下耀眼夺目的,不是玻璃杯的整体,而是倒扣着的玻璃杯圆底的边缘,犹如钻石在闪出白光,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一排排玻璃杯亮晶晶的,造成一排排美丽的点点星光。”玻璃器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晶莹的闪光。我喜欢在家里比较暗的地方放一个很大的玻璃瓶,让它把光线折射出来。
为了喝茶,我经常是见到玻璃杯就买,但杯口儿一定要大一些才好。“明前”和“雨前”最好用玻璃杯冲泡,喝茶不但要享受春茶的味,更重要的是享受春茶的颜色,那种无比娇嫩的颜色,除了春茶不会再有的颜色。如用紫砂壶冲泡不会有这种效果,也很少有人用紫砂壶冲泡“明前”和“雨前”,如用瓷杯冲这样的春茶,白色的瓷杯和黑色的瓷杯都不会有玻璃杯那样的效果。人类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一直在那里追寻美的过程,所以,喝茶既要用嘴又要用眼睛。
以玻璃杯冲茶其实是极大众化的,放茶倒水而已,我主张,几乎是所有的“明前”和“雨前”都要后投,先把水倒上,再把茶叶投进去,看茶叶慢慢在水中载沉载浮,看春茶的颜色在杯里慢慢洇开。喝红茶,用玻璃杯也好,好的祁门红,初始作葡萄酒色,喝下来,渐作琥珀色,让眼睛感到舒服。但日本的抹茶却不能用玻璃杯喝,一是抹茶挂杯;二是抹茶不会让光线从杯那边透过来,也没见过有人用玻璃杯喝抹茶。绿茶粉和抹茶最好用黑色的茶碗。抹茶其实也很大众,一碗茶,传来传去大家喝,虽然有那么点不卫生。
中国各地的茶馆,用玻璃杯的不多,大多是带盖儿瓷杯,我喝茶,喜欢找个有庭院有植物的地方,交钱,领一壶开水,要两只带盖儿白瓷茶杯,然后找地方坐下来慢慢喝。年前与金宇澄去上海静安寺西边,居然找到这样的喝茶地方,坐在池塘西边的小亭子里,喝了半天茶,说了半天话,池塘对面坐了许多老头老太太,也在喝茶,也在说话。坐在我们喝茶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静安寺以东那栋张爱玲住过的小楼,那栋楼的大大出名完全是因为张爱玲曾于此居住。忽然就想到了当年张爱玲和胡兰成在那里会面的时候,难免不一边说话一边喝茶,无端端的,总觉得张爱玲喝的应该是红茶,或许就是五月春摘的“大吉岭”,而且是用大个儿的玻璃杯。满满一杯,红孜孜的。胡兰成的那张脸,想必也是红孜孜的。
玻璃乐器
有一种玩具,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人拿出来卖,是玻璃吹制的喇叭,说是喇叭,却封着口,放在嘴里轻轻一吹,“叭叭叭叭——叭!”脆亮好听,但好景绝不会长,吹着吹着——“叭”碎了!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玩具,好像是也没人再做,会这种手艺的人大同不知道还有没有?如失传,也真可惜。大同人把这种玻璃玩具叫做“琉璃圪棒”。玻璃从域外传来,汉代在中国本土已有生产,北魏时期的琉璃制品远远要珍贵于金银器,但大多都从两河流域进口过来。常见北魏墓出土琉璃残片,真是薄,真是漂亮,在日光下看之,闪烁一如珠母,真是华美异常无可比方!大同把玻璃喇叭称作“琉璃圪棒”,可见其历史该有多么古远!
玻璃喇叭——玻璃玩具,好像更应该叫做玻璃乐器,在吹制上好像难度相当大,要把玻璃吹到极薄极薄才行,要是不薄,岂能吹之有声,可见不是一般人所能来得了,我在上海看朋友做琉璃器,我忽然想请他们吹一个玻璃喇叭,我把形状、大小、薄厚告诉他们,并在纸上画出来,他们试做一二,但怎么吹也吹不响。他们说,玻璃能吹响吗?这是你的一种设想吧?我对他们说,这是一种大同民间的玻璃乐器,寿命绝不会长,吹久必碎,但声音绝对无可比拟,你想想,玻璃在吹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美妙而独特的响声!我在那里说,他们好像还是不相信,玻璃能做乐器吗?玻璃能发出声响吗?再吹几个试试,均不成功。我忽然更觉得我从小就玩的玻璃乐器是否在大同地区已经失传,要是失传,简直是令人痛心疾首。我去北京,又去北京朋友那边的玻璃小作坊,我告诉他们“玻璃喇叭”的颜色是紫红色或淡茶色的,这一回,他们马上明白了玻璃的配方,这次虽然可以吹得薄一些,但还是无法吹响。虽吹制不成功,但我的朋友的兴趣却高涨起来,他说,吹大大小小几十个玻璃喇叭,找三四十个人在台上吹奏岂不好看,玻璃闪闪烁烁,声音清清脆脆高高低低,舞台必须在全黑的底子上有那么一束光打下来照在那些玻璃喇叭上,那一定是一场极为奇特的演奏会!无可比拟的音乐会!我说这个音乐会是应该在我们大同开,虽然别处也有这种“玻璃喇叭”,但我以为大同的最好!
在中国,经过了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但跳过了铁器时代,也没有玻璃时代,而是直接进入了瓷器时代。玻璃在中国的发展史我一直不清楚,好像至今也没有这样一本书能把这个脉络理得清清楚楚。那天我翻看一本《波斯工艺美术史》真是吓了一跳,上边写着“以玻璃做吹器也”!以玻璃做吹器还能做什么?那不是玻璃喇叭又会是什么?北魏一朝受两河流域的影响最大,我设想,那大同民间的“琉璃圪棒”也许一直是从北魏吹到今天!
吹玻璃喇叭要有耐心,我从小到大笨拙且粗心,买两三个玻璃喇叭,吹一个,“叭叭”——碎了,再吹一个,“叭叭、叭叭”——又碎了,剩下一个不敢吹了,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盒子里,下边还垫一块布。总记着,我把一个紫颜色的、漂亮的、薄得不能再薄的玻璃喇叭放在了什么地方,一过就是三十年,我不知道那个玻璃喇叭现在在什么地方?
爬格子
许多人把作家写作叫作“爬格子”,像是有那么点写实的味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稿真可以算是辛苦,写着写着就真的要“爬”在那里了,八十年代的作家也真是能熬夜,写一阵,看看表,半夜十二点多了,再写一阵,再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那时候,我常常会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为了醒醒脑子,我会走到自家北边的小院里看看天上的星斗,那星斗是那么的清冷,那么的明亮,周围又是那样的寂静。在这种众人都睡你独醒的时候,你的脑子像是特别的清醒。我那时候年轻,在仰望星斗的时候,心里,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到了后来,才明白作家只不过是一种职业,任何加在作家头上的美誉都很好笑。
八十年代作家写长篇,简直是无一例外,几乎全部是靠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一次大学的讲座上,有个大学生突然站起来提问:“您的第一部长篇,三十多万字,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吗?”我当时在心里笑起来,难道可以两个字两个字抄吗?那只能是用电脑,一下子打出两个字或三个字的词来。所以近二十年中国的小说产量才会那么高,有人计算过,现在小说的年产量是二十年前的三十多倍还不止。所以我会在心里更加佩服那些古代的作家,用毛笔,写小楷,那些上百万字的小说是怎么作出来的?那才真叫是毅力!比如《红楼梦》,或者是《三国演义》。简直是“好家伙!”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种种美好理想和憧憬的年代,写作在那时候真是神圣,开笔会,头天晚上就开始兴奋了,想第二天怎么发言,“思想”和“哲学”这两个词在那个年代总是挥之不去。那时候写发言稿是彻夜的事。由于没有电脑,只能靠写。我那时候特别喜欢那种很大张的稿纸,这种稿纸的天地和两边的地方特别的宽大,改起稿来特别方便。那时候开笔会,不止是我,许多人都特别热心收集稿纸,《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和《青年文学》的稿纸,是让青年作家眼热的东西。一旦收集来,却并不单单是用来写稿,更多的是用于写信,亦是一种虚荣心。八十年代人们没有手机,打电话也不方便。想和朋友说些什么就写信。各种的信纸,各种的信封,都是为写而准备的。信纸有特别漂亮的花笺,信封也有各种的样式,上边且印着各种漂亮的图案。我认为,近二十年来邮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美感的邮政,一时间,竟然取消了所有形式的信封,要想寄信就必须买他们印制的那种牛皮纸信封,可以说是一种可耻的垄断行为,好在,我们现在有电脑,想说什么可以发电邮!好在,我们现在有手机,想把消息告诉朋友,我们可以发短信!不必再为那种丑陋而统一规范的信封气恼。我现在自己印有好看的信封,我给朋友写点什么,比如用八行笺,写好了,装在我自己的信封里,然后亲自交给朋友以做纪念,我们才不稀罕邮电局的那一枚邮戳。
八十年代对作家而言是个辛苦的年代,是,一定要写,是,一定要把时间耗到,趴在那里,把背拱起,眼睛近视的,要把脸几乎贴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我的第一部长篇《乱世蝴蝶》,最后一遍抄完,右手的手掌上留下了厚厚的茧。好多年后,才慢慢退去。说作家的写作是个体力活,可以说一点点都不夸张。用陕西话说,是“没有身体,吃架不住”!作家有写死的,从古到今,不在少数!而现在的写作就相对轻松得多。但我还是怀念八十年代,那种情怀,那种神圣感,那种彻夜写作的“耕作”精神。当然我也喜欢电脑,现在我也离不开电脑。我们这个时代是受电脑左右的时代,你去银行取钱,有时候银行的人会告诉你电脑出问题了,什么都不能办!
这是个让人有许多说不完的麻烦的时代,如果电脑一出毛病,作家的烦恼就更大,走出来,走进去,抓耳搔腮。我不大懂电脑,说来好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在电脑前点了一支香,唯愿电脑在新的一年里不要给我找麻烦,好好儿的别出毛病。我现在是完全接受电脑的统治!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谁让现在是“现在”,而不是八十年代。
案头
我的书房,现在是没有斋名的。前不久翻阅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巢林的诗集,很喜欢他的“清爱梅花苦爱茶”。这句诗真是很好,便想用来做斋名,但太长,如取其中两字,起一个“清苦斋”,又显得太娇矜。我毕竟不清苦,起码比一般人还过得去,还喝得起八九百元一斤的六安瓜片。我很喜欢周作人先生给自己取的斋名“苦雨庵”,后改为“苦茶庵”,左右不离一个“苦”字。如果自己也真把书房叫做苦什么庵,恐怕写出文章也要枯淡无味了,更何况我也没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把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的情怀。
再说我的书案,我的书案很像银行堆满账簿的台面,三面都是书,左边一摞是工具书,我常用的计有:《古汉语辞典》《辞海》《语言与语言学辞典》《说文解字》《中国地图》《中国大辞典》《日汉小辞典》。靠着这一摞的是大本可达四斤之重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鲁迅手稿》《孙中山先生手稿》。旁边的那几摞就常常变换了。比如现在的有:《牡丹亭》《养吉斋从录》《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四声猿》《绝妙好辞笺》《古代房事养生术》《袁中郎尺牍》《坛经》《诗经》《易经》《孙犁论文集》《丰子恺漫画集》《博尔赫斯小说选》《冬心先生集》《六朝文笺注》《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肯特版画选集》《林风眠画册》《京华烟云》《燕子笺》。这些书像好朋友一样团团围坐在我写字台的三面,终日与我频频交谈,令我想入非非。桌子左边还铺着一小块织得很粗放的小麻毯。这份格局比较特殊,毯子由绿、粉、黄、灰、紫五色的麻织成,写东西的时候正好衬着左胳膊,一边写一边喝茶时,茶杯也顺便搁在这块小毯上,既不滑动,洒了又不至于惊慌。小毯上有一拳大的玻璃球,球里一朵永开不败的粉色玻璃花。还有一青花笔筒,上边是山水亭林,为杨春华所赠,是她的画瓷作品。一汉代漆木瑞兽,其状如蟾蜍,却有角有翼。一对北魏蓝玻璃小鸟,玻璃里布满内裂,迎光视之,漂亮非凡,应该是当年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的存世孤品。还有两只大骰子,每一只都有婴儿拳头大,写累了的时候,掷一掷骰子玩,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比如说,我的长篇《蝴蝶》,一共写了七章,就是掷骰子的结果:掷三下,最大一次是七点,就写了七章。桌子右边是台灯,粗麻的灯罩,灯下边是亮晶晶的小铜闹钟,提示我该去睡或该去做什么。旁边又是一方北魏四足石砚,四边各一壶门,砚面四角又各一朵莲花,砚池圆形,围着砚池周边又是一圈绹纹。古砚的旁边是开片瓷水盂、放大镜。还有放闲章的盒子,里边有几十方闲章,其中两方闲章我自己最喜爱,一方的印文是“友风子雨”,一方是“境从心来”。桌上还有镇纸,一块是糯米浆石的,上边镌“笔落惊风雨”五字。一块是红木镶螺钿的,三棱形,三面都镶的是琴棋书画。我很喜欢这个镇纸,画小画用它压压纸,我喜欢用很粗糙的毛边纸写写画画,这种纸留得住笔,画山水梅花笔笔都枯涩苍茫!
我的案头,删繁就简到现在还有两大盆花,一盆是龟背竹,在书桌的左边,大叶子朝我伸过来,夜晚就显得很有情。当人们都睡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你的朋友,热闹时会失去许多朋友,冷清时会记起许多朋友。我的身后,另一盆几乎可以说是树,比我都高!叶子有蒲扇大,开起花来可真香,有人说它叫玉簪。我看不大像。这两盆花总伴着我到深夜。我常常于深夜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花用不用睡觉?这个问题恐怕无人能解答。
我的书房里还有什么呢?铜炮弹壳,一尺半高,里边插着一大把胡麻籽,让我想起那个小村子和那个部队。搬家后,我把许多东西送人,但永远不会送人的是那两件青花瓷。一件是花熏,像小缸,上边有盖,盖上有金钱孔,遍体青翠。当年是熏小件衣饰的,如手帕,如香包,如荷包。熏袜子不熏我不得而知,但我想象我的祖母用它来熏淡淡发黄的白纱帕,帕上绣着一只黄蝴蝶和一朵玉兰花。还有那青花罐,圆圆的,打开,盖子像只高足小碗,下半截就更像是碗。我很想用它来做茶碗,但舍不得。这两件青花瓷,一件上遍体画着缠枝牡丹,一件遍体画着凤凰和牡丹。都是手画。除了两件青花瓷,还有几把紫砂壶,还有一盒老墨,老墨是一位小时候的朋友送的,他去英国伦敦定居已有十一年。那盒墨真香,打开,过一会儿,家里便幽凉地弥漫了那味儿。盒子是古锦缎的,里边是白缎。这盒墨我一直舍不得用,都裂了。十锭墨没有一锭拿得起来,再过数十年或数百年,它一定是书画家们的宠物。盒里白缎上写着我的一首诗,诗曰:
相见时难别亦难
常思相伴夜将阑
联衾抵足成旧梦
细雨潇潇送离帆
写这篇小文时外边正下着雨,是入秋以来第一场大雨,原想打开窗子让屋子里进进雨气,想不到那雨却一下子飘到案头来,用手摸摸,案头分明已湿了一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