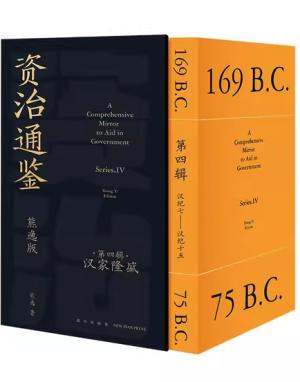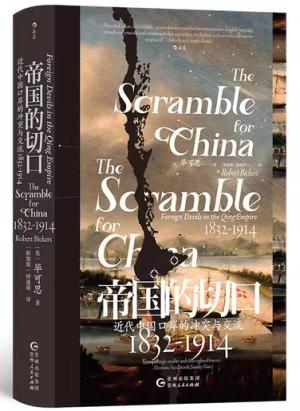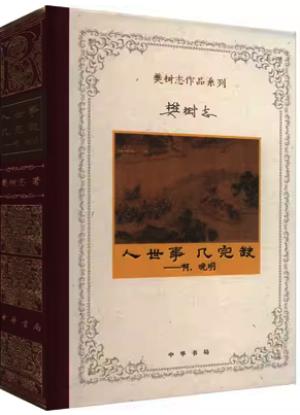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61.4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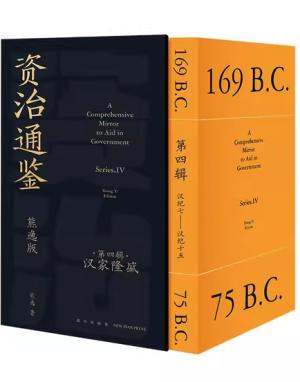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70.8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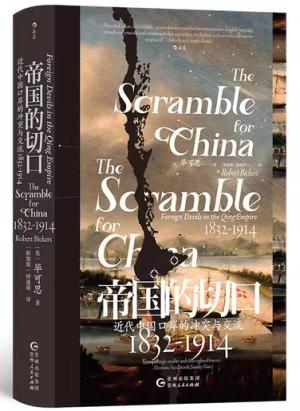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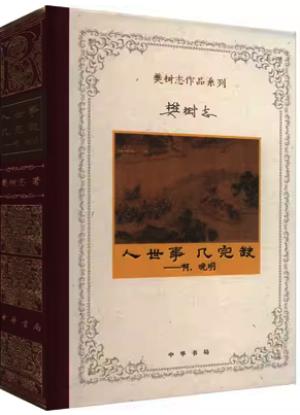
《
人世事,几完缺 —— 啊,晚明
》
售價:HK$
115.6

《
樊树志作品:重写明晚史系列(全6册 崇祯传+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万历传+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
售價:HK$
498.0
|
| 編輯推薦: |
|
我们常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文学亦如旧。在这本《文学的怀旧》中,作者用怀旧的心情,畅谈了鲁迅的翻译主张,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渊源,茅盾对丹麦文学的介绍,老舍对旧体诗的看法,郁达夫受唐诗的影响……因为种种机缘巧合,作者与中国许多学术、艺术大师有过亲密接触或书札往来,诸如熊佛西、黄药眠、夏衍、汪静之、曹靖华、罗大冈、萧乾、季羡林、施蛰存……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文化使命,于文学的怀旧中继往开来,于长路的漫漫中薪火相传。
|
| 內容簡介: |
该书是一本作品集,有五十多篇文章,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鲁迅的翻译
和翻译主张之类的文章,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作者认为鲁迅的翻译主张更提倡译文必须流利,这一点至今没有收到重视。二是回忆多次采访老作家时的文章,关于拜访的作家,其中包括巴金、罗荪、碧野、萧乾等,这些谈话具有史诗般的意义,从中也可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馆创建的全过程。
|
| 關於作者: |
|
刘麟,笔名刘季星。浙江黄岩人。中共党员。1951年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历任北京《俄文教学》杂志编辑,武汉大学外文系办公室主任、系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词集《温泉集》,编辑《巴金书信集》、《茅盾书信集》等,译著有《在蒲雅诺夫卡》、《天涯芳草》、《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果戈理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选》、《戴灰眼镜的人》、《克里米亚的海岸》、《诗人的市场》、《即兴诗人》以及《丹麦文学史》(合译)等。
|
| 目錄:
|
漫谈鲁迅的翻译
七十四年“牛奶路”
《死魂灵》五问
死魂灵乎,抑或死农奴乎?
语言学家的解释
文生社旧事
鲁迅与十八世纪的打牌
茅盾与丹麦文学
茅盾的政论诗
历史的陈迹
郁达夫诗出自唐诗考
郁达夫的《乱离杂诗》
白花
曹靖华的译著
老舍的旧体诗
模仿与扬弃
车过横浜桥
听夏衍一席谈
睡莲
胡风的旧体诗
聂绀弩《散宜生诗》的语言
青山的怀念
世纪的回顾
巴金的最后一件工作
愚公“填海”
巴金与石上韶
巴金与彼得罗夫
可敬的实干家
患难之交
季羡林先生与《中国大百科全书》
纪念罗荪九十冥寿
光明的使者
致霍松林先生信及其回复
无声的对话
橘园
叔侄
东禅巷风景
回忆静安别墅
第一次当编辑
台北十日
速写王仰晨
张继的诗和枫桥的寺
评唐诗三首
窗外的风景
果戈理两段译文的比较
对别林斯基批判果戈理的另类反应
莫斯科的文学馆
莫斯科的中央展览厅
雪地上的红花
悲凉的别墅
维也纳回声
南欧道上
我们的导游
复活节前夜
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馆
|
| 內容試閱:
|
漫谈鲁迅的翻译
今年是鲁迅去世七十年,也是他翻译的《死魂灵》——此书在我国的第一个中译本——问世七十年。鲁迅是位大家,创作和翻译是他的两翼。五四以来,像鲁迅这样集创作和翻译于一身、并且在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学家,为数不多,他们是文坛的骄傲,读者的偶像。
鲁迅的翻译以短篇居多,大部头的作品较少;以苏联和日本的作家居多,其他国家的较少;而从时代来看,则当代的多,古代的少,然而对于身处十九世纪上半叶帝俄治下的果戈理,鲁迅竟然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因翻译他的《死魂灵》过于劳累以致不寿,则是唯一的特例。
鲁迅最早接触《死魂灵》,可能已在他的晚年。据他的日记记载,1934年6月24日,他在上海内山书店购得《死魂灵》的日文译本一册,这大概是结缘的开始。他称赞这部小说是“世上著名的巨制”,欣赏作者的才能,因而继续留意收集并介绍其作品。7月24日,他有翻译中篇小说《鼻子》之举;8月3日,他翻译日本学人立野信之对果戈理的评论《果戈理私观》一文,两者同时在《译文》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时在9月)。8月13日,鲁迅又购得德文版《果戈理书信集》两卷。11月27日,黄源从旧书店为鲁迅淘到德文版《果戈理全集》一部,共计六册,鲁迅大喜,在翻阅之余,产生了与人合作翻译一套《果戈理选集》的计划,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梦想。他设想中的这套选集也分为六册:1)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2)《密尔格拉特》。3)短篇小说和Arabeske(即《小品集》)。4)戏曲。5)和6)则是《死魂灵》。由于《译文》月刊容量有限,不可能给果戈理过多的篇幅,于是他又想到了另行出书,名之为“译文丛书”,除了果戈理之外,也翻译出版其他作家的作品。
事有凑巧,次年2月,郑振铎从北平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学担任教职,并编辑《世界文库》,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他得知鲁迅对《死魂灵》有兴趣,就约鲁迅把它翻译出来,交给他在《世界文库》上逐月刊登,鲁迅同意,于是一项大的工程就此开始了。
1935年2月15日,鲁迅试译了一段《死魂灵》。3月12日,他译出了最初的两章,约两万字,交付郑振铎,郑即安排在《世界文库》第一辑发表,并亲自登门送来样书及稿费。此后鲁迅每月翻译两章约两三万字交稿,直到9月下旬,历时半年,《死魂灵》第一部十一章全部完工,郑振铎也依约分辑刊登完毕。在这期间曾经发生一件严重的纠纷,鲁迅和郑振铎程度不同地被卷入其中,但鲁迅没有把《死魂灵》未刊的译稿从生活书店撤回,照旧让它的《世界文库》发表。他认为中途撤稿,对读者来说是有悖于译者的道德的。但《死魂灵》第一部的单行本,却交给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鲁迅所梦想的《果戈理选集》和“译文丛书”之一,于1935年11月出版。
所谓“严重的纠纷”,至今已过去了七十年,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纵有“怨仇”,早已化为一笑而消泯了,此处旧事重提,只是为了说明与本文有关的重要史实而已。事情须从1934年6月说起。有一天,鲁迅邀请茅盾和黎烈文小聚,商谈他的一个主意,即编辑出版一种杂志,专门发表翻译作品,选材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以提高当时备受责难的翻译的身价。茅、黎二人均表赞成,愿与鲁迅共同作为发起人,并推举鲁迅为主编,另外找来黄源充当编辑。刊物定名为《译文》,经黄源与徐伯昕交涉,由生活书店出版。每月一期,前三期由三人分头翻译,提供稿件,交由鲁迅汇总编辑。第一期于9月16日出版,初印2500册,供不应求,当月即重印了四次。从第四期开始,鲁迅认为黄源见习期满,“已经毕业”,便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他,自己“退居二线”,继续为《译文》译稿写稿,出主意想办法。
1935年8月底,生活书店老板邹韬奋从国外归来,见徐伯昕带病工作,即命他离沪疗养,店务由毕云程代理。徐伯昕主持工作时,黄源已与他约定由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创议的“译文丛书”,此时黄源惟恐徐的离去会使事情生变,即向邹韬奋说明,邹果然否定徐的承诺,拒绝了黄源的要求。鲁迅听说后,叫黄源另找出路,黄转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吴朗西、巴金求助,却一说就成,他们愿意出版“译文丛书”。生活书店闻讯,当即邀鲁迅赴宴,宴会一开始,毕云程就向鲁迅提出要撤换《译文》月刊的编辑黄源,鲁迅把筷子一放,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拂袖而去。据茅盾的解释,“上海流氓请人吃茶而强迫其人承认某事,谓之吃讲茶”,却没有想到鲁迅不吃这杯茶,也不能忍受“吃讲茶”。
事情弄成僵局。郑振铎出面调解,他提出了折中方案,鲁迅接受,但邹韬奋不肯让步,于是鲁迅苦心经营一年之久的《译文》,不得不宣告停刊。
10月4日,鲁迅在致萧军的一封信中写道:“那天晚上,他们……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鲁迅并且批评了他称之为“文化统制”的东西。
关于这件事,自始至终周旋其中的茅盾评论说:“这都是生活书店过分从经济上打算盘的结果,造成了鲁迅后来对生活书店一直有不好的印象。”(《我走过的道路》中册241页)
巴金听说了这件事,也做出了反应。他原有一册高尔基小说的译本《草原故事》在生活书店出版,1935年10月间便把版权收回,让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为此并增写了一篇《后记》。多年以后,1989年11月13日,他在给王仰晨的信中,承认当时这样做是“对生活书店有意见(尤其是他们停掉《译文》月刊之后)”,但“抗战后形势改变,我对生活书店的工作有了新的看法,1939年初从桂林回到上海,整理旧作,便把《后记》删去了。”(这篇《后记》现收入《巴金全集》第17卷第169页。——刘注)
后来生活书店方面的徐伯昕养病回沪,自觉《译文》停刊一事对不起鲁迅和黄源,为了作些弥补,他请黄源从《译文》选出两本书,另外又请他翻译一部长篇小说,都由生活书店在抗战前给以出版(《黄源回忆录》109页)。四十年以后,大约是1970年代间,在关于当年《译文》停刊事件的一次调查中,徐伯昕认为,书店当时要撤换黄源,把问题搞严重了,怪不得鲁迅十分生气。他说,黄源在鲁迅指导下编辑《译文》,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同国民党作斗争,书店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要撤换他,这种做法对谁有利,不是很清楚了吗?……像在《译文》停刊这样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分歧,还从来没有过。“我认为书店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鲁迅先生是正确的。”(转引自黄源所著《忆念鲁迅先生》一书105页)
1936年3月,在中断五个月之后,《译文》复刊,编辑人仍为黄源,但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据说舆论仍然不坏,销量上升至五千份,一度达到六千,甚至超过了《文学》月刊。(见鲁迅临终前二日致曹靖华信)影响所及,翻译界的风气也有所好转,这年4月1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近来有一些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的倾向了,比先前的好用手段,进步得多;而读者的眼睛,也明亮起来,这是一个较好的现象。”
鲁迅于《译文》复刊半年后不幸病故,临终前只来得及翻阅它的出版广告,得知《死魂灵》第二部三章发表,却没有亲见它的全译本的出版,留下绝大的遗憾。但他创办的《译文》不仅加强了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培养了翻译人才,而且带动翻译界开始改变风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他为了提高文学翻译水平,采取了引导、示范以及批评等诸种文学的办法,没有借用行政的权力和缉私的手段,去对所谓“劣质翻译”围追堵截。当年全国的文学翻译杂志只有《译文》孤零零的一家,没有现在这般热闹景象,然而中流砥柱,居然力挽狂澜,是值得深思的。
鲁迅曾经多次声明,他之翻译《死魂灵》,是根据它的日文和德文译本来转译的。不是从俄文原作直接翻译,而是通过别种文字间接翻译,在鲁迅的词典中,这叫做“重译”。鲁迅是主张“重译”的,因为当时文人中懂英文和日文的居多,如果懂英文的只能翻译英美的小说,懂日文的不许翻译非日本的作品,那么,中国也就没有上起希腊罗马下至易卜生塞万提斯的文学名著的译本,连极流行的安徒生童话和阿拉伯故事也看不到了,何况即使有人懂得原作的文字,他愿不愿翻译、能不能翻译文学作品,也是问题,更不用说翻译得好不好了。
因此,他反对过分强调直接翻译的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看译文本身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即使将来各种名作都有了直接译本,重译本面临淘汰的时候,还要看看新译本是否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花边文学?论重译》)鲁迅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经手翻译的苏联或者俄国的作品,如《表》、《毁灭》、《十月》、《俄罗斯童话》以及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等人的论著和契诃夫、果戈理等人的小说(特别是《死魂灵》),都是由德文或日文转译而来的。当读者需要从外国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的时候,能让他们坐等懂原文的翻译家姗姗而来做直接的翻译吗?直接翻译的质量又必定可靠吗?鲁迅曾经指出韩侍桁的矛盾,1935年5月17夜,他在致胡风的信中说:
看《申报》上所登的广告,批评家侍桁先生在论从日文重译之不可靠了,这是真的。但我曾经为他校对过从日本文译出的东西,错处也不少,可见直接译亦往往不可靠了。
当然,鲁迅在进行间接翻译时,也并不顺利,他曾经几次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他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手上有英、德、日三种译本,不想有几个地方竟然三种译本都不同,这事情很使他气馁。在重译苏联女作家绥甫林娜的小说《肥料》时,发现另一个日文译本的语句颇为不同,不知谁是谁非,以哪一个为依据,他感叹说:“重译真是一种不大稳当的事情!”但他不能中途而废,必须把他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下去。
时至今日,文坛的情况与1930年代已大不相同,掌握外语的文人大量增加,所掌握的外语的种类也十分多样,但“重译”的生存基础并没有消失,鲁迅的主张仍然合乎实际,没有过时。我们只要看一看几本名著的译本就行了,比如说托尔斯泰,他的《战争与和平》,可读的仍然是董秋斯的译本;《安娜?卡列尼娜》,受欢迎的仍然是周扬的译文;《复活》以汝龙的本子为优,但他主要是根据它的英译本重译的。当然,这几种译本后来都对照着俄文原著做了校订,作过某些润饰,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取代。文学翻译与外交文件、医学著作、法律契约或者数学教材等等的翻译是不同的,不是简单的“忠实”或“准确”二字可以打发的,它首要的任务是把文学作品翻译成文学作品;翻译的小说像小说,诗像诗,而不是敷衍出字字准确、句句无误的考生的试卷。鲁迅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激烈的话,他说一切翻译,“错误是百分之九十九总在所不免的,可以不管。”(1935年9月8日致徐懋庸信)这不是在提倡“拆烂污”,而是提醒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不要忘了根本,把大作家的小说翻译成考生的试卷,才是最大的失误。
与此相联系的,鲁迅又主张“复译”。看准了一部外国作品,自信能把它译好,你动手就是了,无论是直接译还是间接译,无论有没有别人的译本,都不要畏缩,出版后可以一比高低。关于这一点,他在1935年2月初在致黄源和孟十还的信中都加以强调;他还进一步指出,后出的译本如能吸收已有译本的长处,加上自身的新心得,也许会造就为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他认为翻译界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但要“击退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
鲁迅还主张“直译”。所谓直译,不是把“跪下”翻译为“跪在膝之上”,而是注意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这些输入的外来的东西,经过若干时日的消化之后,可以被我们据为己有。在刚输入时,它们是不“顺”的,但据为己有后,它们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转化为顺;有一部分实在不能转化,就会被淘汰。(参见《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的这一表述,澄清了他的容易为一般人所误解的观点,他在翻译中并不是绝对推崇“不顺”而反对“顺”,相反,他是暂时容忍“不顺”,他的终极目的仍然是“顺”。但他经常使用的是意义相同的另外一个字眼:“流利”,或者“流畅”。他在评论别人译文的优劣时,首先着眼于译者的文笔是否流利;在修改自身的译文时,所要达到的满意的目标,便是流畅。从1920年代以来,他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
鲁迅自称,每当他动笔翻译之前,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使原文“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他认为,既然是翻译,其目的在于博览外国作品,不但移情,还要益智,因此,完全归化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兼顾两方面,一方面力求易解,另一方面要保存原作的丰姿,即原有的异国情调,也就是洋气;而要做到这一点,非直译不可。打开《死魂灵》,读者首先可以看到,他在书中翻译的人物的姓名,有不少相当古怪,比如“乞乞科夫”,“胚土赫”,“且泼拉可夫”,“泼留希金”以及“梭巴开维支”等等,用的字与一般姓名用字的习惯不大相符。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存洋气。他很早就有一个主张,反对在翻译作品中让外国人用上中国人的姓。例如王尔德姓王,高尔基姓高,高尔斯华绥也姓高,两高成了本家了,他对这种现象是加以嘲笑的。他也反对用花草一类字眼或者带丝旁、女字旁的字眼作为女性的名字,认为这样做有损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见《华盖集?咬文嚼字》一文)。但他的这个主张遭到了赵景深的批评,于是鲁、赵二人打起了笔墨官司。
其实鲁迅的这一主张,他本人并没有全面实践,他有时故意把外国人的姓名弄得古里古怪,同时也有背离自设的规范的行为,我们不妨认为他无力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他翻译的《死魂灵》的序言,其中就出现了裴伦、夏杜勃良、霍夫曼、莫利哀等人的名字,他们都戴着中国人的姓。也许可以辩解这样做是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应该沿用既有的译名,但是,这正好也说明了他的主张是有缺陷,是难以照办的。
数十年之后,北京的一些翻译机构,为了消除出版物上译名混乱的现象,实现统一,纷纷制定“译音表”,有的甚至编辑出版人名、地名的对照表,译者到时照抄就是了。而作为标准的译名,却采取赵景深的办法,起用《百家姓》,人物尽量姓中国人的姓氏,女人的名字多用草字头或者绞丝旁、女字旁的字眼,翻译界几乎全国一律。这个措施宣告鲁迅的主张的完全失败,后人愿意接受赵景深的办法,
无话可说。
除了人物姓名的保存洋气之外,鲁迅在译文中还拒绝中文的陈词滥调。《死魂灵》中有一句问话,某译本翻译为:“什么风把你吹来的?”鲁迅则译为:“什么引你到这里来的?”
下面是一个长句子的两种译法,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同,鲁迅的译文是:
……他的性格是刚强的……如果和他的意见相反,他也决不赞成。他不肯称愚蠢为聪明,尤其是别人吹起笛子来,他决不跳舞。但到结束,却显出他的性质里有着一点柔弱,驯良,到底是对于他首先所反对的变了赞成,称愚蠢为聪明,而且跟着别人的笛子,做起非常出色的跳舞来了。他们以激昂始,以丢脸终。
某译本则为:……看来他绝不会同意显然违背他想法的意见,绝不会把蠢家伙叫做聪明人,特别是不会答应让人牵着鼻子走;可是闹了归齐,在他的性格中总是会露出柔顺的本色,他恰巧正是会赞同他曾经反驳过的意见,把蠢家伙叫做聪明人,接着就让人牵着鼻子走,而且再听话也没有的了。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人。
这里不想比较两种译法的好坏,只请读者看鲁迅是怎样吸收外来的表现法,在译文中保存洋气,并拒绝乱用、滥用成语的。
鲁迅在翻译《死魂灵》之前,大致把它读了一遍,觉得写法平常,没有加以细究。他承认自己当时太小看果戈理了,以为他的作品容易译,不料很难,因而叫苦不迭。1935年5月17日在致胡风的信上说: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果戈理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其中虽无摩登名词(那时连电灯也没有),却有十八世纪的菜单,十八世纪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6月28日又向胡风诉苦说:“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德译本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坠,无聊,连自己也要摇头,不愿再看。翻译也非易事……”8月24日,他告诉萧军:《死魂灵》的作者“常常要发一大套议论,而这些议论,可真是难译,把我窘得汗流浃背。这回所据的是德译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错误一定不免,不过比起英译本的删节,日译本的错误更多来,也许好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他翻译的进度比较缓慢,“化了十多天功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却弄得一身大汗,恐怕也还是出力不讨好。此后每月一章,非吃大半年苦不可,我看每一章一万余字,总得化十天功夫……”(1935年3月16夜致黄源信)
尽管如此,他在细节或者个别字眼上仍不肯马虎。他虽然不怕被人说错误,但努力避免错误。大家知道,鲁迅在翻译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小说《表》时,文中有个叫做gannove的词把他难倒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遍查不得,为之日夜不安。译文发表半年以后,他终于查出了它的意思是“小偷”,于是在《译文》上用整页的篇幅,郑重其事地向读者作了更正。在翻译《死魂灵》时,他同样遇到了几个德文,一时没有查出意思,就用译音的办法和注解的方式告诉读者,以备今后订正。这就是第八章中的一句话:“一张名片,如果那名字是写在忒力夫二或是凯罗厄斯上面的,那就是神圣的物事。”什么叫做忒力夫二?什么又叫做凯罗厄斯?原来是德文的Treff-Zwei
和Karo-Asz,也就是扑克牌里的“梅花二”和“方块爱司”。可惜他来不及亲自予以更正,后人编辑出版他的译本时也没有在这里补写几个字,听任他的遗憾保留至今。
七十年来,《死魂灵》的中文译本已繁衍出将近十种,其中以鲁迅的译本历史最为悠久,影响也最大。由于当时工具书的欠缺以及鲁迅所依据的德文和日文译本存在的缺陷,鲁译本难免有各种不足,这已成历史事实,无可挽回。作为读者,我们赞同鲁迅的主张,希望有更优秀的复译本出现,在鲁译本的基础上提高一步,集合各家的优点,并融入本身多年研究的心得,铸成一个“定本”,早日流行于天下。
(2006年6月于北京)
七十四年“牛奶路”
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翻译的“牛奶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相隔已有七十余年,而某些批评者对它的兴趣至今不减,仍时不时地把它拿出来嘲弄一番,以揭露其无能。不过从他们的笔下可以看出,他们对它的来历若明若暗,几个基本事实也没有弄清楚,人云亦云,不免有美中不足之叹。
所谓基本事实,第一,赵景深原始的译文并非“牛奶路”,而是“牛乳路”,它出自赵译柴霍甫短篇小说集《悒郁》中的《樊凯》一篇,全句的译文为:“天上闪耀着光明的亮星,牛乳路很白,好像是礼拜日用雪擦过的一样……”(见此书第53页,开明书店1927年6月出版)。奶、乳二字虽是同义,但字面不同。
基本事实之二:早在鲁迅批评之前一两年,“牛乳路”已修改为“天河”。这一修改是在赵景深翻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期间完成的,具体时间约在1928、1929年之间,最迟当在此书出版的1930年5月之前。以上所说短篇杰作集的译文约百余篇,分为八卷,仍由开明书店出版;它的第五卷《孩子们》又把《樊凯》收入其中,并重新翻译了一遍,那个肇祸的句子修改为:“天上闪耀着明星,天河清晰得好像在假日扫去路上的残雪似的……”(见第81页)这一修改并非鲁迅的批评所促成,而是译者自觉的行为,是在“牛奶路”与“天河”之间作了选择,在重新翻译中权衡优劣后作出的结果。至于认定译者重新进行了翻译,那只要比较一下新、旧两种译文就可看出。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鲁迅批评“牛奶路”的文章《风马牛》最初发表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杂志上,距离它的修改已有一两年之久。如果1927年出版的《悒郁》那时仍在市面上流行,读者有可能明白鲁迅先生批评的矛头所向,否则,就会莫名其妙,因为他的批评,在一定的范围内,已落后于现实的变化;就其部分而言,则失去了瞄准的靶标。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鲁迅先生即使是在批评赵景深的历史错误,或者是已经改正的错误,并没有什么不妥。既然有了错误,白纸上印了黑字,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都应予以批评;一次不够,大可以再来一次,被批评者虚心听取就是了。
言之有理。又过了一年,即1932年12月,对于赵景深及其“牛奶路”,
鲁迅先生仍没有忘记,而且意犹未尽,果然再来一首古体五言绝句:“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书以赠人,同时批赵,提供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翻译中仅凭一字之错,赢得了鲁迅先生的两篇文章一首诗,甚至伴着他的不朽而留下千古的笑柄,在当时的文坛上,除了赵景深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人。那么,“牛奶路”究竟错在哪里?这个错误又有多大的严重性,值得如此关注呢?
Milky
way,横跨夜晚晴空中的一条乳白色星带,英国人和俄国人称为“奶路”,中国人叫它“银河”、“天河”,只是叫法不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可以意译,也可以直译。鲁迅先生在上述《风马牛》文中认为它可以翻译为“神奶路”,但同时又为“牛奶路”开脱,说是因为“白种人把一切奶都叫做Milk,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误译所造成的后果,到底有多么严重呢?鲁迅先生又说,对于像赵景深这样的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可以“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
所谓谈助,大多是有趣的材料;当然,对于别人是有趣的,当事人不会开心。原来“牛奶路”错误的严重性仅限于此。从这里也可看出鲁迅的批评是手下留情的,用心也是好的,毕竟当年的赵先生还是个未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这也是第四个基本事实。
小说家描写“牛奶路”与天文学家论述“银河”,意义是无法相比的,前者是写景,毕竟与国计民生无关,即使有错误,也只是提供谈助而已。而区区一个字眼之能掀起持久不衰的风波,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它背后所隐藏的翻译观点的某些分歧,而首先挑起事端的,可能是赵景深。1928年10月,他在《拜伦与婀迦丝朵的恋爱》一文中不点名地批评鲁迅关于外国人名翻译的见解:“记得某名人曾反对以花草的字眼来译女人名字,这在女性中心说或是男女平等说的人看来,自然有他的充分理由,但我却处处为看不惯译文的人着想,在男女译名上加一点分别,也未始不是便利读者的事。”这里的“某名人”即指鲁迅,他在1925年2月写了一篇《咬文嚼字》(后收入《华盖集》),指出“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鲁迅在这里只是谈翻译中的一种现象,没有使用任何不敬的词句,赵景深的文章就显得有点气势了,“某名人”,“看不惯译文”,都带着刺激性。
1931年2月,赵景深在一篇《论翻译》的文章(发表于《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中继续发挥他的翻译外国人名的主张,针锋相对地表示爱给外国人加上一个中国的姓,男女的译名也有分别,声称“这并不像社会问题大家的意见那样,是侮辱女性或是主张男女的根本差,只是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容易记忆”。为了翻译人名,甚至于根据《百家姓》列出一个表,附在文末。
1928年赵景深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读书杂记》,批评茅盾在《小说月报》上编译的“海外文坛消息”的六处错误,同时批评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正文与附录的冯雪峰的译文人名译法的不统一,“这对于读者是很不方便,容易误会成两个人的。”
而引起鲁迅无法继续容忍下去而起来反击的,是赵景深在上述《论翻译》中的这一段话:“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其害处当与误译相差无几。”他主张把严复的“信、达、雅”的次序调整为“达、信、雅”。鲁迅认为赵景深这番言论是在拼死命攻击“硬译”,并把它的“精义”归纳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加以抨击。他的激烈的言辞当时不见得给对手造成伤害,却在旧貌换新颜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但那是后人推波助澜变本加厉的结果,恐怕不能把账算到鲁迅头上。
其实鲁迅并非不要“顺”,否则,他翻译的《死魂灵》还能拿得出手,还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吗?认为鲁迅单纯强调“硬译”而排斥“顺”,是一种偏见或者误解。仅就1929年而言,他在一些场合也曾从流利、顺畅的角度来要求译文。例如这一年6月21日,在致陈君涵的信中,他指出陈所翻译的契诃夫的剧本《蠢货》“直译之处还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同年9月,他又在《小彼得》的译本序中说道:“……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11月8日致孙用信,他称赞《勇敢的约翰》“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以上种种,恐怕不能说不代表鲁迅先生对于翻译的看法,因此,说鲁迅不要“顺”,只有梁实秋、赵景深等人才主张“顺”,是片面的,与事实不符。
我倒认为“牛奶路”这一译法实在是不顺的表现,因为不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和构词规范。牛奶是液体,是食品,又是商品,可以说牛奶公司,牛奶贸易,牛奶房,牛奶罐,或者牛奶酪,牛奶糖,甚至可以说牛奶浴,牛奶池;如果说牛奶山、牛奶林,那就不通。抛弃“牛奶路”而取“天河”,才算通顺。凡是批评或者嘲笑“牛奶路”的,实际上是批评或者嘲笑它的不顺,主张顺者大概也是因为它的不顺而修改之,应该说,双方在求顺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
赵景深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长期处于不加声辩的沉默之中,但他并非没有反应。1936年2月或者更早,他在《文人剪影》一书中为鲁迅剪影时,说了一些闲话,然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他对于小说的翻译重信而不十分重达,我则重达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现在他的译文也重起达来,而我也觉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对的了,虽然我已经很早就搁下了翻译的笔。”现在看来,实际情况恐怕确实如此。
1976年10月20日,赵景深在一封致友人的复信中,回答当年受到鲁迅批评的事,一方面为误译进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说明事实,否认鲁迅所归纳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是他的意思,他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从他的《论翻译》一文来看,事实确也如此。鲁迅的归纳和瞿秋白据此而作的进一步的提炼(“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皆非赵景深的观点。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1985年1月赵景深先生告别了人间,“牛奶路”的事件至此应该结束了吧,然而,批评赵景深的喧嚣仍然不绝于耳;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展,出现了为赵景深辩护和对鲁迅进行反批评的声音。这种现象不足为怪,因为不平则鸣,历来如此,不过请不要忘记上述的第二个基本事实。“牛奶路”早已被赵景深自觉抛弃,揪住不放是无知,终将招来读者的厌烦;矫枉过正,反过来认为它传达了什么“文化意象”而加以美化,这岂不是在贬低或否定赵景深当年修改的意义了吗?
回顾历史,文学翻译中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即使是名家也有失察或者失手的时候,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拿现代文坛的顶尖人物来说吧。据茅盾回忆,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被人指出错译十多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文也遭到批评,郭沫若大怒,写信指责发表批评的编辑者是“借刀杀人”;1922年,茅盾本人在《小说月报》撰文介绍英国诗人雪莱时,曾经把“无神论”错译为“雅典主义”,成仿吾做了一篇长文加以嘲笑,激起鲁迅的不满,认为这是创造社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攻击”(见《上海文艺之一瞥》);而鲁迅翻译的《毁灭》,单是序言中的几段,瞿秋白就开列出了九个地方需要加工或修改(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如此等等,实乃顽症与通病。有了错误,改正就是了,茅盾说得好:“……我想,读者自会衡量轻重,辨明是非,不会因为错译了一个字就否定整篇文章,更不会因之否定我这个人。”(《我走过的道路》上册217页)对于其他人,包括赵景深在内,似也应该采取此种态度。
赵景深先生在文学翻译事业中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是他第一个把契诃夫的百余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为八卷出版,几乎可以称为全集,但他不愿用全集之名。是他第一个于1932至1933年把《格林童话》全部翻译成为中文出版,共计13卷。而早在1923年,他就开始翻译安徒生的童话,后来编为6部(即《无画的画帖》,1923;《安徒生童话集》,1928;《安徒生童话新集》,1929;《月的话》,1929;《皇帝的新衣》,1930;《柳下》,1931),据粗略的统计,数量超过40篇。今年是安徒生诞生200周年,他的作品在中国已广泛流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有书店,定有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出售;而在它们的翻译者的群体之中,赵景深是属于先锋之列。今天已经买不到他的译本了,但他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时代的脚步声中,可以听到他的呼吸。
(2005年2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