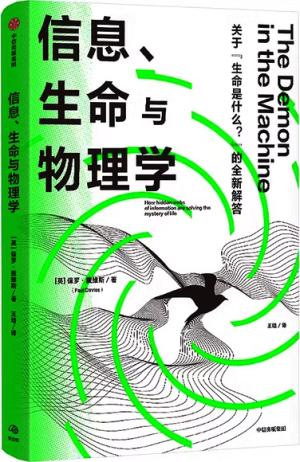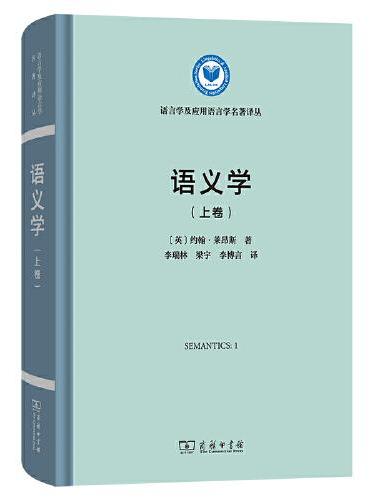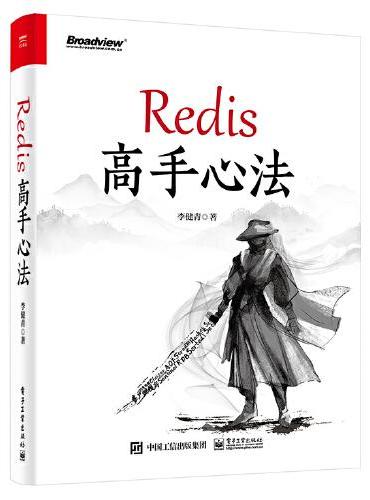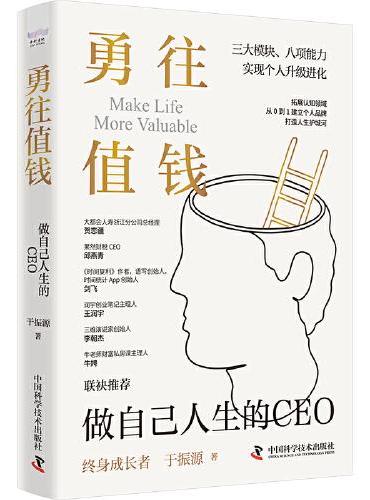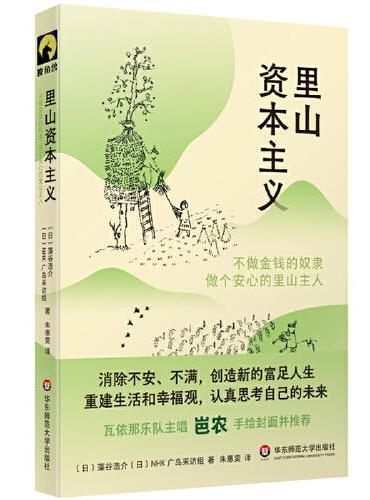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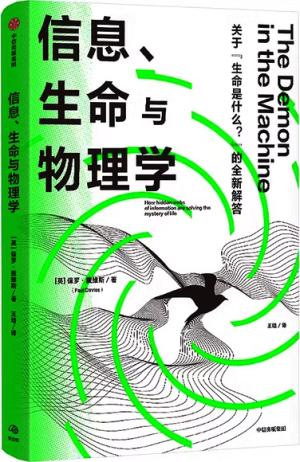
《
信息、生命与物理学
》
售價:HK$
90.9

《
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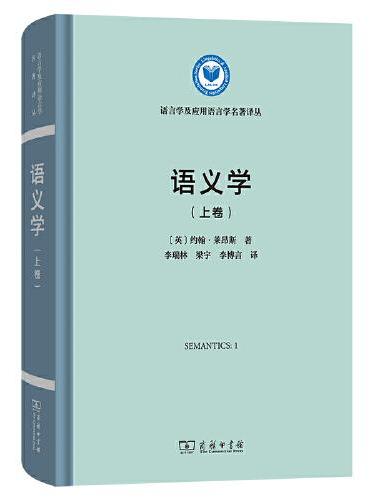
《
语义学(上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著译丛)
》
售價:HK$
1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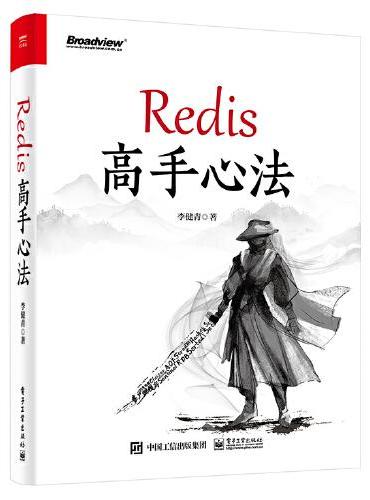
《
Redis 高手心法
》
售價:HK$
1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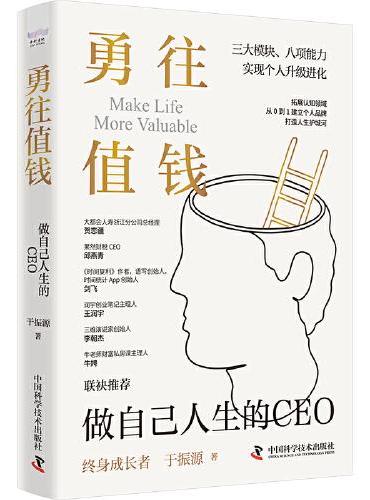
《
勇往值钱:做自己人生的CEO
》
售價:HK$
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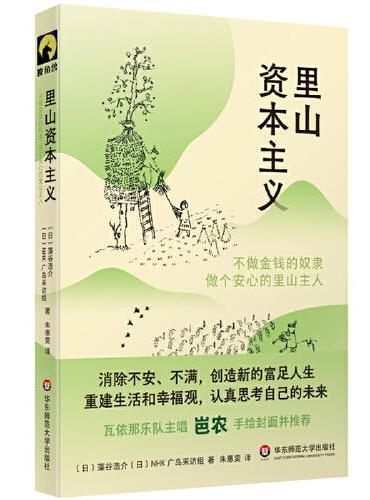
《
里山资本主义:不做金钱的奴隶,做个安心的里山主人(献礼大地)
》
售價:HK$
67.9

《
欧洲雇佣兵研究(1350-1800)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
贾平凹:在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总书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还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我说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他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
| 內容簡介: |
|
“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收录作者1973年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中篇卷六卷,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作品集用“倒叙”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
|
| 目錄:
|
|
九叶树 商州又录 小月前本 鸡窝哇人家 马玉林和他的儿子
|
| 內容試閱:
|
一
吃罢午饭,石根撂下筷子就到了阳坡里,给香獐子开膛。他脚手麻利,刃游自如,先将麝囊割了,连同鞭子一起粘贴在石头上,就缚起野物的后腿倒吊在两棵毛柳木树上,以致把毛柳木树合弯成一个满满的弓形。掏了心肺,摘了肝胆,五脏收拾得空空,刀在背上分边子猛劲儿砍了,毛柳木树“嘣”地弹射分开,白花花两扇肥肉便挂在那里晃荡不已。一个冬天里,饭是可以不吃淡的了,酸菜也能用荤汤热煎;单这一堆下水,盐腌烟熏,足够喝十天八天柿子酒的下酒菜,真是神仙的日子!香獐子头不要,一扬手丢到下洼蒿丛里去,立即招来三只老鹰。老鹰打着旋儿快活,他也快活,哼着花鼓提了肠子到溪里去翻洗。水流清清的,一棵倒在溪边的榛子树,根部已经断裂,奇怪的是浸在水底的叶子,还绿得翠翠的新鲜。几只蜉蝣,长脚轻柔地在那里悠闲,一弓身子就都从水面极快地划去,水好像不是水,是光滑的玻璃呢。
让肠子像绸带一样在水里抖,石根就仰躺在草窝里唱花鼓。花鼓的曲名儿叫《十唱姐》,是卖丝线的货郎对着一家黄花女子唱的,从头上的红头绳一直唱到脚上的绣花鞋。石根唱到“姐儿好裙子”,心里舒坦得很,张眼四处打望,天空下的面前这座山崖,好像织在匀匀的彩网里。槲叶多么黄啊,一丛一丛的;栲树、青桐、杜梨、花榛的叶子却红得滴血,常又和松树搅在一起;桦树似乎更粉白了,这媳妇精变的,仿佛是执意地在显示自己的风骚。深秋的山上景致真好,怪不得城里的人来了,都说是“丰富多彩”。那台台坎坎上的龙须草,今年长得比往年都好,齐严严罩了岩角石嘴;穴洼里的腊木条叶子也全落了,一丛便可以砍一担子呢。山下马王镇收购站里,龙须草开始收购,价钱比去冬提高了几分,黄腊木条子编成筐,镇上有汽车收着往城里拉。这都是钱啊,等着石根去割、去砍呢。还有山核桃、毛栗子、橡碗子……树底下的茅草窝里,荆棘丛里,只要愿意去捡,一晌午蛮能收获一麻袋。这山里,遍地是宝哟!人却长不出个三头六臂。邻居的三户人家,都忙着采集木耳,泡制春上的拳芽菜,老婆娃娃都忙活了;石根单枪匹马,他顾不过来,也不眼红,尽力而为嘛。
洗好了肠子,捆起来,他还在唱着。突然听见山崖上哇哇地一片噪响。举目看时,好一群白脖子乌鸦被惊乱了,半人深的茅草里,倏地出现了一只香獐子,老得毛都焦黄了,向这里窥探。这是一只死难者家属,是来向同类哀悼,还是寻石根复仇?石根一下子咽了“姐儿好”,闪身趴下,从毛柳木树下抓起那杆猎枪。一声巨响,老香獐子连忙跑掉了;乌鸦们也霎时投入槲叶丛里去,失却了踪影。
石根本无意再有什么收获,空放过一枪,也便没心思去穷追。新政策颁布以后,分给他二亩八分坡地,一亩三分沟畔平地。他不喂牛,也不养猪,一亩种毛苕子压肥,三亩春种小麦、芋头,夏播包谷、荞麦,一年二料,耕种收获,他十天半月就收拾得清清白白。空下来的日子,就全是他的,在家里酿着柿子酒喝,喝足了就站在门前小桃树下唱花鼓。石根的花鼓唱得好,山里人家过红白喜事,他是少不了的角色。他模样俊俏,声调清亮,又不要酬钱,大受村人称赞,他也就乐在其中。或者,一个人到山上去,提了那杆猎枪,满山跑着打野物。他的猎龄并不长,却眼睛好使,脚腿有力,常常十枪八枪就会有一样东西死在他手。这日子正应了俗话说的“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昨天,他正在割龙须草,发现了这只香獐子。丢下镰刀放枪,一颗子弹就将百二八十块钱的宝物打跌下崖来。邻居的倒骂起老婆娃娃是拖累,害得他没有石根富足自在。他在心里说:“哼,吃饱了肚子嫌打嗝儿,老婆娃娃是多余的,你给我送来啊!”口里却说道:“你何苦哩,下猪娃一样有了三个女子,你还想要个小子,三更半夜地往九叶树下磕头哩!”
九叶树是这一片山上人家的村志,离石根家三里。石根本来是取笑邻居的,但一说起九叶树,心里就痒痒的,又得唱那《十唱姐》,“十唱姐儿唱完了,姐儿浑身都是好”,就有一个念头从心眼缝儿钻出来,自言自语说:这货郎不知娶了没娶那姐儿?
他们这地方,说偏僻也真够偏僻,说不偏僻也就不能算多偏僻。北边一百二十里外是陕西最南的一个边城;南边八十里是湖北最北的一个县。虽都是县,人口却多,繁华得比一个市热闹。本来两个城市相距二百里,但一座白马岭却从中隔绝,长期因为是两个省,各自为政,谁也不肯花钱打通一条公路来,这地方也便被久久地遗忘了。山沟里只有一条小路,供山里人出入使用,外人是不曾涉足的。世代以来,山外人都以为山里贫困,殊不知风光之美尽在这里。从沟口往里走,路随山升,越走越高,但高到山脑,却成了平地。入平地处是一个坝型的坡,相传是早年两边山峰崩坍后堆积成的。于是坝坡后便将沟道里的流水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潭边住了几十户人家:沿潭往后的东沟岔里几家,西沟洼里几家。拢共繁衍百十户。九叶树就在坝坡之上,高五丈,粗三搂,枝叶平铺半空,像一块不散的绿云。天晴无风,山中百鸟朝来,一起鸣叫,好听得犹如仙乐自天而降。更是天下少有的,竟一树发了九枝,枝枝木质不同,叶形有异,是冬青的,花椽的,榛子的,散柏的,刺柏的,杉木的,青桐的,枸子的,棠梨的。山地人科学不足,以为神物,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来树下烧香磕头。现在这种仪式当然不再公开,求神要娃的人只能夜里偷偷来。但村子里的重大集会,却都在这里进行,以致发生家与家争吵,人与人纠纷,多在这树下拍腔咒誓。树是如此好树,可惜长在深山,出了白马岭,陕西边城的人不知道,湖北县城的人亦不知道。自生虽没有自灭,但几十年几百年寂寂寞寞地自长着。
责任制实行以后,山地的年轻汉子开始走出山来。他们不再是满面黑灰去讨吃要喝。粮食的丰收使他们口大气粗,山货的自销使他们英英武武,可以在山下的城镇里大声讨价还价,可以狡黠地掐指算账;他们满把掏钱地在酒店里打酒喝,啃着锅盔在戏园子里听大戏。到底城里人聪慧,为了赚得山里人的土产,便也钻进山来,带一批破鞋旧衣,换去核桃、柿饼、木耳、拳芽。到后来两省经济互通往来,各所在县向山里筑路,一直修到山下三十里的地方设了车站、收购站。山里被外部世界认识了,这村子的所在更被城里人传为仙境。城里人有的是钱和时间,少的是青春和安静,便有文人记者写文章介绍,说这里坝坡上如何茂林修竹,水有清流激湍,路有十八道弯,弯弯怪石随物赋形,以形写意;说坝后如何一潭清波,山影倒浮,鱼鸟影同,晨露夕雾多变幻,春夏秋冬色分明;说得最多也最离奇的当然是九叶树。于是乎,奇装异服的城里人,红男绿女的时髦者,来探古的,求静的,谈情说爱的,发财寻利的,就都出现在山地人的面前。石根平日里好动,少不了就往九叶树下去,他见的城里人多,城里人也认识他的多。
看看城里来的人,给城里人讲讲九叶树的传闻和神话,说乏了,站困了,他就要到树下麦场边的杂货店子里去。店是一老一少开的。老的是罗子,个头不高,腿又是罗圈形,出门行走,总觉得路不平;少的是女儿,十九岁了,高过爹一头,好一脸颜色。罗子老汉大前年死了老伴,拉扯着独生女儿过活,地分以后,有了四亩地,女儿就成了主要劳力。这女儿几年光景竟出养得如花似玉。待到城里人到山里慢慢多起来,父女俩就开办了这个杂货店。说是货店,酒也卖,饭也卖,夜里也可以歇客。女儿人材好,性情又活泼,人多眼杂,自然成了众目所视之物。她就养了一条白狗,白日在店里的酒桌下啃猪蹄骨头,夜里蹲门口汪汪大叫,山谷空鸣,不亚于古者秦琼、敬德守门之威风。
石根最爱这条白狗,也最怕这条白狗。他每每一走向店去,它就大咬。咬声一起,他就势喊“兰兰!”店女儿却偏要恶作剧,出来并不唬退走狗,倒嘻嘻地瞧着热闹。等到人狗厮缠一团了,罗子会从窗口探出头来,骂兰兰:“你把你的狗惯成什么样了!”兰兰才一个口哨,白狗便安然温顺。他一进店,罗子就说:“你这小子,一定来者不善;狗是咬歹人呢。”他就脸子红红的,偷看一下兰兰。兰兰还是得意地笑。他最爱见这份笑。她知道打扮了,眉毛扯得细细的,袄腰做得窄窄的,身子的线条怪好看的,还总是露着白牙笑。罗子看出石根的憨相,就也呵呵不已,让兰兰切一盘猪耳朵,倒一葫芦酒来。罗子是个酒鬼。兰兰娘在世的时候,家境拮据,常要和老汉为酒吵架。如今手里有了积攒,老汉的酒葫芦便没空过,他不习惯喝闷酒,图着热闹,与石根便成了忘年之交。喝得次数多了,石根也不时提酒提肉过来搭伙。当然,喝酒是一半目的,另一半目的却是为兰兰来的;不过爱喝酒从不在这里醉;爱玩栽“方儿”从不赖字,赢一局,又要输一局;难得的一个糊涂人!因此,喝酒栽方倒博得老汉欢心,勤快殷切又取得兰兰满意。
山林渐渐暗下来,最后一道夕阳跌落在山崖顶上,沟底的雾开始生发,顺着梢林往上蒸。石根将香獐子肉背回屋里,一扇敷了盐,吊在锅台上的屋梁上,又将一束荆棘在肉上的绳子上系了,以防老鼠;却将另一扇一分三块,一块用葛条拴了,要提到杂货店下酒去。他最经心的是那麝药,小心翼翼装在一个瓶瓶里,揣在怀里了。出门的时候,又顺手拿了粘贴在墙上的麝子鞭,就唱起《十唱姐》。但他不愿意唱那货郎词,货郎可以看着人家唱,他不能。他只能想着唱,便自己顺了曲儿随唱随编:
一想你来实想你,
把你画在眼睛里;
黑天白日想起你,
眼睛一睁就看你。
二
石根刚刚走到九叶树下,就听见杂货店里有好多人在说话。三间低低矮矮的店房子,黑黝黝的,房顶上的烟囱里冒着白烟,间或有火星喷出来,灿灿的立即就消失了。门掩着,麻纸糊着的窗子里透着光,隐隐地衬出兰兰剪的“吉庆有余”的雄鸡和鲤鱼。石根理了理头上的乱发,才要走近去,白狗“汪”地就叫起来,黑地里一条影子往他面前扑。他忙将麝鞭丢过去;到底是贪嘴的家伙,得利而忘职,石根推门进去了。
屋子里烟雾腾腾,三间门面房里,东边是里外两间房子,里间是店家卧室,外间是客房;西边是后墙处盘锅灶,前窗下设百货台;空出中堂一间,则满满当当摆了三张桌子。桌子是土漆漆的,油光发亮,现在全坐满了人,都在喝酒吃烟;灶口火红红的,烧了滚水泡茶,烟雾水汽弥漫一起,使靠边桌子旁的屋柱上的油灯不十分光亮,人影晃动,四墙上便图影乍长还短,异形变态。石根好容易看清,来人里一些是西沟洼的,一些是清水潭南沿的;正北桌头坐的一位,他不认识,说着蛮腔,装束入时,听了一阵才知道是湖北过来贩桐油的。这湖北佬天黑歇脚在此,原本客买了酒喝,敬过老人一杯,罗子便得势趋过身子接了话,三说两说,村子里来了人,罗子就自个舀了酒合伙来喝。石根向老汉打了招呼,老汉酒气正盛,话在兴头,推过一个酒杯给他,就又五马三枪滔滔不绝。石根就在屋角的土墩上坐下,灯影里看看兰兰,人没有在。明知道她正在里边卧室里,也没个理由进去说话,只好脸上笑笑的,听着众人议论。
罗子说:“你说我们这九叶树是树中王啊,可山里人却没能耐。人常说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瞧你们就知道了这山里桐油便宜!”
湖北佬说:“老伯倒忌恨我们了?这一担桐油可落不下几个钱啊,亏得如今政策开放,才能腾出手来走走。可一趟来回四天,老婆娃娃撇在家里,出来住店呀,吃饭呀,回去又上税呀,挣个零花钱罢了。哪能像你们,出门就是宝,下一次山,随便带些什么,硬格铮铮的票子就满把抓了!”
罗子说:“话说得好,就是我们太死!没个做生意的习惯,世世辈辈都是自产自吃,端了金筷子银碗要饭。如今政策允许了,又都没那本事呢。”
几个村子里的人就说开了,有的说东沟洼里老杨头今年荞麦三担,让山外一个人一并买了去,老杨头得了一大把钱,可人家回去做荞面饸饹卖,反手就又是老杨头的五倍钱。有的说后坡根王寡妇挖药,一些山下人也跟着她去挖,竟一窝刨出十二斤的猪苓。有的说上一个月,仅南沟四户人家,被城里人用些小玩意儿就换去了一百斤板栗和三麻袋拳芽菜。末了就长叹一声,说山里人好笨,没有去过大城市,见的世面少,市面行情摸不着,还是少不了吃窝囊亏。接着就都眼红起这湖北佬,问他走了哪些地方,曾买了什么东西,又卖了什么东西?人家说出个数目字来,吃惊、奇怪,不免又有了几分嫉妒和气愤。
石根一直听他们说着,眼睛一刻不离湖北佬的脸,视他为英雄。听到山外的新鲜事,痛快处就喊一个好,糟心事就叹几声,骂几句,端了酒杯喝得脸色通红。后来就附过身子来,对着湖北佬说:“你们是城镇上的,离政策近,听说核桃柿饼要提价,这可是真的?城里人大鱼大肉吃得腻了,倒图个山货素口!黄花菜、蘑菇真的是紧缺货吗?要是一麻袋黄花菜背下山去,一天能推得出手吗?”
湖北佬说:“那是没问题的。好兄弟,现在是成龙变凤的时候,你这般年纪,蛮可以大显身手的!城里人吃饭讲究色味香,这色是第一,黄花、木耳、蘑菇都是席面上的菜啊!”
罗子说:“你这小子,见了姑娘家就烧脸,你还想到城里去?陕西、湖北你还不知道在哪个方位呢!”
石根说:“我就想试哩。城里人把手伸到山里来,山里人也要把脚长到城里去,什么事不是人干的?”
湖北佬笑了,拍着石根的肩说:“小伙子有气派!”转而又道,“话说回来,靠山吃山,近水吃水,仅凭坐在你们家门口,就有找上门来的哟!”罗子说:“这倒也是实情。就我这个小店,招呼像你这样的过路客人,我也落个手头活泛了。钱不好挣,也没个够数。世上浮物,你来我去嘛。石根,你怎么不喝了?你独根独苗的,还怕养活不起媳妇娃娃吗?你把龙须草割倒了多少了?”
石根说有三百斤了,还没有晒干,等天晴了,担到山下收购站去。湖北佬说:“光卖草就划不来了,你要安一台拧绳机,一斤草就翻几番价呢!”罗子说:“他要是有一个媳妇就好了,可他小子就是没有个媳妇!”屋子里的人就都哄地笑起来,打谑地问他晚上睡觉脚冷不冷,唱那么一口花鼓调,给人家结婚、生娃的去热闹,心里有没有胡思乱想?
石根倒噎得脸色红起来,端起酒杯子喝了,心里还是闷闷的。看了一下里间卧室的门帘,灯还亮着,不见兰兰走出来。
罗子已经醉眼蒙眬,又问道:“石根,听说你又打着了一只香獐子?”石根说:“打着了,我给你带了肉来。”说着就从墩子上取了肉过来。罗子就喊兰兰洗肉炒了来吃。兰兰没有动,石根有了机会进去叫。
兰兰在卧室的油灯底下纳袜底,嘴撅了多长,见石根进来,故意不理会。石根说:“伯叫你哩!”兰兰说:“他叫我我听不着!”石根才知道兰兰和爹憋气了,说:“我请你哩!”兰兰拔了针,低声说:“你来凑什么热闹!我爹老了,拿自己酒图别人快活哩,你偏要拿了肉来,肉是你的,涮锅生火却耗的是我家的柴!”石根说:“哟,你突然这么小气!让湖北佬尝尝这野味。你听见了吗,那人了不得的,装了一肚子新鲜事!”兰兰说:“我烦呢!他说咱山里那么好,咱们和他换换怎么样?!”石根愣了一会儿,就又笑笑,说:“走,我帮你洗肉去,我还有好东西给你呢!”兰兰走出来,罗子还在叮咛把肉炒得烂烂的。兰兰仍不做声,和石根踏了月色到清水潭里去。白狗照例跟着。
潭里静静的,月光下起着丝丝缕缕的雾,对岸山根下有狗咬了一下,白狗就应和了;此起彼伏,像是在瓮里,有空空的回音。兰兰说:“你有什么东西送我?再耍贫嘴,我让白狗咬你呢!”石根说:“我哪儿哄过你!”就拿出装有麝药的瓶瓶塞给兰兰。
兰兰说:“吓!我怎么敢要这个?这值多少钱哩!”
石根说:“贵重的东西我才给你哩!你做个香包儿戴上,打远处蝴蝶就飞来了。”
兰兰说:“要是惹来了蜂,会蜇我一身疙瘩哩。”
回家的路上,兰兰问:“香獐子是吃什么长大的,倒有这么香的东西?”石根说:“吃的还不是百样草!我一看见它,就想起给你做香包儿,一枪就打中了!”兰兰说:“你好狠心!”石根说:“谁叫它有香呢!”走到九叶树下,兰兰又问起这麝香在香獐子的什么地方。石根不愿说,嫌说了羞口。兰兰偏是问,石根附近来才说出一个字,她蓦地意识到,一个口哨,白狗蹿了上来,前爪搭在了石根的肩上。他大喊大叫起来,兰兰却一溜风地跑进店里去了。
石根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跑回店里,罗子见他一身泥土,就骂兰兰“没大没小”。兰兰在案上一边切肉,一边忍不住笑,说:“爹不知道,我的白狗认得好人坏人哩!”石根还是来帮着烧火。两个人一个忙上,一个忙下,目光一碰,兰兰就笑,石根也笑,浑身的血流得快快的,火也烧得旺旺的。
肉炒好了,端上桌子。罗子只喊着湖北佬不要停筷,说;“你们城镇的人啊,就喜欢吃些天上飞的,林里跑的。我年轻时候去过陕西边城,现在老了,哪儿去不了了,可也见了不少城里人,他们一到这里,说山也可爱,水也可爱,石崖上落一只红尾巴雀儿,还要立下来看个半天!往年里,我们这清水潭里,见谁吃过那鱼儿?鸡被黄鼠狼吸了血,囫囵囵的,挖个坑儿就埋了!”
石根问;“罗伯,今日个来了几批城里人?”
罗子说:“有四批吧。先是两个上年纪的人,天知道怎么爬上十八道弯的;再就是男女青年人,穿的衣服,带带绳绳可真够多,下坡的时候,也不避我,男的把女的就背起来了!”
满屋人哄哄大笑,罗子也越发得意,接连倒酒,酒葫芦里已经剩的不多了,都推说留给他喝,他竟说众人小瞧了他,结果全倒了出来。一时众人就说起城里来的人的趣事:说裤子做得那么宽,又长到包了脚后跟,如果上山去捡核桃,扎了裤管,一裤子能顶两个麻袋哩;说眼睛本来好好的,偏要戴上黑片子玻璃镜,枉花了钱,可却舍不得买上发夹,让那么多头发披在肩上。以此说下去,又说到城里人时兴“开放”,男的越来越衣服包得严,女的越来越衣服遮不住肉,奶罩都是硬壳的,大得像牛的暗眼。又说到城里有些年轻人发了大财,钱花得如流水一样,能喝一脸盆多马尿味的啤酒,喝醉了就跳舞,就亲嘴,亲热得过火了就去领结婚证,过厌烦了就离婚,离婚了还可以在报上登广告再找对象。在他们的眼里,城市是一个有好吃好喝好乐的地方,也是一个叫人疑惑惊慌刺激的地方。他们一尽儿依自己的道听途说、虚构演绎来证实自己的见解。到末了,差不多都喝得晕晕昏昏的了。
兰兰说:“爹,你们别那么瞎说浪话了,我看城里人倒比咱强哩,你们说三道四的,有谁真的去过城里吗?”
罗子就说道:“可不是我当众夸口哩,城里来的女娃娃我也都看了,穿得都好,论起细皮嫩肉的俏样,倒没一个比得上我家兰兰呢!”一句话倒把兰兰说羞了,扭过了脸去。又有人应和道:“兰兰是咱这里的城里人了!”石根就在灶火口叫:“城里人,城里人!”兰兰用铲子撩了他一头涮锅水,返身进了卧室。
这当儿,门口的白狗又咬了几下,大队长走了进来,粗声嚷道:“嚯,都在这儿!快来看看报吧,把咱们九叶树登上照片了,咱这儿以后就要有好多城里人来游览了!罗伯呀,恭喜你了,这店的生意要越发红火了!”罗子端了酒敬了,喜滋滋地说:“就为咱这九叶树?好!我老汉客多了,你常来喝酒呵!”众人都围过来看报纸,大队长拉住石根说:“县上有了通知,让扩修马王镇到这儿的路,咱队上要去三十个人。队里研究了,有你的名哩,一天是一元二角钱的工资。”石根说:“好,我这没媳妇没娃的,那里也得。等路扩修了,来的人多了,咱也娶他一个城里女子!”罗子一拍石根的头乐了:“有种,有种!我有了一个城里女儿,你也找一个城里媳妇,咱这地方真要出龙现凤啊!”兰兰坐在卧室里听了,直气得没好声地叫道:
“爹,你是喝多了!明日店门还开不开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