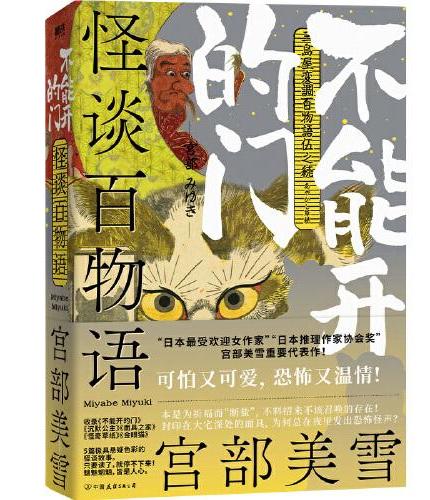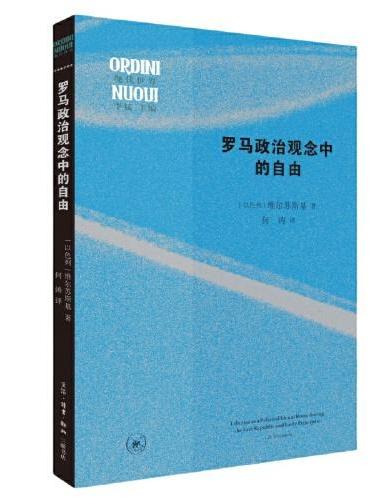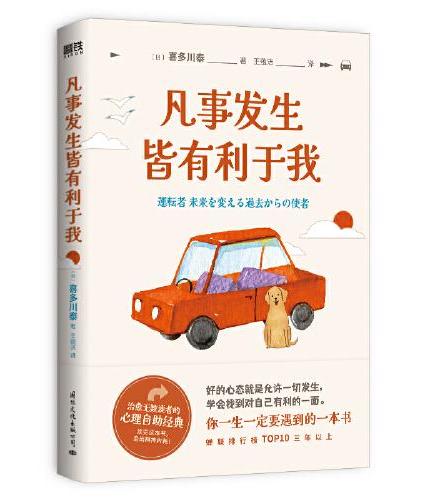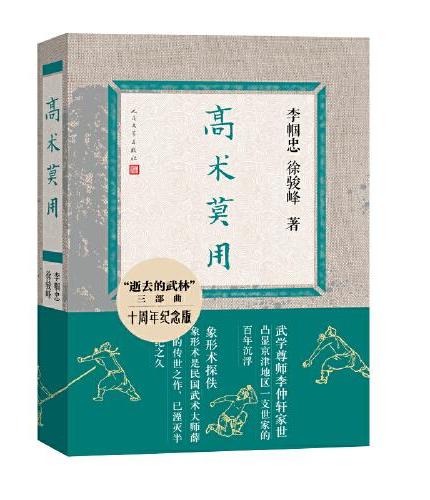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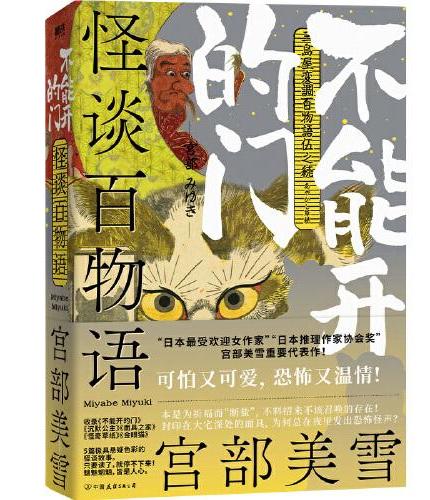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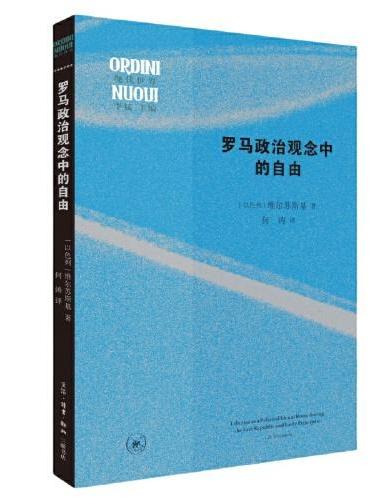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HK$
51.8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HK$
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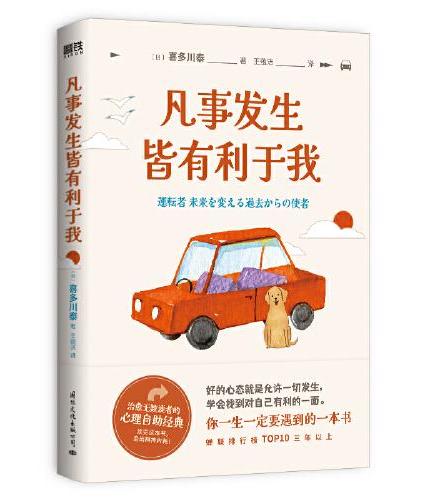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HK$
45.8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HK$
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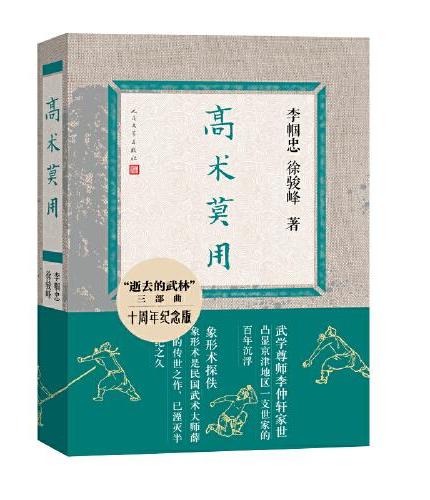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HK$
56.4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HK$
101.2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故宫,旧时叫紫禁城,皇帝住的地方。这座城里,除了皇亲贵胄、宫斗夺嫡,还有三教九流、市井生活……故宫闹鬼事件、惊天盗宝案、摸狮生子秘方……听听现代“大内高手”怎么说。
这本书里的故事是假的,不可尽信;这本书里的故事是真的,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或忍俊不禁,或唏嘘不已,或荒诞不经,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尽是人生百态。
|
| 內容簡介: |
|
作者以其父亲——“京城第一保卫处”警犬队创始人常福茂为原型,以幽默风趣的笔触将他从祖辈、父辈那儿听到的故宫故事一一写了下来。全书由十八章连缀构成,多以在故宫工作的小人物们的市井生活为背景,每章一个主题,讲述你闻所未闻的故宫段子。此书中有关于故宫的种种传说,有老北京人的京味儿生活……能让你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亦能让你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
| 關於作者: |
|
常文博,满族,北京人。祖辈、父辈两代人都在故宫工作,其父常福茂是“京城第一保卫处”——故宫保卫处警犬队创始人,人称“狗队长”。作者自小跟随父辈,耳闻目睹了很多故宫里的事,故以父亲为原型,以父亲的口吻写下了故宫里这些色彩斑斓的生活。
|
| 目錄:
|
第一章 红墙
第二章 冥审
第三章 夜巡
第四章 赌徒
第五章 癖好
第六章 闹鬼
第七章 黄粱
第八章 户口
第九章 宫女
第十章 留学
第十一章 同志
第十二章 宦者
第十三章 诅咒
第十四章 大门
第十五章 升迁
第十六章 盗宝
第十七章 末日
第十八章 子嗣
|
| 內容試閱:
|
第六章闹鬼
一
紫禁城里有鬼吗?这得紫禁城里的人自己说。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说有的人,言之凿凿,态度肯定:“有,肯定有,我亲眼看见过,亲耳听见过。”说没有的人,态度也很肯定:“你放屁,你胡说,你吹牛,真要有,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一个也没瞧见过。”
老李头、老孙头还有我,三个人是一个值班室的,晚上听着声控头报警器,保卫着紫禁城里的平安。这岗位,按我们处长的话说,得是政治觉悟高的人才能来。
老孙头原来当过公安局预审科的书记员;我呢,在工程队那会儿是个团支部书记;老李头呢,在没来紫禁城之前,是个园林局的政工干部。
我问过老李头,园林局好好的政工干部不当,跑这儿来值夜班,您岁数越来越大了,身子骨都熬坏了,图什么?
“图什么?图个心里痛快,不缺德。”老李头看我不解,便慢慢道来:“我原来那工作,缺德,太缺德了。什么叫政工?政工、政工,整人的工作就是政工。这个人有问题,不用说,整他。要是这个人没问题呢?那他总有亲戚朋友吧?做调查,查他舅舅,查他大爷,查他三大姑七大姨,不信找不出点褶儿来。常儿啊,你知道那些年我害了多少人吗?我不想,可我干的就是这么个工作,我能跟领导说,老子我不干了,我不想再害人了?!”
“那您后来是怎么想开了,来这儿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吓得我几天几夜没合眼,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调走了。”
“说来听听。”
“我们园林局,有个小伙子,也不小了,三十多了,还不结婚。他以搞对象为名乱搞男女关系,祸害了不少大姑娘,有本单位的,有外单位的。后来派我去调查他,唉,从他们家根儿上就不正,有作风问题,他爷爷新中国成立前嫖娼逛窑子。不是有句老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吗,我想是有些道理的。我把材料交上去,前前后后给了他三次处分,入档案的那种,领导最后一次警告他说,只要再有一回,开除不说,还要把他送到派出所当流氓抓起来。”
“后来他改了?结婚了?”
“没有,有同事向我反映,说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他和一个女青年跟小树林里卿卿我我,我正准备去调查他,他却自己来了,手里拿着个布包。”
“呵,看来是给您送礼来了。”
“不是,他手里拿着个布包,拖着两条腿,很艰难很缓慢地向我走来,裤子湿透了,脚面上全是血。他走到我面前,龇着牙、咧着嘴,双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布包,布包里面还有一个纸包,他又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他一边打着纸包一边说:‘我再也不犯错误了,这回是彻底改了,我把错误的根源都带来了。’我们低头一看,没看出是个什么玩意儿,再仔细看看,是一块像紫茄子一样的东西,我们问他这是什么呀?他说:‘就是它老让我犯错误、被处分,我恨它!我要跟它一刀两断!所以我用剪子给它剪下来了!’”
“那东西?”
“对,就是那东西!”
“啊?!他把那个给剪下来了!他疯啦!”
“嗯,后来我们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也说他疯了。”
“后来呢?缝上了吗?还能使吗?”
“后头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家以后天天做噩梦,看见他拖着两条腿,手里拿着一摊酱紫色的东西朝我走来,我就吓醒了。不到半个月我就调走了,调到咱单位来了。”
“他应该跟您一块儿调来。”
“为什么?”
“当太监不用做手术啦!”
“哈哈哈哈,还真是……”
“还真是什么呀?”宿舍门被推开了,老孙头走了进来,打断了我和老李头的兴致。老李头瞥了他一眼,没再说话,转过身,翻看起了桌边的《武林》杂志,老孙头见没人理他,只好没趣地走开了。
二
老李头不待见老孙头,不爱搭理他,为什么呢?这得从一年多前说起,那时候我还没来紫禁城上班呢。
李师傅会武术,野路子,练得不怎样,可是喜欢。我是正经科班出来的,拜的是名师,打过比赛,在武术上我是有发言权的。
李师傅练得确实不怎么样,这得赖他老师,李师傅学的是八卦掌,是跟紫禁城里一个叫“宝爷”的人学的,宝爷比李师傅还小几岁,是个酒肉骗子,李师傅每请他喝完一顿酒,他便借着酒劲儿给李师傅走一趟八卦,李师傅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动作死记硬背下来,回去当作绝世武功一样练上了。
老李头三大爱好:走八卦、站桩、看《武林》杂志。日子一长,老李头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站桩,一边听警报器。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老李头敞开屋门,站在院子里,扎好马步,双手摆个“怀中抱月”,闭上双眼,耳朵听着屋里报警器的响动,他听得见吗?听得见,他心静呀,由于长年站桩,他耳朵比我和老孙头都好使。就是一点不好,大半夜的,一老头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有点儿吓人。可是能吓着谁呢,除了跟他一块儿值夜班的同事,没谁能瞧见这幅奇景。
老李头还不爱吃食堂,嫌饭难吃,他自己在院子里开火,架个锅,自己煮,自己吃。这个在紫禁城是被允许的,准确地说,是默许。尤其是值夜班的同志,有种种不便,应该照顾,开火就开火吧,只要能保证安全,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孙头为这个挺不高兴,因为老李头在宿舍炖点肉什么的从来不让他一起吃,当然,老孙头用老李头的锅煮完的鸡蛋也从来不让老李头一起吃。
一到下午饭点儿,老李头扎好马步,架起了锅,生起了火,合着眼,一边听着锅声,一边听着警报声,还挺悠闲。
这天,老李头还是和往常一样,扎好了马步,闻着饭香味,听着声控头里的动静,珍宝馆展区的大门一道道关上了,老李头在心里默念着:最里面养性殿的门关上了,有脚步声,那是封门的工作人员往外走呢,走到了乐寿堂,乐寿堂的门也被他们关上了,工作人员再往外走,到颐和轩了,颐和轩的门也关上了,再往外走,该关贞顺门了……老李头一边听一边笑,很得意地笑,我都知道他笑什么呢,他肯定心里想:神技,我这耳朵听声辨位的功夫真是神技!
老李头笑着笑着脸上的肌肉忽然僵住了,本该早已安静的养性殿忽然发出了响动!封门的同事正在关贞顺门,最里面的养性殿怎么可能会有响动呢?再仔细听,养心殿里传来玻璃移动的声音!不好!有情况!
老李头先是冷静了一下,给钥匙房打了个电话:群工部站殿的全出来了吗?钥匙房回他:珍宝馆的钥匙都还回来了,早没人了。
老李头的心沉下来了,这回是真出事了。老李头赶紧进屋,叫醒了正打盹的老孙头:“走,出事了,拿着备用钥匙,跟我进珍宝馆!”
老孙头傻了:“今儿可不是我的班,我跟你干吗去?真要是个歹徒呢?手里有刀呢?说不定还有枪呢!你还是上报吧,我睡我的觉,今儿不是我的班,跟我没关系!”
老李头急了:“你贪生怕死就别干这个活儿!就算要上报,也得先去现场看看是不是真有情况呀,万一不是歹人是只动物呢?那就是虚惊一场,咱俩落个心里踏实。真要是个歹徒能怎么着?你道我这几年八卦掌是白练的呢,一招‘老猿挂印’我就能给他撂那儿,你信不信?你不去是吧,我一人去,等我回来,我告诉处长去,你说不是你的班。”
老孙头慌了:“别别别别别,我跟你去,咱俩能有个照应,真要是有歹人,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注意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俩徐图之,徐图之。”
老李头拿着备用钥匙走在前面,老孙头背着报话机跟在后面。进了珍宝馆,一路开锁,直奔养性殿。
养性殿的窗台上有一把改锥,再看旁边的展柜,罩文物的玻璃还在,可是里面的文物没有了!玻璃有移动过的痕迹,应该是歹徒用改锥拧下玻璃,将文物取出后,又把玻璃安回去了。
文物不见了,老李头和老孙头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老李头摆了个双换掌,双掌一前一后,脚底下踢起了趟泥步,大喝一声:“嘿!看见你了!出来吧!”老孙头大惊:“瞎叫唤什么你?!不要打草惊蛇,先报警,先报警!”
老孙头用老式报话机报了警,几分钟后,驻扎在紫禁城里的武警把珍宝馆给围住了,又过了一会儿,紫禁城外面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锡庆门广场。刑警们一批一批地走进珍宝馆,最终,只留下两名新来的小警察在锡庆门广场停车的区域负责看车。
这一来,珍宝馆好不热闹,刑警们上房的上房,爬墙的爬墙,四处搜寻贼人的身影,却怎样也寻不到。经保卫处的保卫人员确定,玻璃罩里丢失的那件文物,是一枚“珍妃之印”。
珍宝馆这边热闹,停车场这边却静得吓人。两个新来的小警察窝在车里,浑身直哆嗦。
“哥,我有点儿害怕。”
“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又没让你去抓歹徒。”
“去抓歹徒我倒不怕了,人多势众,能壮壮胆。您不觉得这地儿静得有点儿瘆人吗?我听说紫禁城可闹鬼。”
“别瞎说!新社会哪来的妖魔鬼怪?!你是一名公安干警,还信这个?!你从小怎么受的教育!”
“哥,社会是新的,可这城是老的呀,您想想,新中国成立前再往前,大清朝、大明朝那会儿,皇帝老子奸死过多少宫女呀,老太监害死过多少小太监呀,多少个皇帝是跟这儿驾崩的呀,多少冤魂呀……”
“你别说了!新社会的人民不怕牛鬼蛇神!那什么,你把衣服给我披上,我有点儿冷……”
“哎,哥,你感觉到冷,说明我说的是有道理的。我妈从小就说我,说我招人讨厌,爱抬杠,谁也说不过我。这话不对,他们说不过我,是因为我说的有道理,我就爱分析问题。就拿今儿这事来说吧,他们欺负人,凭什么让咱俩看车,还不是因为咱俩是新来的,您说,这正是立功表现的好机会呀,盗窃紫禁城里的文物,天大的案子呀,大家一块儿去,把坏人抓住了,论功行赏,谁去谁有份。明摆着,最后没咱俩什么事呀,咱俩就是个看车的,谁让咱俩是新人呢。”
“兄弟呀,你这么说也不对,做人不要太虚伪,不要太功利。我觉得,人活着,能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没病没灾的,比什么都强。你哥哥我刚结婚没多少日子,唉,听说今天出警,要去紫禁城抓盗窃文物的江洋大盗,我这心‘咯噔’一下子,后悔死了,心想还不如昨天跟老王把夜班给换了呢,要不现在,我正陪你嫂子在家看电视呢。这一路上,我那心脏啊,突突的,感觉都快跳到嗓子眼这儿了,后来听咱队长说,让咱俩留下看车,我这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要说咱队长真是个好人呀。”
“哪至于呀。”
“怎么不至于?你以为他们这些人好去呢,有的人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敢偷紫禁城的人,你以为能是等闲之辈?那都是身上有功夫的人。”
“咱们的同志们有枪啊。”
“没用,人家能躲子弹!再着说了,你有枪人家没有?弄不好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呢?是一个装备精良的飞贼团伙!飞贼带着飞爪呢,会‘壁虎游墙功’,看见这墙了嘛,得有七米来高吧,人家一纵身,就爬上去了。就这么着……啊!有鬼呀!你看!眼睛还冒着绿光呢!哎呀妈呀!”
“啊!哥,我也看见了!往那边跑了,好像一动物。跑墙那头去了!哎呀!不见了!不见了!哎……哥,你快看!墙上站着一个人!鬼呀!救命呀!”
“别瞎叫!走过去看看,不会是罪犯吧?”
两个小警察的叫声太大,已经吸引了那个站在墙上之人的注意力,两个小警察下了车,朝他这边走来,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由于害怕从高墙上摔下来,他缓慢地移动着。
墙上之人从墙西头挪到了墙东头,又从墙东头走回了墙西头,两个小警察也跟着他一块儿移动,他走到哪儿,他们便跟到哪儿。一个警察大叫着:“不许动!你跑不掉了!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另一个警察拿着对讲机大喊:“队长,我们发现歹徒了!请求支援……”
僵持了一会儿,怕鬼的那个小警察发现情况不妙,那个歹徒好像在找他原先的上墙之路,想从原路爬下去。小警察四处寻摸一番,见地上有些瓦片,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琉璃瓦碎片,奔着那贼掷了过去,偏是那样凑巧,琉璃瓦夹着一股劲风,正中那贼子身上,只见那贼从七米五高的红墙上直摔下来,落地后,一动不动,瘫软在那里。
后来的事,全中国都知道了,那个人叫陈银华,湖北人,因盗窃“珍妃之印”,于1980年8月1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再说说立功的那四位大英雄,先是那两个小警察,因立大功,回去后被连升两级。这两个小警察一个怕鬼,一个怕人,据说怕鬼的那个小警察日后冲锋陷阵、勇抓歹徒、顶撞领导,很是勇猛,和同事吵了架怄了气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你们谁也甭牛,老子当年可是仅靠一块飞瓦就抓住了紫禁城大盗的人,你们谁行?”终其一生,直到退休,他也只是立功那次长了级,再未升迁过,倒是平平安安一肚子气地活了一辈子。怕人的那个小警察呢,连升两级后,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和同事、领导的关系和睦,人缘极佳,一路高升,做到了局级干部,在他快要退休的那几年里,不知是被什么人举报,说他为了儿子出国留学和包养情妇收受贿赂,最后下了大牢,那是后话。
再说说另外两名大英雄,老李头和老孙头。处长下了通知:“老李啊,你写份报告交上来,年底给你长级。”老哥儿俩乐坏了,一人一张报告交了上去,没过几天,处长来要当天的排班表,老孙头的报告给打回来了,老李头的报告给留下了。
老孙头找处长理论:“我和老李头一块儿去的,拿老式报话机报警的那个人是我,为什么把我的报告打回来?”
处长很和蔼地劝道:“孙师傅,首先您的工作能力和英勇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凡事得按规章制度办,那天的正班是李师傅。孙师傅您本来是可以回家的,您留在了岗位上,这说明您爱岗如家,这很好。李师傅去抓贼,您陪着一块去,还报了警,这说明您英勇无畏,这更好。我私心上是一百个想给您报上去,评先进、长级,但是我得按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因私废公,这是要交到院领导那里的,还是那句话,那天的正班是李师傅,很可惜不是您孙师傅。”
老李头知道了这件事很难过,有些为老孙头鸣不平,也来劝他:“你是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走的那一遭,都是为了工作,什么正班不正班的,他说那种话,是托词、是借口、是不负责任,领导不该说这种话,让人寒心。”
老孙头没好气儿地“呵呵”一笑:“你少跟我来这个,假惺惺!当面说好话,背后捅刀子!是你点的炮儿,对不对?是你跟处长说那天不是我的正班对不对?是你跟他说不应该给我长级的对不对?”
老李头涨红了脸:“你胡说八道,你诬陷好人。你亲眼看见他找咱俩要走的考勤表,傻子都能看出来他那是找借口不想给你长级,你不敢跟他横,就敢跟我能耐是吧,有能耐你找他闹去啊,我懒得搭理你!”
老孙头还真听话、真有能耐,真的找领导闹去了:“我不服!为什么不服?你知道警报响那会儿,老李头在干吗?在做饭!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贻误战机!如果他不做饭,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什么叫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就是那时候贼还没跑出养性殿,我就把贼抓住了。我不服,因为他做饭,贻误战机,导致驻扎的武警来了,外面的刑警来了,最后贼都跑到锡庆门了才抓到,还是外人抓到的,丢人!你选他当先进,我不服!”
对,老孙头是闹去了,但并没有把自己的先进闹回来,而是把老李头的先进闹丢了。
老孙头闹了没多久,处长开了一个大会,点名批评了老李头,让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因私废公,作为惩罚,把老李头调离了东值班室,调到了不太重要的西值班室,又念在他是老同志岁数大了,这个错误就不入档案了。
这件事在紫禁城里传开了,老李头从一个英雄一下子变成了罪人,被大家议论起来。
第三小队正队长魏“痔疮”长叹一声:“哎,老李头要是不做饭,坏人就抓住了。”
警卫队的齐仁颇有感慨:“贻误战机这种事可大可小,要我说,田处长这个人,对下属,够意思!”
全紫禁城最为愤怒的人要属看大门的刘大嘴,你听刘大嘴瞋目大骂道:“调离?便宜了他!这要搁清朝,那可是杀头的大罪,不对!是满门抄斩!这个老东西!”
三
我在东值班室上班,和老孙头一个值班室,但是我讨厌他。在一千多米外的西值班室,老李头经常来“串门”,教我一些使用报警器的知识,和他渐渐熟识后,我发现,我和老李头挺聊得来的。
老李头有时候会和我说心里话:“常儿啊,那事不赖我,你说能赖我吗?我在心里想过很多遍了,煮饭和听警报器,这俩事儿不冲突。我不煮饭,早到了那儿,那贼还是跑出养性殿了。你说时间耽误在哪儿了?时间耽误在我们俩往现场走的那段路上了,可是没办法,我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发现情况,勘察现场,员工守则上是这样写的。哎,这个老孙头。”
老李头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认真负责的值班员,我觉得他冤枉。
我和老李头有了共同的爱好,在老孙头不在的时候,拿他开涮,过过嘴瘾。
那会儿老孙头还在帮娟姐照顾她三岁多的儿子。娟姐则有空给老孙头做做饭表示感谢,一来二去,竟勾搭上了,老李头和我总拿这事来开玩笑。
“常儿啊,怎么不进屋啊,跟外边瞎晃荡什么呢?”
“外边空气好,我活动活动筋骨。”
“不是吧,你孙师傅屋里有客人吧,不方便进吧?”
“您明知故问。”
“哈哈哈哈……”
“您说,他那么大岁数了,还成吗?”
“成,能不成吗,你看他窗台上泡的那一大坛枸杞子酒了吗?补那个的!”
“管事儿吗?”
“管,那个是咱紫禁城里自己长的,野生的,比外边的劲儿大。”
“您试过?”
“我没试过,我跟谁试去啊,这个喝完了,要是没地儿出火去,能蹿鼻血的,我从来不喝那玩意儿。”
“您是不是也想喝那玩意儿啊,也想找个人出出火去?您说实话。”
“我没他那么缺德!他岁数大得都快当人爹了,这种事也就他能做得出来,禽兽不如,伤天害理!这是生活作风问题,应该入档案的。”
每每到这里,我和老李头便聊不下去了,因为他太气愤了。但我总是卑鄙地觉得:在老李头的内心深处,他其实是羡慕老孙头的。
老孙头知道老李头有多么地鄙夷他的人格,所以,一有机会,老孙头总是会发起反击。
有一天,老孙头很神秘地对我坏笑,问我:“没发现你李师傅最近有些不对劲?”
“好像是,李师傅最近有些情绪低落,爱走神。”我回答。
“他们家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老孙头的表情更神秘了。
“您又开始编派人家了。”我有些不屑地顶了他一句。
“谁编派他了?得,你不想听,我还不想说呢,拜拜。”老孙头转身要走。
“您别走!我想听,您说吧!”我原形毕露了,把老孙头叫了回来。
老孙头慢慢道来:“是他儿子出事儿了,闯了大祸,不对,是犯罪了,滔天大罪。话说,他儿子平时在学校里就是个小霸王,辱骂老师,殴打同学,你不信?你看他爹,一上班就爱摆弄他那个花拳绣腿,他儿子能是什么好东西?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咱接着说那小崽子啊,他在学校是个霸王,和学校里其他几个霸王义结金兰,祸害一方。那天呀,其他几个小霸王要给他儿子做寿,又觉得几个小爷们儿吃喝没意思,强行拉着一个女同学去了他家作陪,一顿酒肉过后,把那姑娘往小屋里一锁,哥几个把人家给祸害了!轮奸!七八个人轮奸一个女学生!公安局现在已经把他儿子和其他几个从犯抓起来了,这是重罪,知道判多少年吗?无期!死缓!主犯有可能判死刑的!”老孙头很自信地说。
“您又知道了,说的好像这案子归您判似的。”我又顶了他一句。
“没判过,但是我审过,我在东城预审科当过书记员呀,这种案子我见得多了,真的是会判死刑的!”老孙头更坚定了。
“您还见过什么案子?总不能全是轮奸吧?有没有通奸的?就是俩人都愿意,男的有老婆,女的有爷们儿,最后滚炕上去了,这该判多少年啊?”我一脸无辜地望着他,等着他回答我。
“这个……嗯……那就另当别论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犯什么王法了?碍着谁了?只要不被家里人发现就成,自由恋爱嘛。”老孙头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得不想再聊下去了,是我打断了他的兴致。
真的是这样吗?全是放屁,至少部分是放屁。没过多久,我找到了第三小队正队长,魏“痔疮”队长,向他打听起这件事儿来。
“痔疮”叔很气愤:“放屁!他还嫌糟蹋人不够是怎么着?他还嫌害不死老李是怎么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儿子过生日,请同班经常打闹的几个好朋友到他家过生日,那女孩平时跟他们嘻嘻哈哈惯了,也去了。喝多了开始做游戏,石头剪子布、单人我倒霉……谁输了就挨罚,能罚什么呀,都是大小伙子,还不是罚喝酒、蹲起、俯卧撑。结果,老李他儿子输了,该挨罚了,有一个同学犯坏,说不罚你喝酒,也不用做俯卧撑,罚你亲她一口,亲嘴,不许亲脸蛋。旁边的同学也开始起哄,叫好、拍巴掌,亲!亲!亲!老李他儿子借着酒劲儿,捧着女孩的脸,嘬了一口。女孩脸一下子红了,酒桌上的同学们狂笑起来,接着叫好,噢!噢!噢!女孩跟着大哭起来,怎么劝也不好使,好好一场生日饭,最后不欢而散。本来到这儿也就没事了,偏赶上那天参加生日的一个孩子嘴欠,回到学校,在班里乱说,说是老李他儿子跟那个女同学在家里打啵儿来着,先是班里的同学在背后骂她,男同学、女同学都骂她,骂她是骚货,随后,传言从一个班扩散到了整个年级,全年级的人都骂她是骚货。女孩一回到家就哭,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她妈问,闺女你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她闺女说,我让人给亲了,亲的嘴,全年级的同学都骂我,今天我从两个男生身边走过,走出有十米远,我听见他们在背后骂我,说我是骚货,我都不认识他们。女孩爹妈急了,谁也不许污蔑我女儿清白!他们上派出所报了案,说老李他儿子耍流氓,公安局就给他儿子拘留了。前几天,公安局来调查,调查老李头思想品质,我做了担保,他是老党员,紫禁城盗印大案他立过功,当了几十年的老实人。警察信了,回去后,考虑到老李他们家政治背景清白,把他儿子从轻发落了,拘留了几天就放回来了,连劳动教养都没有,现在已经回学校了。唉,要说也是报应,老李他没来咱单位前,搞了半辈子政工,查了半辈子人家家里人的政治背景,岁数大了,儿子出事儿了,人家来查他,你说是不是报应?”
“痔疮”叔说的没错。那可是八十年代,搞对象吹了,让人告到派出所都有可能把你当流氓抓起来判刑,真要是轮奸,真的就吃枪子了。
老李头的儿子没事儿了,可老李头他却消沉了下来,走路抬不起头来,甭管上班下班,总是没精气神儿。老孙头的精神倒是极好,逢人便讲他所知道的真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儿子平时在学校里就是个小霸王,辱骂老师……总之,他还年幼,不一定给毙了,但是,这辈子出不来了,该是没错的……
我有时候会去看看李师傅,找他聊天,他再也没有以前那样欢乐了,也不走八卦了,也不站桩了,连他最爱看的《武林》杂志也不买了,我和他聊天,是希望他心情能好起来,可无论和他聊什么,他都没有兴致,只是反反复复那几句话:我那天不煮饭,坏人还是会跑的……从我到我祖上,一直没有作风问题,我儿子怎么能亲人家女同学的嘴呢,这是随谁呢?家门不幸,家门不幸……
后来,老李头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掏心窝子说话,是在他要退休的那一天。
那个时候,声控头警报器已经被淘汰,换上了能看到影像的监控头报警器。有人说,以前好像有个老同志因为做饭报警晚了,像那样的重大过失,再也不会重演了,值班员可以准确地从监视器里发现歹徒的作案身影,并迅速报警,不会再贻误战机了。
由于这几年李师傅的低调做人,他很少能再引起他人的注意,仿佛紫禁城里没他这个人似的,由于声控头变成了监控头,东西值班室也早已废弃,李师傅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不再是值班员了。直到我送别他的那一天,那天他退休,我们俩像很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
“听说您退休了,我来送送您。”
“谢谢你,我本打算收拾好东西去跟你打声招呼的,没想到你先来了。”
“应该的,我叫了您几年的师父呢,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现在还记得,我刚来值班室那几天,您教我怎么听声控头,怎么辨别哪个是脚步声、哪个是老鼠叫唤……您那听声辨位的本事,真是神技。”
“常儿啊,我问你个事儿,是说现在声控头全都变成监控器了吗?”
“是,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现在也不是值班员了,倒是前几天我去监控室远远地看了一眼。”
“怎么样,能管事儿吗?”
“好,管事儿着呢,有一女游客打了个哈欠,我连她门牙都看见了。”
“声控头呢?那批声控头呢,他们怎处理的?”
“扔了吧,好像是扔了……嗨,不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吗,留着也占地儿,扔也就扔了,您操那份心干吗?”
“全扔了?”
“嗯,差不多吧,斋宫还留着几个声控头,余下的都扔了,换成摄像头了。”
“唉,你怎么能说它是废铜烂铁呢?它们为紫禁城服务了一辈子,说扔就给扔了?我也占地儿,他们用不着我了,把我也扔了。”
“您想多了,不就是个退休吗,您有空常来溜达溜达,来看看我。”
“我现在没用了,紫禁城不要我了,紫禁城不要我了。”
说完他便走了。
看着李师傅渐渐远去有些迟迈的背影,我以为,他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