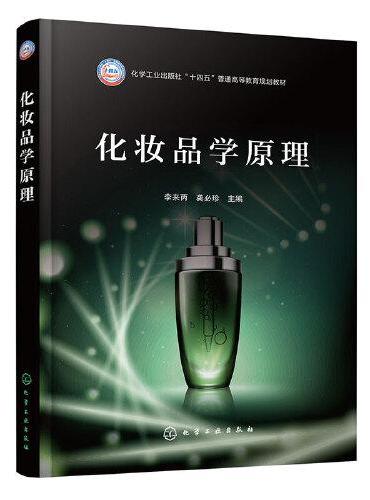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不挨饿快速瘦的减脂餐
》
售價:HK$
67.0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HK$
110.7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HK$
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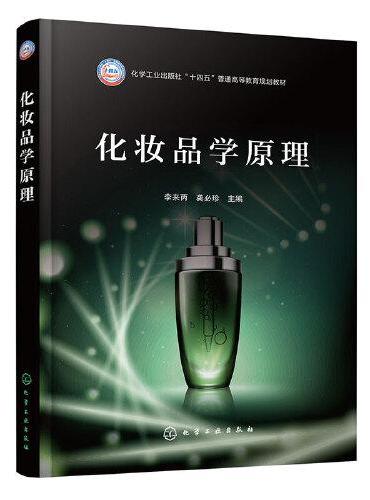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HK$
55.8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HK$
47.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HK$
55.8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HK$
55.8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HK$
109.8
|
| 編輯推薦: |
比肩《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
公认的古典现实主义巨著
百部传世文学经典
文化根脉 成长必读
|
| 內容簡介: |
|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吴敬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五十六回,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生活。《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世界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
| 關於作者: |
|
吴敬梓(1701-1754) 清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雍正诸生。早年生活豪放,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穷困以终。工诗词散文,尤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
|
| 目錄:
|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借灯笼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第十三回 蘧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姻亲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三 十 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第四 十 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里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典回家葬亲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五 十 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
| 內容試閱:
|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伙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顽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带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带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
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旁着实撺掇,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
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复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甚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
回复知县。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坐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跕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跕,七十里小跕,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到也挤个不开。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的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
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缕。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甚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
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淹淹一息,归天去了。王冕擗踊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棺椁。王冕负土成坟,三年苫块,不必细说。
到了服阕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一声,那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屯在外边,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不识,原来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贵步?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这日秦老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向年在山东相识的,故此来看我一看,说着就罢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道:危老爷已自问了罪,发在和州去了。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王冕接过来看,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着,天色晚了下来。
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蟏蛸满室,蓬蒿满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
元人杂剧,开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然与本事毫不相涉,则是庸手俗笔;随意填凑,何以见笔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
穿阔衣、戴高帽、叹黄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传内事,用来都不着形迹。
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贵。呜呼!是真其性与人殊欤?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
翟买办替时知县办事,时知县替危老师办事,各人办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穷书生得纳交于知县,诩诩然自谓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师而来也。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
学画荷花,便有雨霁湖光一段;将谪星辰,便有露凉夜静一段。文笔异样烘染。
秦老是极有情的人,却不读书,不做官,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第二回 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做薛家集。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殿宇三间之外,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后门临着水次。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个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这庵里来同议。
那时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约齐了,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到了早饭时候,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都还过了礼。申祥甫发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岁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阿弥陀佛!受了十方的钱钞,也要消受。又叫:诸位都来看看!这琉璃灯内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说道:不论别人,只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燎的滚热,送与众位吃。
荀老爹先开口道:今年龙灯上庙,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夏总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卸了鞍子,将些草喂的饱饱的。我议完了事,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起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说道:俺如今到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的腰胯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想是有事不得来了?夏总甲道: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他就是老爷面前跕得起来的班头。他抬举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黄老爹,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他家又无兄弟儿子,却是谁做主人?夏总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请。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说了半日,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道:这样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从前年年是我做头,众人写了功德,赖着不拿出来,不知累俺赔了多少!况今年老爷衙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个不了,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但你们说了一场,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任凭你们那一位做头。像这荀老爹,田地广,粮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分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众人不敢违拗,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余众户也派了,共二三两银子,写在纸上。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付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来。
申祥甫又说: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一个先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众人道: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只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也要人认得字。只是这个先生,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夏总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却还不曾中过学。顾老相公请他在家里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落后请将周先生来,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顾老相公为这戏心里还不大喜欢;乐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方才喜了。你们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请来。众人都说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筋牛肉面,吃了,各自散讫。次日,夏总甲果然替周先生说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约定灯节后下乡,正月二十开馆。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时候,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周进就问:此位相公是谁?众人道:这是我们集上在庠的梅相公。周进听了,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进再三不肯。众人道: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先生请老实些罢。梅玖回顾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
闲话休题。周进因他说这样话,到不同他让了,竟僭着他作了揖。众人都作过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摆两张桌子杯箸,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众人序齿坐下。斟上酒来,周进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扰,一饮而尽。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乃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叫一声请,一齐举箸,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一箸也不曾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为甚么不用肴馔?却不是上门怪人?拣好的递了过来。周进拦住道:实不相瞒,我学生是长斋。众人道:这个倒失于打点。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周进道:只因当年先母病中,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斋,倒想起一个笑话。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诗。他便念道:呆一字,秀才二字,吃长斋三字,胡须满腮四字,经书不揭开五字,纸笔自己安排六字,明年不请我自来七字。念罢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不好意思。
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该罚,该罚!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但这吃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个母舅,一口长斋。后来进了学,老师送了丁祭的胙肉来。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圣人就要计较了。大则降灾,小则害病。只得就开了斋。俺这周长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来,不怕你不开哩!众人说他发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预贺。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扛子火烧。众人道:这点心是素的,先生用几个!周进怕汤不洁净,讨了茶来吃点心。
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你亲家今日在那里?何不来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的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时运也算走顺风,再过两年,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当的了,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只怕还有做几年的梦。梅相公正吃着火烧,接口道:做梦倒也有些准哩!因问周进道:长兄这些年考校,可曾得个甚么梦兆?周进道:倒也没有。梅玖道:就是徼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彼时不知甚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于是,点心吃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灯时候。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向和尚说定,馆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
直到开馆那日,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了。周进上位教书。晚间学生家去,把各家贽见拆开来看,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勾一个月饭食。周进一总包了,交与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时照顾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气不了。周进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导。
不觉两个多月,天气渐暖。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河沿上望望。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红红绿绿,间杂好看。看了一回,只见濛濛的细雨下将起来。周进见下雨,转入门内。望着雨下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这雨越下越大,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芦席蓬,所以怕雨。将近河岸,看时,中舱坐着一个人,船尾坐着两个从人。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将到岸边,那人连呼船家泊船,带领从人走上岸来。
周进看那人时: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三十多岁光景。走到门口,与周进举一举手,一直进来。自己口里说道:原来是个学堂。周进跟了进来作揖,那人还了个半礼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进道:正是。那人问从者道:和尚怎的不见?说着,和尚忙走了出来道:原来是王大爹!请坐!僧人去烹茶来。向着周进道: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拿茶。那王举人也不谦让,从人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王举人道:你这位先生,贵姓?周进知他是个举人,便自称道:晚生姓周。王举人道:去年在谁家作馆?周进道: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王举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周进道:俺这顾东家,老先生也是相与的?王举人道: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又是拜盟的好弟兄。
须臾,和尚献上茶来吃了。周进道:老先生的朱卷是晚生熟读过的,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举人道: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进道:老先生又过谦了!却是谁作的呢?王举人道: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时头场初九日,天色将晚,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自己心里疑惑说:我平日笔下最快,今日如何迟了?正想不出来,不觉磕睡上来,伏着号板,打一个盹。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中间一人,手里拿着一枝大笔,把俺头上点了一点,就跳出去了;随即一个戴纱帽、红袍金带的人,揭帘子进来,把俺拍了一下,说道:王公请起!那时弟通身冷汗,吓了一跳。醒转来,拿笔在手,不知不觉写了出来。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
正说得热闹,一个小学生送仿来批。周进叫他阁着,王举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仿,俺还有别的事。周进只得上位批仿。王举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叫和尚拿升米做饭;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进道:我方才上坟回来,不想遇着雨,耽阁一夜。说着,就猛然回头,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仿纸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觉就吃了一惊。一会儿咂嘴弄唇的,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周进又不好问他,批完了仿,依旧陪他坐着。他就问道: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周进道:他才七岁。王举人道:是今年才开蒙?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进道: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开蒙的时候,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个王傍的名字,发发兆,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作不得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那里有甚么鬼神!周进道:老先生!梦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来,会着集上梅朋友。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王举人道:这话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进过学,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像我这发过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的了?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自这一番之后,一薛家集的人都晓得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进士同年,传为笑话。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荀玫了,都叫他荀进士;各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说他是个封翁太老爷,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分。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那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图他个逢时遇节他家多送两个盒子。俺前日听见说,荀家炒了些面筋、豆腐干送在庵里,又送了几回馒头、火烧,就是这些原故了。众人都不喜欢。
以此周进安身不牢。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那年却失了馆,在家日食艰难。一日,他姊丈金有馀来看他,劝道:老舅,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差一个记账的人,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伙内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周进听了这话,自己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有甚亏负我?随即应允了。
金有馀择个吉日,同一伙客人起身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周进无事,闲着街上走走,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晚间向姐夫说要去看看,金有馀只得用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领着。行主人走进头门,用了钱的,并无拦阻。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只因这一死,有分教:
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
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
未知周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起首不写王侯将相,却先写一夏总甲。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文笔之妙,乃至于此!
梅三相顾影自怜,得意极矣。不知天地间又有王大爷在。甚矣!功名富贵,宁有等级耶?
场中鬼跳是假梦,荀玫同榜乃真梦也。偏于假梦说得凿凿可据,转以真梦为不足信。活活写出妄庸子心术性情。
周进乃一老腐迂儒。观其胸中,只知吃观音斋,念念王举人的墨卷,则此外一无所有可知矣!
从吃斋引出做梦,又以梅玖之梦,掩映王惠之梦。文章罗络勾联,有五花八门之妙。
书中并无黄老爹、李老爹、顾老相公也者,据诸人口中,津津言之,若实有其人在者。然非深于《史记》笔法者,未易办此。
金有馀云:人生在世,难得的是一碗现成饭。此语能令千古英雄豪杰同声一哭,盖不独吹箫之大夫、垂钩之王孙为凄凉独绝人也。
到省买货,极寻常之事。偏偏遇着修理贡院,何其情事逼真乃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