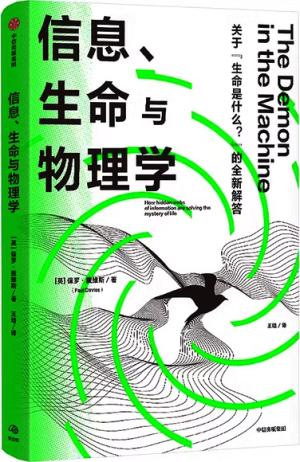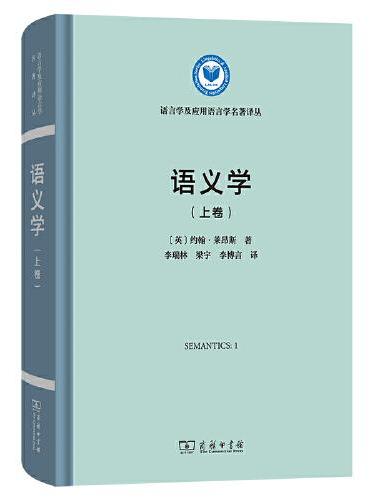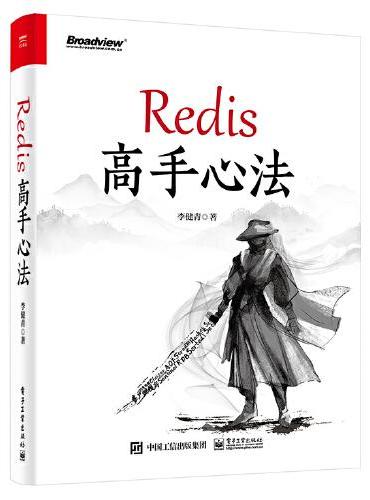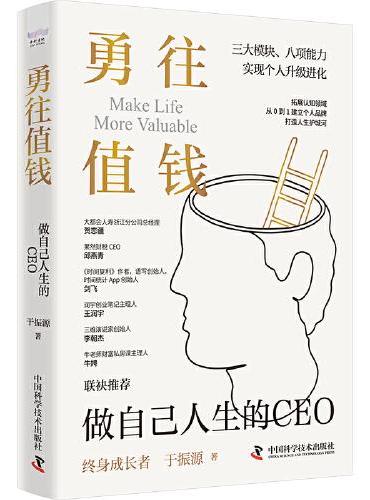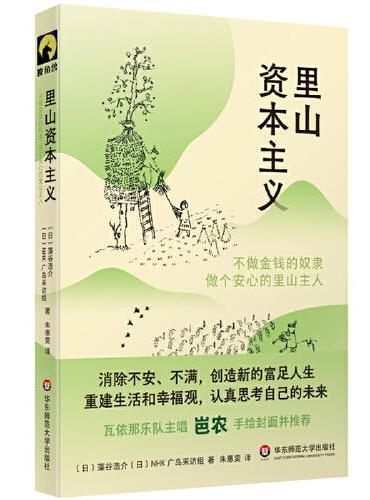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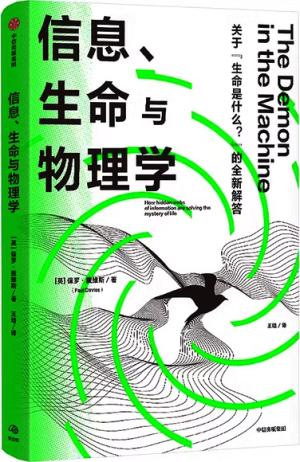
《
信息、生命与物理学
》
售價:HK$
90.9

《
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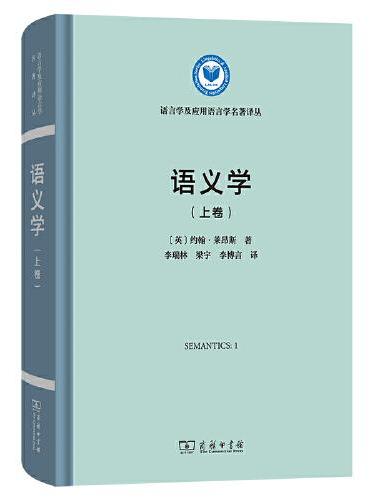
《
语义学(上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著译丛)
》
售價:HK$
1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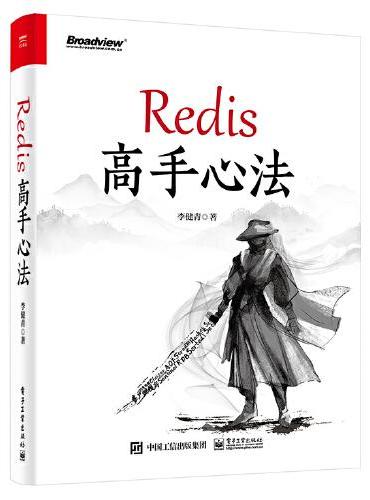
《
Redis 高手心法
》
售價:HK$
1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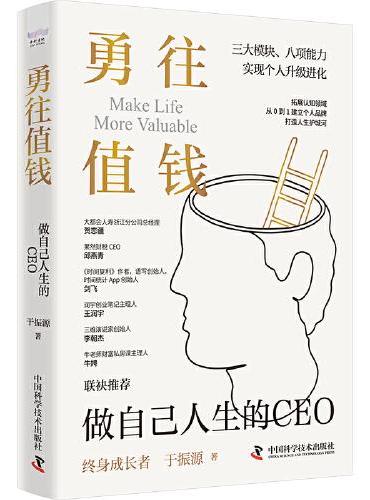
《
勇往值钱:做自己人生的CEO
》
售價:HK$
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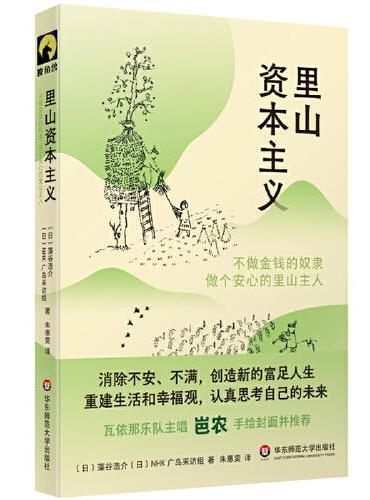
《
里山资本主义:不做金钱的奴隶,做个安心的里山主人(献礼大地)
》
售價:HK$
67.9

《
欧洲雇佣兵研究(1350-1800)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城乡图景或一首恋旧的挽歌,而是在深挚明净的笔调中洋溢着流水般的情致,折射着对历史变迁中的人事的思考,是一种自由与坚忍的生命力的宣扬,一种纯粹、明净、深远的爱的渗透。
|
| 內容簡介: |
|
《南方的河》是一部叙事散文长卷,在作者笔下,南方的河拥有着宽阔而又柔和的性格,而鲜活其中的,是河流上及河流两岸有血有肉的人和故事。生存、死亡、失败、眷恋、背离,是她在童年生长的河流边与离开后生存的城市中不断经历的悲欣苦乐。
|
| 關於作者: |
|
连亭,原名廖莲婷,壮族,20世纪90年代生于广西,求学于上海等地。自幼即爱好文学,写作源于日常关乎时代,展示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镀金时代的精神层面。在《散文选刊》《青年文学》《民族文学》《时代文学》《广西文学》《红豆》《山花》《飞天》《山东文学》《诗刊》《星星》《中国诗歌》等刊物发表多篇散文、小说、诗歌。
|
| 目錄:
|
灰姑娘1
陇头流水14
下水街27
有没有一袭桃花落在水中39
中间地带52
路边的浪子63
列车是略微颠簸的一种平稳71
镀金的孩子85
蝴蝶飞往何方97
悠悠桂林城104
那一代人的背影107
河岸116
没有靠岸的人121
风中的呼唤129
那街市的潮汐135
红色光晕140
原谅144
河流的乳房146
小渔村152
最初出发的地方157
台风160
文学的隐喻163
春天画廊169
樱桃河畔的秋风172
谁的眼在凝视175
南京,南京178
后记182
|
| 內容試閱:
|
灰姑娘
一
我家宅院以前很深阔,满院子影影绰绰的,都是些花草树木,围墙周遭密密地栽了许多玫瑰花,三五时节,一片清月,就升过氤氲的花丛来了。我时常在夜晚的梦里,被花香搅得睡不着,只是那是短暂的一段美好时光罢了。有什么能比时间和一把火厉害。
在那个寂静的中午,我趴在墙脚的玫瑰花丛里。看见一丝纤维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树梢上几只花雀扑棱着翅膀久久不归巢。偶尔传来几声狗吠,随即淹没在寂静里。门前那条路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转着圆嘟嘟的小脑袋幻想过那条路尽头迷人的天地,直到一些画面的片段消逝在晚霞中。我和我最亲近的人谈论过我儿时的这些举动,我说我迷恋一切温暖的光线穿过树丛或者屋檐的感觉。家里的挂钟悠扬而响亮地准确报时,响彻厅堂,再传入花园,和各种小生灵在地表发出的无数种声响交织在一起。阳光穿过树叶的优美线条在氤氲的香气中缓缓流淌,这时候的我会听到一首古老的歌静静地唱了起来。我的个子很小,因此离生动的地表很近,见过不少奇异的东西却不敢告诉我的父亲。比如一条带着鳞片的花蛇会在午时哧溜穿过花丛,使得我既兴奋又害怕。我从未往门前那条路上走得更远,农人驾着牛车缓缓经过门前,牛儿会高兴地叫一声哞,我就会咕噜从地上跳起来和它打招呼。一阵风从身旁经过,吹起片片绿浪,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声响,我开始有点困倦了,那些到处乱伸的玫瑰枝条不时把我的手臂扎得左右开花,午后从树叶漏下的光线也把眼睛刺得晕眩。于是我就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并且随便去到哪里都行。
我盯着一朵玫瑰的屁股,红红的往外翻,让我想到课堂上老师画得过红的那个嘴巴,忍不住嘿嘿笑了两声。那是一个刚专科师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女孩,已经膨胀的青春和这个小村庄不太搭调,记得她被年轻的校长甩了之后自己不会分辩自顾自幽幽地哭,哭坏了用制服擦眼泪,口红也跟着涂在袖子上,那袖子就像开了太多的玫瑰在颤抖。整个小学的时光是漫长而孤独的,等着老师扔下粉笔,等着下课铃,等着太阳落山。记得女老师用带着粤语口音的腔调教我们唱《童年》时,我们班最娇小而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女孩突然扯开嗓门大哭起来。下课的时候,我和班里最调皮的男孩们丢掉了对家长和老师听话的承诺,急不可耐地跑出教室,奔向操场,爬进树林,然后趴在草地上吁吁地喘气。我们都不喜欢上课。我背着书包从河滩上走过。听到父亲的叫喊就会躬下身子做出听话的样子。父亲照例会坐在门前的树下摇着蒲扇检查我的背诵功课。我念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他嗯一声,点点头。我念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他也嗯一声,然后点点头。要是哪一次我背不出了,他就会停下摇扇,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最后还会和我说祖父当年如何如何,祖父的祖父当年如何如何。我耷拉着两个耳朵,没有听进去。我倒是喜欢家里果园下的小河。有时父亲在月圆的时候领我去河边玩,让我偎依在他臂膀中玩他的胡子。
小村庄是一个河湾和一个沙洲组成的,村庄所有的一切都靠这条河孕育。在清晨,柴门开之时,可以看到各家里飞出鸡鸭,窜出猪狗,癫癫狂狂晃进树林滚下河滩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吃掉日出日落。然后,村里的妇人开始做早饭。烟从囱里钻出,飘飘摇摇,袅娜在树梢上,伸着懒腰拉到岸边的竹林,溶进水里了。鱼在水里做着蒙眬的梦的时候,或许闻到饭香了呢。这时,夜里出航打鱼的男人像是得了闻讯似的驾着渔船回来。进湾的船笛一响,就有许多光着屁股的男孩甩着褐色的鱼篓奔下河滩。河湾丰收的热闹里孩子们完全忘记了作业的枯燥。中午,渔村就给太阳晒得昏昏的了。渔船搁在河湾里,一浮一沉,一沉一浮,似乎世世代代就只有这个动作。村里人都在果园里或院子里休息去了。唯一醒着的,是不知什么地方的新蝉,拉着疲倦的调子,像妇女手中的纺线,织着一村人的梦。只有到傍晚的时候,渔村才会热闹起来。蝙蝠驮着夕阳织满暮色,鸟儿在路上寻找归巢。孩子们欢叫着在河中游泳,他们知道河底淤泥乌黑发亮,水草柔软得像母亲的乳房。晚风中,河边潮湿的滩涂上,丛生的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的车前草疯长着青春的萌动。空气中滑动着朵朵紫红色的影子。各家门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对岸在船笛声中愈离愈远,鸟儿在竹尖上,树梢上,船舷上,叽叽喳喳。
噢,父亲,这是你喂养给我的童年。
二
父亲经常讲起祖父。但是我脑中没有多少祖父的印象。只有一次父亲把我接回家时,祖父拉着我到村上卖水果的地方给我买了几个杨桃。我知道他是很疼表哥的,也就是我父亲的姐姐的儿子。表哥经常出现在祖父身边,祖父看着表哥长大,也许还因为表哥是男孩吧。我吃着祖父给我买的杨桃,一口咬下去,酸得要死,然后我想丢掉算了,但是我看着他的拐杖没敢这样做,那时我还没上学,没有他的拐杖跑得快。我最后记得他是他快要死的时候。我在外婆家的河滩上和伙伴们玩堆沙丘,突然父亲就出现了。他说我们要赶快回家,不是外婆家,是河那边的家。于是父亲和我没来得及和外公外婆道别,就先坐小巴后坐中巴回到河那边的家了。祖父睡在祠堂的大厅中,父亲给我两块钱叫我拿给祖父。我一路小跑到他床前,把钱给他,他没有接,我就塞到他手里,他一直看着我,我想他要和我说话,但是我等了很久他也没有说,然后母亲把我叫走了。不知过了几天,总之后来家里很热闹,许多人进进出出,头上戴着奇怪的白色帽子。有一天快中午的时候,突然锣鼓喧天的,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嘱咐我待会不要乱跑,也不许跟着大家出去。我一听就不愿意了,嘴上答应着,心里已经想着怎样溜出去了。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大家都忙开了,没有人管我,我跑到祠堂的大门边,看到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用金竹子做成的仪仗,上面缠着白纸带。于是我在锣鼓声最响的时候抓起一根竹仗先跑出了祠堂的大门。我跑得离家两百米的时候,气喘吁吁,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一看,几个人抬着一个黑色大柜子也出来了,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我怕他们把我抓回去,又向前跑了一百米。但是后面柜子和人都停下了,有些人又唱又跳,我看到姑妈在哭,又有人念念有词并抓起一个装有水酒的碗在柜子前的香火边摔破。我看得愣愣的,几乎傻了眼。大概过了几分钟,柜子重新被抬起,所有的人都跟着走动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跑到我前面去了。后来回到家里,祠堂空空的,没了先前的热闹,三叔公把我叫过去,说妹妹听话给了她二十元利是,我不听话不给我了。我觉得有点委屈,但是见他不和我玩我就走开了。过了几天我问妈妈爷爷去哪里了。当时好像是傍晚,妈妈指着家里烟囱飘出的烟和我说,爷爷在那里,还有红色的楼房住呢。我问妈妈我们也可以去那里看爷爷吗,妈妈说有一天我们也会去的。再过几天,父亲又把我送回外婆家了,我仍然在河滩、树林、花园和学校之间匆忙地玩着,就忘记要去看爷爷的事了。
以后父亲来看我的时候,和我讲爷爷,我不知道他在讲谁。很多人我都要喊爷爷的,卖冰棍的也是爷爷,五爷爷也是爷爷。父亲说他讲的是画像上的那个,然后他在我被他接回河那边的家时从抽屉里翻出爷爷唯一的没有经过装裱的画像,说,看,你的爷爷是这一个,参过军,他的病就是当兵的时候落下的,就这样早早地离开了。
三
我在河滩上花丛中玩着玩着,就被表哥打了。
我拿着玻璃珠一个人在花丛中弹来弹去,还把玻璃珠放到小昆虫的屁股上,看它们喷出不同颜色的雾气。这时候我听到表哥和表姐在吵架。他们经常这样的,有时候为一块饼,有时候为一个小玩具。这次我听到他们嚷着玻璃珠不见了。于是我赶紧把玻璃珠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只昆虫一跳一跳地转入了草丛。表哥大嚷,你拿了我的玻璃珠了。我看见表姐向地上吐了一口痰,一甩屁股,腰上一伸一缩扭回去了。我把玻璃珠藏在身后。这时候表哥向我叫起来:
大丫大丫
我低着头嗯着答应了一声。
表哥已经开始往这边走,我乜了一眼,表姐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和枯槁的玫瑰花瓣一般,更显得怪异。
你手里拿着什么。石头。我撒了一个谎。我仍沉迷于昆虫世界中,害怕他们把我的玻璃珠抢走。石头?你要石头干吗?他们开始笑起来。我爹叫我捡着玩的。
表哥突然变得很生气,将扫把丢到墙脚,把尘土扬得到处都是。你,一把火烧不死的鬼!
我看到表姐在这时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画得太浓的眉毛揪成了一团。一边说着还想用一半的眉毛去讥笑,结果眼睛拧成了蚯蚓。
我没有我没有拿我觉得自己在着急地辩解。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表哥突然大叫。
着急使我忘记了手上的玻璃珠,不知觉地手臂从背后掉下来。
好哇,你敢骗我。
他们兴奋异常,失禁的笑声倾泻出来。
就在表哥要抓起我的手的时候,我飞快地向路的那边逃去。拼命地向前跑,听见后面的喊叫,我没有回头,尘土扬起让我觉得路边的草像是飘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快要跑不掉了,便立住了脚,转身来仰着脸大口大口地喘气。
路的那边好像是一片菜花地,远远的远远的,我仿佛看到那朵金黄色的菜心。一只蝴蝶扑着翅膀在菜花里上下飘去。此时,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我乖戾地躺在床上,在一间被反锁的屋子里,然后沉沉地睡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现在红色的宅楼里,坐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穿着红色的大袍时端庄和雅静。我看到了自己,一张受惊吓而惶恐的孩子的脸在火中映得通红。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哭喊,而后寂寞如婴。
没错你跑什么,荒唐,火人!
记忆中那场火又开始燃烧。
房间里哭声一片。我在拼命地叫喊,我没错,我没错。我突然急切地希望着在那条路的尽头会突然传来母亲的声音,放了她放了她。但火光映红我的脖子,我也没听见那个来自遥远的声音。
我往门口望去,看见他们急切地往这边走来,他们在河滩的荒草里没有发现我。
我慌忙缩回了头,逃到石头的另一边。
南方小村落河滩上的石头一堆拥挤着一堆,黑乎乎,因年久而着满苔藓,像一个个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生活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它们着色。荆棘爬山虎一样不知不觉地堆满每一处空间。盛开着火红杜鹃和旺盛的仙人掌缠在一起,郁郁葱葱的绿色里时而露出斑褐色水坑,半汪水泛着刺眼的白光。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长得像母亲的女人,站在河边。阳光直直地从头顶射下来,把我打成银蜡样,我静静地趴在沙地上,呼吸低得几乎没有。我几乎要喊出来,可谁都知道我母亲在河那边的家里。火灾发生后我就一直被寄养在河的这边的。
做梦了吗?鱼儿刚把头拧过来,就满脸通红,哭泣着跑开。
花香在空气中一摇一摆地荡开。几滴亮盈盈的水珠落在我脸上,眼中的火还在燃烧。我的脸色有些发白,左手一直握着右手的拇指。
一颗石子落在水里,几只鸭子惊起,游走了。半河发亮的水晃了一下我的眼睛,或许我看错了,眼里泛出两点泪光。
哈哈,原来你在这。
表姐扯了嗓子喊:大丫,大丫快快上来。
我转过身,对表哥说:我不怕你。
表哥张大嘴巴看着我。我便哧溜地在表姐转过身前往下跑。表姐在我身后喊:快,快截住她,她在往下跑。
阳光白茫茫的一片。于是,我便使劲跑。突然在一块石头后伸出一条腿,把我整个绊趴下。想逃?没门。我被摁在地上,或许是我自己摔倒的,总之我倒在了地上,地上的沙土揉进我的眼睛里生生地疼。
表姐流着满头的汗走出来,他们把我圈在丘堆那棵唯一的苦楝树上。苦楝树结了圆滚滚的果实。有好闻的木青味道,从树干一个开裂的口子里渗出来。
我感觉我的玻璃珠被抢走了,我所有的宝贝都被抢走了。表哥打了我屁股三下。一辆客车在丘堆的不远处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男男女女的大人们吃惊地看着表哥打我。
树后面探出一个脑袋,使劲地喊,声音像一口洪钟:
胡闹什么呀,快回家去。吃饭了,大丫,再不听话告诉你爹!还有你们,别缩着头,不伸出来就不认识你们了
是大爷。
玫瑰花香在大爷的叮嘱声中飘散了。表哥咧着嘴在笑,突然被石头绊倒摔了一个跟头。
我在回去的刹那,回头看了一眼河边的水花。我突然拼命地向那条很远很远的路喊了一声:
娘
四
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风潮刚刚撕开南方的云雾,我在小平爷爷第二次南巡的讲话声中诞生了。大爷的收音机立着一条天线,小平爷爷的讲话声就从那里出来。
那天,大爷关好收音机,来到自家田头,看刚插下的秧苗在风中婀娜地摇摆,看油菜花在嘤嘤的蜜蜂阵下花香四溢。那些大的花朵在风中彼此推搡,一朵的脑袋磕碰到另一朵上。大爷感到一种灿烂得要死的生命。
是的,那些生气勃勃的油菜花,仿佛一片在绿色的草地上摇曳的火焰,它们反抗着土地,推开大地的窗子,被暖和的阳光点燃,卷曲又卷曲,呵,在光、影、声、色中,赤裸而灿烂地绽放。
大爷卷起袖管,摘了一朵花骨朵儿,塞进了衣袋。那个衣袋还放着它的烟管,于是花香和烟味弥漫他的那个早上。
正午时刻,他看到表姐气喘吁吁地跑向他,嘴里喊着:阿爸,阿爸,姑姑生了,姑姑生了,是个女娃
我在正午阳光最耀眼的时候诞生了,在母亲身旁迎来了自己的段落。祖母从箱子里翻出一块大红布做我的襁褓,那是我祖母几年前缝的,颜色像太阳一样又红又亮。祖母把红色襁褓裹在我身上,光线微弱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
父亲走了进来,在长长的午后,父亲就坐在母亲的身边,我和母亲都在床上安静地睡着。祖母开始在家里的门窗上都放上桃叶和艾叶,整个坐月子的季节母亲和我都浸润着这股清香。在我以后成长的日子里,祖母每次都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发辫上系上红头绳。我挂着祖母的红头绳,跨出家门,在花园和村弄一带燕子一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进入了校门,然后我就长大了。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首海子的诗,叫《门》:
一块白布
自负地挂着
等着夜晚
等得穿红小褂的男孩
发现了墙上的玻璃碴
沿着一条灰白的路
成熟的黄麦秸
收藏起他
另一端是种地的妈妈
那健康的眼神
许多人的童年大抵如此,只是我在两个家庭之间来回住着,好像我的成长也被两条线牵着一样。
我上学的时候祖母就曾给我扎过红头绳,然后傍晚会在门前等我回家吃饭。我总是太淘气,总要她一遍一遍地叫唤,才慢慢地告别同伴回到家里。
祖母的坟头在油菜花的尽头,坟上长着两株桃树,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坟上落满了桃花。在四月初昏暗的天空下,父亲的神情肃穆而阴郁。
关于火人的传说发生在祭坟之后,那会儿坟上燃过的纸灰还有余温。风吹过,纸灰扬起来,变成凌空飞舞的黑蝴蝶。长在那个年龄的我,没能理解父亲的神情。
风从油菜花丛中穿过来,在祭祀后安静的大宅院里东碰西碰。母亲在寂静的夜里听到一阵沉闷的轰鸣,然后是火燃烧的清脆的毕剥声。母亲一边叫醒父亲,一边冲向我的房间。我是在睡梦中被救出宅院的。至今我仍然不明白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只是那一场火一直在我梦里燃烧着。这场火为我植入了超乎寻常的幻觉基因。
父亲阴郁着脸,祖母留给父亲的所有家财全部化为灰烬。
五
我们的家总是那么大的,还远远地分成两边住着。大爷永远是家里的主儿,从祖母在世时就一直是。祖母生了四个孩子,大爷,父亲,姑妈,还有小叔。小叔在60年代那场饥荒中死于瘟疫,祖母只留下了三个孩子。祖母的娘家以前是地主,祖父靠着岳丈操持农庄果园积累了不少钱财。祖父在当兵的时候染上了肺病去世了。于是大爷成了家里的老大。祖母死了,祖母留给父亲的东西化在火里。从此父亲没有大爷有钱。大爷是好人,很多次都是他把我从花丛中叫出来,然后塞给我一颗糖果或者一个饭团。表哥欺负我的时候,他拿着鞭子教训孩子,但是鞭子从未真正打下来。只是在我的幻觉里,却感到隐隐的伤痛。
大爷从来不会骗我,父亲就会骗人。有一次,父亲领着我在油菜花的田头耕作。家里地太多了,总要请些村中的妇女来帮工,那些妇女每天能在大爷那里领三十元钱。在90年代,那是不小的数目。那天,风吹着大爷曾感到灿烂的油菜花,十来个妇女穿着花色不同的衣服从油菜花间隔的小路走来上工。我在田头玩着泥土,突然父亲叫住我,说母亲来了。我问他母亲在哪里,他说就在那群妇女中的一个。我看向那群妇女,里面没有母亲,而父亲却仍笑着说:是的,就那儿。我继续看过去,我看到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我看到几个女人在油菜花上变成风浪向我移来,慢慢地,移来。渐渐地我真的看到有一张脸是母亲,于是我喊了出来:妈!妈!我听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那笑声使我眩晕。父亲也在笑,他说他是看我想不想母亲才这么说的。
母亲一次也没有从油菜花的小路尽头出现。我的童年里就种满了油菜花。
有时我总在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把我寄养来寄养去的呢。我一遍遍远远望着油菜花地,想着这些问题,想到泪水全无,被大爷召唤回家。
在花香中我产生太多幻觉了。我想我什么时候把花香还给花朵呢。
90年代,村里的刘姥姥还活着,她是村里有名的仙婆。在那片灿烂的油菜花香中,她为我算了一卦,领了大爷一百元礼金。她说,正午的火太旺,会给这个家带来一把火。
是的,父亲的家财被一把火烧了。长大后我离开了那个遥远的村庄。家乡的风总是比家还近的。我想把自己归还给那个家,然后那个家把母亲归还给我。我和母亲,还有父亲,在灿烂的油菜花地笑声灿烂爸爸叫油菜,妈妈叫玫瑰,然后我叫蜜蜂
六
很多年后,我从大学回家看望他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没有很好地解释火人的传说,我依然是火人。火人很想念油菜花了。
我在回家的火车上翻看着地图,却不能在地图上找到在东南的僻远之地的那个村。它太偏远、闭塞了。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块土地还是被现代化远远抛在一边。地图上只能看到黔江和坡陌岭从西北南三面围拢起来的部分,大概就是它了,东面毫无遮拦,是留给外界的通道,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鱼篓。一个村,一百来口,占着数不尽的土地,南方地广人稀之所。祖上跑路时从福建莆田迁居于此。而这个村繁衍至今也不过百来人,多的都往外面搬迁,像我一样。这里山林漫野,遍河鱼虾,人烟稀少,傍晚,江天薄雾轻笼,半钩新月初上,父亲说当时的祖父,念及多年前的旧事,劳歌一曲老班人啊不容易,两条腿走几万里。半支船橹伸进水,捞起鱼虾换菰米
下火车后,坐中巴,再转坐三马,到村口的时候刚好是傍晚,鱼篓敞开着。
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通红的一轮,周围涂着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晚风抚过,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归鸦驮着夕阳,蒙着一层薄暮的橘香,游荡在蛙声和云霞充斥的渔村。广阔的田野袒露着结实的胸膛,稻谷在它宽广的怀抱中温润如绸缎。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间小路若隐若现,谈笑声此起彼伏。一个辫子长长脸色黝黑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挑着玉米从我旁边经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玉米在霞光的浸泡中更加红艳逼人。
见到父亲的时候,他正在一口泛红的池塘边牵牛吃水。看到女儿回来呵呵地笑了,嘴里空洞洞的,像许多空白的岁月。他老了,欢喜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霞光。
妹仔,归家啊!
妹仔,困莫?
妹仔,赶牛归栏,我们食饭!
那牛就从水中扭动着屁股缓缓从红光闪闪的水域中走上岸来,仿佛田野的新嫁娘,身上罩着红红的霞衣。从牛肚皮吧嗒吧嗒掉下的水,成了红艳的珠子。
吃过晚饭,我把椅子搬到黔江边的树下,靠在上面回味柴火烧出的饭香,一年到头在大学食堂吃腻了大锅饭,这烟火味真成了乡愁的味道,更何况父亲已经练成了手艺。
他确实老了,再也不是当年在河滩上让我拔胡子的父亲,再也不是看我淘气骗我母亲归来的父亲。
比不得你们年轻人跑世界哩,我们这班人只能和这屋子变朽咯尾音拉得好长。
在滚圆滚圆的月亮下,他说我是最乖的女儿。两滴浑浊的泪从他的眼角淌下来,在月光中闪闪发亮,魑魅魍魉。
我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时常流出浑浊的泪水。他的脸还是父亲的轮廓,但是多了许多皱纹,动不动眼角会流泪。他说倒不是因为时常悲伤,在高兴的当儿,甚至什么都没发生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的,然后举起和乡间泥路一样的手指,擦去眼泪,如同弹去身上的稻草。
人身上最承重的是脊梁。但脊梁隐藏在后背里看不见。它终日坚韧地弯成弓状,默默地承受背上沉重的压力。有时,在过重的负担下脊梁会发出咯吱一响。可是只要脊梁不断,便会把任何超负荷的重量扛住。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脊梁骨是被压断的。大丈夫是不会哭不会流泪低头的。父亲说这是祖父在世时常说的,这话支撑着这个大宅院的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
老宅子,轩昂的大门剥了一层又一层皮,铁链耷拉着,雕栏的屏墙旧得像崩塌的墙照,福建样式的天井,讲究的阴阳格局,朽坏的阁楼,在当年放铜镜的地方结着的蜘蛛网虽然只是些经历文革岁月之后的老宅,但是依旧隐约显出家族的血脉。
一个个残破的灯笼吊在屋檐,在一个个夜晚次第打开,搁在那里,曾经看子孙满堂。披着火的木头,像披着自己的肺腑。许多年过去了,江上空来去的月光流放随光落下的人影;许多雨走过了门前,尘埃冉冉升起来。
门外油菜花依然开遍。
七
娘
我还想对着油菜花地,远远地喊一声。
原载于《青年文学》
陇头流水
20世纪的末尾,陇头人和南河人在干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是记得零星的残片。那时的我才七八岁,读写课上语文老师一直在教我们说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可是我们不知道信息是什么。我只知道有外来人找村干部租山头种桉树了,后来村干部又鼓动大家把部分甘蔗地腾出来种上龙眼和葡萄。外公也一天天对着果园陷入了沉思。
陇头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南河那边的女儿,我是被父母寄养在外婆家的。陇头人说我之所以从小要吃外家饭长大是被逼的,被什么逼的他们也说不上来。那时除了我被寄养在外婆家,爸妈也时常要来回两边跑,而这些路途都是那一辆老凤凰牌单车走过来的。
我之所以被寄养在外婆家,乃是因为90年代初南方抓超生躲超生厉害。计划生育的施行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是贫还是富,想多要孩子的家庭面对此政策都得紧张起来,尤其那种传统的想要男孩的家庭,几乎是跟抓超生的打起了游击。我的家庭也不例外。我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妹妹出生了,我即被送往外婆家。我爸爸蹬着凤凰牌单车载着我妈妈,我妈妈背着我妹妹,我坐在架在单车横杠上的座椅里,那种座椅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东西,四个人穿行在一百多公里的路上,往返于我家与外婆家之间。车杠上架一个娃娃椅,把我放在上面坐着。有时会在路上碰到衣衫褴褛腥臭的乞丐。我要是坐在车上的娃娃椅里打瞌睡,爸爸便会吓我说要把我丢给乞丐,我则又拼命睁开我三岁的疲倦的眼。就在这样的路途中,我们等待妈妈早点怀上孩子,等待先祖的眷顾,等待我弟弟的降临。我无意于指摘计划生育政策,我也无意于指摘中国农村里的重男轻女观念。因为这些并没有减少父母以及亲人们对我的疼爱,我并没有像路上碰到的被抛弃在车站的女婴的遭遇,更没有一些小学同学被母亲弃于山中,又被其祖母抱回的遭遇。这些年岁除了增加我父母亲的奔波劳累,以及担惊受怕,并没有带来更多损害。河水教会陇头人要知足,要向前看。河床宽了,深了,只管向前流去,没闲工夫去斤斤计较。河水向前流,遇见绵延的山岭,则聚支纳流;遇见险滩阻石,则奋力冲过去,留下笑开的浪花。父亲是向我这样讲述陇头人的性情的。
1998年的3月,父亲带着我在河滩上转来转去,寻找到一个上平下斜的石洞。父亲把石洞下的沙子挖平,铺上干爽的细沙,细沙上架起木板床。第二天,父亲再把扎成屏风似的甘蔗叶沿着石洞斜面围起来,围成一面挡风的墙,对江的那面留道小门,门面用甘蔗叶和竹篾编织而成,一拉一扣,门就开关自如。待把一切准备好,父亲就带着母亲住进了石洞,那时我正在陇村小学上二年级。
每天,外公给我热好粥后,外婆把我从床上叫醒,帮我梳好看的羊角辫。我吃完粥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中午则跑下河滩看妈妈。
我的同班小伙伴叫方婷,她家在我外婆家的隔壁。她家一共有四个姐妹,一个弟弟。她是老三。她们家四妹妹小时候在我外婆家的池塘边玩耍,掉下去淹死了。他们家恨塘及人,大人们并不和我外婆家来往。只是她大姐和我表姐要好,她和我要好。
作为我的玩伴,方婷从未能进入外婆家的果园,但我会把果摘了放在书包里带给她以及其他同学吃。我知道表哥表姐有时也是这么做的。
199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1998年我发现妈妈的肚子好大好圆,像南瓜一样。妈妈再也不能坐在单车后面和爸爸一起奔波了,所以1998年的3月爸爸领着妈妈住进了河滩的石洞里,那里抓超生的是不会到的。
3月的河滩,小草已经爬满沙面了。妈妈住的石洞不远处的那一窝蜜蜂,已经开始繁忙地寻花采蜜。江水流过洞前的石头,绿草装点了河岸,在春天饮水的花朵构成了江岸的嘴唇。
季节繁茂如一位女神的头发,所有的生命都在经历妊娠前的阵痛。
住在石洞的母亲,每日每夜听见水从身边流过的声音,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她的身躯孕育,使这个春天的美变得更加神秘。春天原谅了所有人的错误,她优美的手臂借着树枝甩动着,和所有的人打招呼,摇摇晃晃的风中有迷人的花香,有一些船只停泊在桃花的芬芳中,连石头也在蜂群中起舞。
那是星期天的早上,妈妈从河滩上来,坐在外婆家屋后的苦楝树下给甘蔗种子剥叶,中午时说肚子有些痛,她就自己下到河边石洞休息了。由于产期没到,外公、爸爸两个大男人都没在意。妈妈又不是娇气的人,没什么事的话自己忍着惯了,她自己没说,外婆也不知道。下午,我便和爸爸一道在岭上种甘蔗。他吆喝着壮实的水牛,犁开土地,一畦畦的,从地的这头到地的那头。我弓着身子把甘蔗种子整齐地摆进畦沟里,从地的这头到地的那头。我个儿小,动作灵活,弓着身累了,还可以跪爬着摆,不像大人得始终弓着身得不到休息,因此小孩干起这活总是又快又好。一畦完了,又摆一畦,一点不都不需要爸爸敦促。下午五点多的时候,爸爸说要回家拿点东西,嘱咐我自己在地里摆甘蔗。我很听话说好,他就自己回去了。
我一个人又是弓、又是跳、又是爬地摆着甘蔗,可快活了。爸爸回来了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同。
天黑了,我把甘蔗摆完了,爸爸也给它们盖完土,我们就着星光驾着牛车回家了。爸爸驾着,我抓着牛鞭,时不时吓唬牛儿,好让它跑快点,实际上我并没打下去,可是牛儿它害怕,所以它就会走得快一点了呢。
土路弯弯曲曲的,又细又长,一条线一样延伸在甘蔗地之间。由于月亮白白胖胖的像大饼,水牛也显得高兴起来,哞哞叫了两声。我们的头上都顶着星星和月亮,我哼起自编的歌来,布谷鸟也时不时远远近近地传来叫声。从路过的每个窗户到每棵树,都可以看见星光、月光、灯光在夜晚中指路。布谷、布谷,它们的叫声总是伴随着春耕。好像是它们叫醒农人窗户里那些一个又一个厚厚的梦,潮湿地粘在一起,变成春雨洒在大地上,然后一点点地滋润庄稼。
夜晚的风凉凉的,我的毛孔似乎随着万物打开,我的肺叶快活极了。我看见爸爸一直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微笑中,像那些在夜晚中呼吸的树,那么舒展,那么柔和。
一束星光从树叶落下停留在我的耳边。爸爸把我揽在怀里,头俯在我耳边神秘地说:你有弟弟了,五点多的时候你有弟弟了,你妈妈给了你一个弟弟。
而至于妈妈如何在羊水破后,一个人在石洞的木板床上忍受剧痛,并发出只有黔江水才能听到的呻吟和喊叫声,我则不得而知。弟弟在大家都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意外地降临,只有妈妈和黔江水知道他是怎么来的。至于他为什么那么急不可耐地到来,我觉得是陇头湾的花香太浓了,把他都勾出来了。妈妈挣扎着拿水果刀割断脐带,他扯开嗓门哇哇地对着整个春天大哭,那厚足的劲头像渔艇出航的马达,白哗哗的浪花翻滚着,一路欢笑着尾随。
弟弟出生后,爸爸领着妈妈回到南河家里了。我仍旧留在外婆家里,在河滩树林玩耍的日子很快又淡化了他们,我是连弟弟出生的事都忘了的。外婆家门前的枇杷要熟了,我每天都惦记着要去摘它们。只有我宣布果子可以吃了,表哥表姐和其他小伙伴才能吃。这是由于大舅和外公外婆分了家产,所以属于外公外婆的果园里的果子,表哥表姐的权利已经在我之下,我是外公外婆养的嘛,我是最小的小孩,由于大家宠着,权利就最大了。就连别个村经过陇头湾时停泊的渔艇的船主,为了在外公外婆家吃上热饭,也会把水上捉的小鸟,用绳子绑了小脚,送给我玩儿。有一天我的小鸟连带着绳子挣脱我的手飞到枇杷树上去了,我连忙脱了鞋子爬到树上想把它捉下来。我三下两下地跟着它一会儿爬到树的这边,一会儿爬到树的那边。忽然它停在一挂枇杷上,开始对着一颗熟透的枇杷啄食起来。我一下子看呆了,我许久没见它那么快活过,我就让它吃着,自己则坐在一根较粗的树枝上,也开始吃起枇杷来。太阳渐渐热起来,阳光透过枇杷叶晒在胳膊上暖暖的,我越吃越欢,完全沉浸在这熟透的早春里,已经忘记飞脱的小鸟了。
许久,突然听到外婆叫唤我,让我赶紧换好衣裳准备出门。外婆已经把果园里的鸡生的蛋装了两打,另加婴儿的新衣裳两套,小毯子两件,全部打点好了。原来外婆要带我回到我家给弟弟庆祝满月了呢。
弟弟的满月酒是在四月底,桃花已经花枝招展地开过并纷纷扬扬地飘落了,这个时候酒窖里打开的酒,也带了桃花的香气的。照例是族里的人都回来,尤其是三姑六婆之类的。时辰到的时候,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大厅里,接受大家的礼物,等人都围拢了,祖父会在族人面前宣布给孙子取的名字。可是那时祖父早就去世了,于是爸爸在征得族里老一辈的同意后替代了祖父。爸爸对着众人,动作庄重,神情却很温柔。他把观音玉佩小心地拢到自己儿子脖子上,隔着一层襁褓,生怕磕疼了婴儿。随后他当着众人握着母亲的手说:谢谢孩子他妈。然后他站到八仙桌前面向大家,大声说:孩子取名叫庆生,族名随祖上排行洪字辈,叫洪生。于是大家欢呼起来,小孩子在人堆里穿来穿去的,差点挤掉我兜里的糖果。
我的太爷爷即爸爸的叔公接着说,这洪的排行可有讲究了。洪是洪武三年的洪。说是洪武三年的时候先祖廖盛泰奉当时皇帝朱元璋之命,从福建莆田调往广西任广西总兵,从此便在广西扎根下来。此后族里的读书人写了一首七律纪念迁居广西抚平岭南的功业,从我们这第二十四代起,子孙的族名依这首诗来排行,以示子孙不忘先祖之德。先祖在整个明代都是广西的武将,是岭南的名门望族,可惜清兵入关,最终连南明王朝也在桂林覆灭了,祖上救国无望,便隐姓埋名逃避清兵追捕。直到乾隆年间才有人参加科举中了进士,在清代,我们族里是出了三个进士的。
我突然想起去年我回到这边家里过清明,清明扫墓时,龙头山上盛泰公的高高的墓碑确实写着总兵、清逸将军等字样的,塘廉文公的墓碑确实写着某年进士的。老太爷领着族人祭拜的场面可肃穆了。老太爷燃上香烛,拿香烛的手的背上布满一根根的筋,像地图上的河流,仿佛还藏着某种祖先流传的密码。族人按辈分一列一列排好,老太爷带领全族跪拜,先祭天地,后祭先祖,追思颂德,一脸崇敬,我们孩子也鸦雀无声。祭拜完毕,洒三杯酒在地上,然后烧金银纸钱,鞭炮震天动地。清明后族里中年、壮年的男子守着祖坟,香烛持续烧三天三夜。
如今老太爷在弟弟的满月上讲祖先的故事,声音还如祖庙里的大钟那样,洪亮得很。后来大家就开始吃饭了,饭菜可丰盛了,按乡里的习俗是八盘八(就是八盘生菜配八盘熟菜)。我吃饱了自己蹲在门槛剥糖吃,我正认真地剥开糖衣的时候,一个城里的远亲领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来见妈妈。我看见妈妈原本幸福的眼一见小女孩就立马哗啦啦地掉泪,爸爸此刻在席上敬酒,只有外婆在旁边安慰妈妈。我心里感到奇怪极了,可是我又害怕得不敢过去。我躲到窗户底下,用手指沾了口水,湿破糊在窗户上的纸往里偷看。我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妈妈搂着小女孩哭,小女孩也是一脸诧异,只是她由于被妈妈搂着而她的眼睛正好对着窗户,她眼珠子看见我窗户洞里的眼珠子,咯咯咯地笑起来。她的手朝着窗户晃动,我看到她的手上戴着和我一样的红色玛瑙镯子。后来外婆告诉我她是我那被寄养在表叔家的妹妹。
五月里,外婆家的园子里茉莉花开,樱花灿烂。花瓣落了,被风吹到水里,黔江水咚咚地响。小孩子跳着,凌乱的脚丫印在河滩上,走出曲曲折折的道来。河边草更青了,绿色摇曳着长大,平铺在大河母性柔和的曲线中。过去的人曾经像一团沙子一样随着水飘荡,见到陇头湾便停留下来。他们像春天一样插在陇头湾的身躯上。放牛娃牵着牛在河边饮水,歌就朝他饮水的嘴唇流过来。
外婆家的房子,总想把自己藏起来,藏在那绿绿的果树林里,却总也藏不住。风一在林梢跳跃,花香就来了。风掠过河面穿过树林,几棵柳树展开容颜摇摆婀娜,铃铛在门角叮叮当当互相打着招呼,然后旧黄历在桌上翻了几页。黑燕子在纸窗户外飞来飞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木门开始潮湿,南风天在岭南漫天铺地地延展。于是有白色的一双手就从半掩的门外伸进来,带着绿色的苇叶,外婆要包粽子了。后来几只鸟飞到一棵树上,喜鹊叫了,从每个窗户到每棵树,甚至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中。悠悠长长的光阴里,花香、苇叶香和潮湿的空气附在每一个粗瓷碗,每一件旧农具,每一块土坯中,当然也在每一束昏暗的灯光之中,外婆粗糙的手中。
我和表哥表姐们在一片片花香和苇叶香中欢喜,外婆给我们包的粽子总是一般大的,不会因为是亲孙还是外家孙而有不同。吃完粽子,我和表哥表姐在河滩上跑来跑去,三四月的枇杷和桃花走远了,五月里还有茉莉和樱花。春天在我们的童年形成了一条路,让原本不同的成长拧到了一起,果园里的花香、果香就是就着苇香抱着一幅画,走到放声大笑的孩子面前来。
五月里,外婆坐在院子包粽子,我和表姐坐在树下面边唱一首自己编的歌边玩着几颗光滑的石子。下午有客人来,是找大舅的。那天没有什么招待的,大舅捉了外婆一只公鸡宰了招待客人。公鸡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从一个角落躲到另一个角落,最后终于被堵在了一个角落里,它逃不了了,最终成了那个外来客人的盘中餐。
外来客人到来的消息很快飞得很远,一直飞过院子的那棵树,飞过去的时候还擦过了我的头顶,一团热热的东西裹住了我的脸蛋。一泡鸟屎从树叶滑了下来。
我们运来几车桉树苗,你们这很适合种。桉树长得快,赚钱快,是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外来人熟络地对大舅说。
外来人离开家门后,外公摸摸索索地回到屋子里,拿出一本旧书,又坐到树下面念给我听。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要在树下背书了。
大舅张罗着在屋前屋后种上桉树。土地被一片片翻起又落下,那些从土地深处长出的水分被卷入贪婪的桉树根须里,土地还来不及从这些根须中更新,又被拉进桉树的另一场消耗。而桉树过分的消耗使它的领地里其他植物无法生长,连小草也住不进桉树的家里。这是大舅和其他村民也搞不明白的地方。
人想要变肥就把土地变瘦,可是土地瘦了人最终也要瘦的,除非人离开了土地,可是庄稼人离开土地能干什么呢?
庄稼人都是老实人,他们来不及多想,也不会多想,就在外来人和村委的鼓动下大片大片地种起桉树来。他们一如既往地勤劳,树坑挖得又宽又深,树苗栽得又正又直。每家每户的劳动力都出动了,连十几岁的孩子放了学,也要挑起水桶,下到黔江边担水上来浇树苗。大舅的堂弟老四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四舅妈,还因大表哥担水时不小心踩了他家的树苗,和大舅妈大吵了一架,害得大舅妈回来直数落大表哥,大表哥只好躲到我外公外婆家也就是他爷爷奶奶家吃晚饭了。
那些天,大表哥每天都得照看树苗,我则每天仍在外婆家门前的果树下背书,外公说下次爸爸来看我的时候是要检查的,而且我背好了将来还可以教弟弟。外公外婆一点都不忙,他们老了,并不想再种些什么经济林挣钱发家,只想守着老房子守着果园就行了。
桉树长得真快啊,种下去的时候还是筷子一样粗的小树苗,两个月后像太爷爷的拐杖般粗了,五个月像啤酒瓶般粗了,一年像粗瓷碗口那么粗了,两年三年已经长得直径十几厘米粗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卖给外来人了。花花绿绿的钞票抓在庄稼人手里,庄稼人脸上乐开了花,把瓦屋掀了,盖起一层两层的砖房。于是更多的庄稼人种起桉树来了。陇头人在日夜不息的黔江边开始一天天对着树苗地计划起来。
长长的土路已往的喧闹没了,在白日下变得更加漫长,村子的每个青壮年都在桉树地忙活,我总站在桉树地尽头等表哥和表姐一起玩,可是他们太忙了。
春天就要过去了,那个外来人没有再来。独臂货郎在天热后进村了,串门走户,摇着拨浪鼓,唱着歌。他原本以为小孩们会像以前一样迫不及待地从院子里跳出来,抢着买他的小玩意儿。可是一天过去了,孩子们都没怎么搭理货郎,他们在地里跟着大人学种地去了。天黑前,货郎收起货物,数着一小撮零散的纸币,纸币和他凌乱的头发在风中毕毕剥剥地翻动。我过去和他买了一个蔗糖做的唐僧,糖衣上面写着长生不老,那是我们这些迷恋《西游记》的小孩以前总抢着买的。现在我一个人可以随便挑,却总也不像之前那么兴高采烈了。我付钱时货郎对着我笑,露出漏风的门牙,越发傻了。我问他第二天还来吗。他说天要下雨了,没人买他的东西,他不来了。最后他说他去别的村子看看吧。我听了老大不高兴,他就多送了我两块唐僧,叫我留着吃。然后,他自己推着他的装货单车,慢悠悠地骑过长长的土路。
转眼夏天来了,南方雨哗啦啦下个不停,长江、珠江水暴涨。那是中国人熟悉的1998年洪灾。庄稼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武汉、梧州等城市告急。庄稼人说那河水都高过路和人了怎么行呢,堤坝怎么拦得住水呢,只有草木才吃得了水呀。
可没等大家在电视机前回过神来,黔江水也涨到家门前了。
陇头村人家都在码头的高地上,外婆家就在高地的果园里。家门对着黔江和码头,家门十米开外是下河滩的路,河滩到高地有差不多一百米高差,每年洪水猛的时候也只能淹到离家门四十米外,1998年破天荒地淹到家门二十米外了。这个中的原因,陇头人后来翻旧账的时候,才知道是桉树惹的。
为了多种桉树,村里人砍掉了不少河边的竹子。可是桉树是一种被称为地下抽水机的植物,耗水量非常大,吸收土层养分又多又快,水土在桉树扩张的地方不断流失。由于土壤贫瘠,且桉树落下的叶子和果实含有污染水和土壤的油,种桉树的地方经常寸草不生,一下大雨,雨水就哗哗啦啦顺着坡度流到黔江里去了。
黔江水不知不觉地漫过河滩,漫过桉树地,漫过妈妈住过的石洞,漫过弟弟出生的地方,冲到家门前了。有些在稍微低洼一点的人家,睡梦中感到床在浮动,放在门角的瓢漂到手边,惊醒了。天亮站在高地一看,黔江汹涌的河水变成了野兽。桉树随着江水的冲刷剧烈摇晃,许多桉树被冲断了,还有很多被江水连根冲走。
起初大舅带着大表哥划着渔船在湍急的江水中抢救养在林子里的鸡鸭,后来就什么补救也做不了了,他们沮丧地丢开船桨,愣愣地看着打着旋涡的江面,衣服裤腿都湿淋淋地淌着水。
在洪水的洗刷中,只有少数已经长得很结实的桉树保留下来,那些桉树长成后卖给外来人挣得的钱还补不上洪水带来的亏空。洪水漫过甘蔗地,村里几千亩的甘蔗长期浸泡在水中,这些甘蔗到了秋冬时节长得萧条萧条的,和往年比起来大大地减产。
在洪水包围村庄的日子里,只有我仍然是最快活的。陇头村点缀在黔江的一个沙洲边上,地形像敞开的一个鱼篓,除了水路外,只有穿过甘蔗地的路是村里到外界的通道。洪水期,潜伏在地下河的河水通过地形的漏斗涌上来,漫过甘蔗地,整个村庄被水隔绝开来,几千亩的甘蔗林处在水海里。爸爸妈妈那时候也不能从南河过来看我了,我没有了背书的压力,和表姐在甘蔗地边折纸船放在水里玩儿,水流带着纸船扎进我和爸爸种下的甘蔗地里,不一会儿就漂不见了。那水涨的速度让我们半小时往高处腾挪几米。
洪水退后,外婆家果园里的橘子熟了,像一盏盏小灯笼吊在树上。招来许多小孩聚集在外公外婆家玩。外婆把橘子摘了许多来,放在果盘里分给孩子们吃。一村子的疯玩嬉戏慢慢又从外婆家的果园开始了。
大舅看着桉树林被洪水冲刷后的狼藉状,又看看果园里橘树上缀满枝头的橘子和满园子钻的孩子,脸上一沉一暗的。我看到他点着一根烟坐在石头上闷不作声,就摘了几个橘子拿给他,他接过去放在石头边上,仍然继续抽闷烟。当晚他就去找了村支书,一夜都没回来。大舅妈可担心了,天一亮就叫大表哥去村支书家找大舅。
不久,大舅挂着黑眼圈回来了。他一回来第一句话就是:老子再也不种桉树了,谁要是再种桉树老子操了他家的地。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舅把桉树林地重新翻耕了一遍,大舅妈还带着表哥表姐挑着簸箕到甘蔗路上捡牛粪,他们把牛粪倒在千疮百孔的桉树地里,慢慢把地育肥,8月份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在地里种上西红柿和辣椒了。
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的3月,桃花再一次盛开,我和表哥表姐以及小伙伴们又开始更疯地玩儿。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表哥恋爱了。表哥什么事都瞒不过我的,我和他那么要好,我的指甲长了要他剪,我的木屐短了要他做新的,他是什么事都瞒不过我的呢。
我第一次在园子里碰到表哥和方婷她大姐的时候,一只蜜蜂正停在我面前的一朵桃花里,我的脸几乎贴到了桃花的脸上,蜜蜂窝在那里已经许多秒钟了,我在花和蜜的过渡里进行着我的幻想,但从来没有想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遇见他们。
当时春天的早晨像是亮澄澄的河水,阳光肆意流淌着。花枝如会唱歌的笛子,将一点点若有若无的朝霞,分割成带着些许温暖的手指,拂过人们时带来只有在被窝里面才会回荡起来的温暖。
他们亲嘴的时候连花都更香了。这些芳香几乎是从土地,从空气的各种气息,聚拢到我的脚下,然后从我的喉咙中冲出来的。
这花香不仅会影响我,也会影响大人们,甚至整个村的陇头人的。
磊落而温情的黔江静静拥抱着一座温存的村庄,为了他的儿女,他可以奉献更多的鱼、宽容和善良。
三月的尾巴就要被南风从陇头湾拖走了,蔬菜也一茬一茬地肥绿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