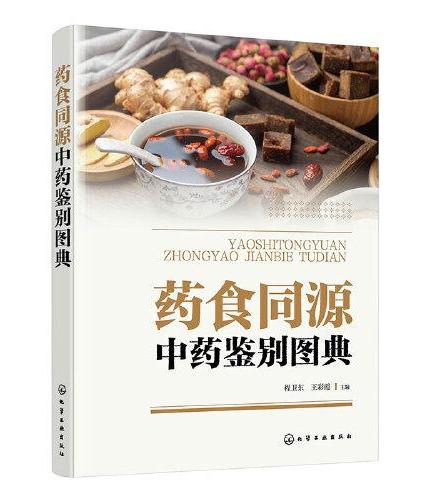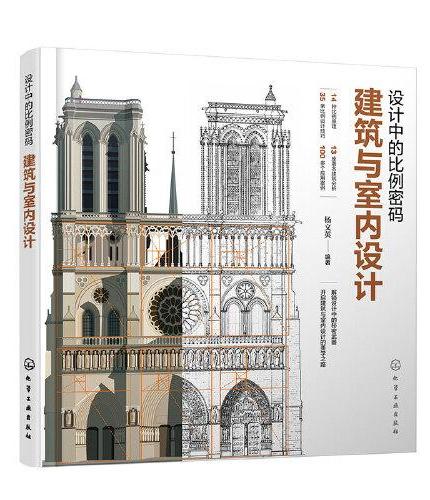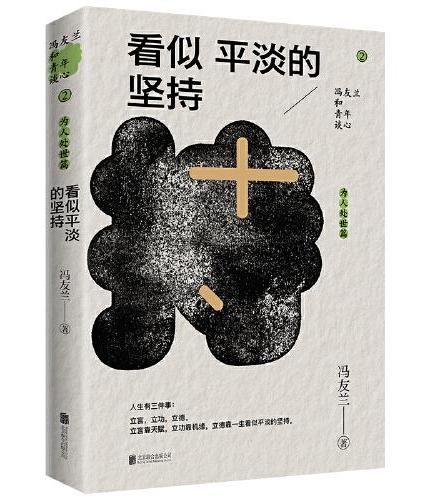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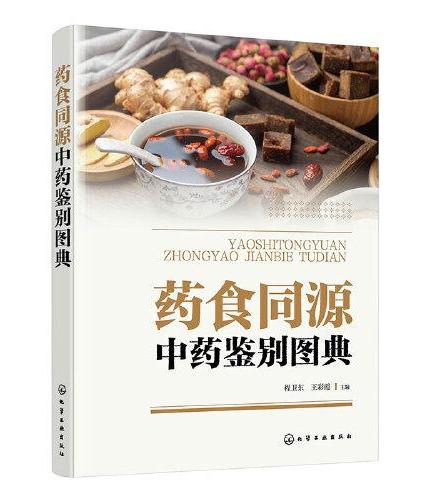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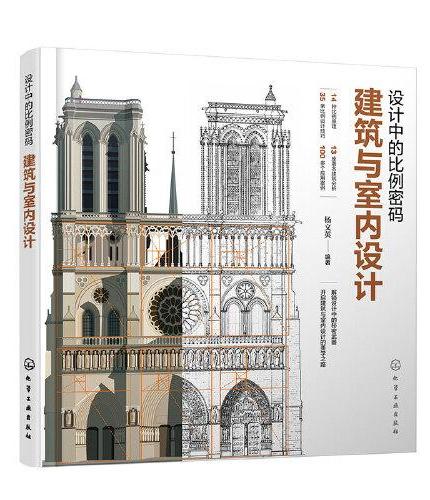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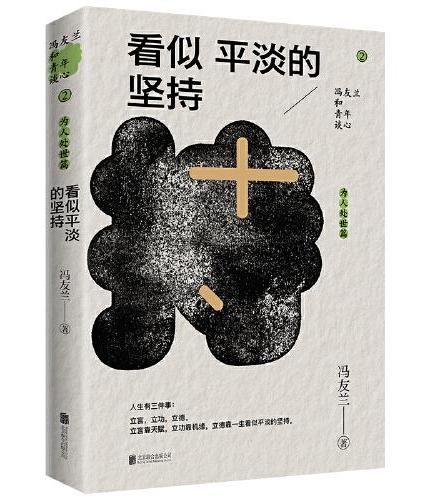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HK$
55.8

《
汉字理论与汉字阐释概要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作者李守奎新作
》
售價:HK$
76.2

《
汗青堂丛书144·决战地中海
》
售價:HK$
168.0

《
逝去的武林(十周年纪念版 武学宗师 口述亲历 李仲轩亲历一九三零年代武人言行录)
》
售價:HK$
54.9

《
唐代冠服图志(百余幅手绘插画 图解唐代各类冠服 涵盖帝后 群臣 女官 士庶 军卫等 展现唐代社会风貌)
》
售價:HK$
87.4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散文随笔作品集,集中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精心创作的散文随笔作品六十余篇,有很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地方风情,作者出身林场,对森林,对那片白山黑水和父老乡亲,都有着深厚的情感,生长地给了他文学的冲动和灵感,启发他灵犀一点,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便处处都有农家饭的香甜、家乡人的纯朴赤诚和大森林的宽厚丰饶。
|
| 關於作者: |
|
屈兴岐,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儿童文学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伐木人传》《祖母绿传说》,散文集《兴安雪》《七色光》,儿童中篇小说集《树海迷航》,长篇报告文学《金奖是怎样铸成的》《白森林告诉未来》《命运在今天决定》《三环大进军》《太阳传人》,另外发表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随笔百余篇。
|
| 目錄:
|
目 录
小屯逸事1
瓜秋12
乡间童趣16
春饼23
菜包饭26
豆儿酱29
育雏图33
尝鲜36
玉米秋39
又见红高粱41
流萤45
乡井47
冬之韵50
打年纸53
隐没了的行当56
告别了的生活59
远离了的什物62
源与流66
故乡的风76
落差79
怜爱81
主蔬89
牛冤93
雀儿趣97
太阳岛上看踏青103
云的家园106
歌号子酒112
大森林的色调126
山女131
山韵137
雪回来了143
河谷柳林146
巢营何处147
小鱼儿150
鱼眼152
石火153
永远的一瞥162
莽林风景167
向往净土171
心灵漫步大自然179
中州思絮186
愉悦190
溪水纯金192
岁月195
告别198
伞语200
田野遮阳伞下203
拜年208
红T恤211
门球场情趣215
灵犀219
酿224
三个兵站的站长227
满心胸的绿240
想念乌苏镇245
山崩地还在251
火红的中国结261
老人与客265
中东路遐思269
我知道你为了谁275
|
| 內容試閱:
|
乡 间 童 趣
一般以为,偏远的小山村,才闭塞落后。现在也许如此,旧时,尤其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就是平原小村,也像居于天涯海角,很少与外界往来。大人们都是这样,孩子们可想而知,周围放眼是茫茫地气,那以外有县城与其他乡村,但那是朦胧而渺茫的。然而,小屯里的孩子们,也自有他们的乐趣。自然,那多半是从祖辈父辈传下来的。
那时乡村孩子的乐趣,也是玩儿。天性嘛,与现在孩子相差不多,但玩法却有天壤之别。小屯孩子的玩法,可分为单独、结伴和集体这样几种。
先说单独玩。比如捉蝈蝈儿,人多相互干扰。亚麻摇铃、小麦泛黄、黄蒿涌动着暗香的时候,田野里、水壕塄上,便有成千上万小金铃摇动,此起彼伏,那是蝈蝈儿的叫声。男孩子们魂被招了去,就分散开去捉。侧耳倾听,拣声音响亮撩人的,猫着腰,猫一样轻手轻脚拨开庄稼或蒿草,猎人般凑过去。看见的时候,天不在了,地不在了,我不在了;在的,唯有眼中的蝈蝈儿,心免不了狂跳,要切忌毛躁。看准地形地势,决定是捧是压。捧,两手捧水似的,沿着植株慢慢上移,兀然一合。手中扑棱棱地撞,好,抓住了。这时两手尽量空得要大,免得手中物的大腿儿脱落,待它火性小了一些,再捏它头胸部。这一捏,也需技巧,轻了捏不住,重了要捏伤。迅速拿下掖在后腰上的笼儿,小心装进去。压的抓法,是蝈蝈儿在植株的中下部,忽地压倒一小片庄稼,就裹夹在里面了,这是笨招,“名家”多不用。笼儿呢,是用“箭竿”,也就是秫秸,自己扎的,方尖碑形状、尖三角形的都有。还有麦秸拧的,是个螺丝转的金灿灿的小塔。那多是有父亲或哥哥,还得是巧手的,有耐性的,其他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们那儿,有火蝈蝈儿、铁蝈蝈儿,还有青头愣,等而下之。火蝈蝈儿,头胸火炭般红,极少见,鸣声嘹亮清脆,我们很珍视;铁蝈蝈儿,黑而大,性情凶猛,发起疯来,可咬死同笼的同伴,鸣声高亢;青头愣长而绿,有胜于无而已。还有一种豆蝈蝈儿,生在青枝绿叶的大豆地里,短而粗,通体嫩绿,玉雕一般,只可惜鸣声吱吱啦啦,故弃置不用。
这时节,小屯有男孩儿的人家,家家茅屋檐下,挂着蝈蝈儿笼儿,笼上还插着嫩黄的倭瓜花,那是蝈蝈儿们的美食佳肴。于是,田野与村落,小金铃声连成一片了。
乡下的孩子,很少有玩具,制造小玩具,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玩法。我就自制过不下十种,材料匮乏,竹头、木尾、短铁丝、碎皮角,都金贵。工具呢,镰刀、菜刀、斧头,好在有尖端的,那是一把旧钳子。冷兵器,制过刀枪剑棍,拐子流星,当然都是木竹削的。还有柳条弓箭。较多的还是胶皮弹弓,先后有三四把。制弹弓的胶皮条,我们叫猴筋儿,是胶皮车轮胎剪成的,屯里哪有?只好托人从城中捎来。比现在托人从国外捎东西还难。费大劲弄成了,向苍茫上天奋力试射,泥丸带着风声消逝,兴奋不亚于科学家发射火箭。火器,木头手枪多把,有的有机头和扳机,能打纸炮子和红火柴头,有声有响有火药味。有了基础不愁发展,竟造了把“轻型”火药枪。枪管是妈妈的一个铜烟袋杆,小指头粗细。药囊是三八大盖枪的子弹壳。工期三天,组装顺利。软磨硬泡,从打围的炮手处,讨来一点点米砂和火药。试射场选在小屯后边,老杨树林里。有一只鸽子蛋大的蜘蛛,横行霸道在蛛网上享受满汉全席。目标就选它啦。我把小火药枪架好,像打机枪那样,两腿叉开趴在地上瞄准开火。轰然一声,目标灰飞烟灭。
我真庆幸,那以后,我还有两只完好的眼睛。
我还造过一只铅坨子,是玩“拒砟”用的。画一方志,每人下均等的砟,就是马掌锲铜钱之类,两丈远以外,画一条线,叫“杠”。站在杠外,用铅坨将砟拒出去就赢。乡间哪里有铅?吉人天相,偏遇我家有只铜灯台,约尺半高,为放得稳,底座做得挺大,还卷起一寸高的边。那时算,灯龄不足百年。与长信宫灯比,不伦不类,与“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那种比,恰如其分。我将那边缘剪下,剪碎,放在一只大铁勺子里,大铁勺子,是过去大人家盛菜用的。放在灶坑里做饭烧的豆秸硬火上,一会儿就熔化。事先在土地上掏一半球形大小适宜的坑。铅一熔化,轻轻端出,小心倒入坑内,冷冻后,一崭崭铅坨子,闪着青白的光,就出厂了。
说不上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我一心要造一把胡琴。我家有一旧的木茶筒。哪里找蟒皮去?只好蒙之以猪“吹泡”,也就是猪膀胱。好不容易,剪来一小扎长马尾,做了一个弓子,其余依葫芦画瓢,也都有了。装上后,怎么拉也不响亮。后来才知道,马尾上应涂松香。即便当时有松香,那声音也不会怎么美妙吧。
下一两场雪,小屯子周围,甚至屯边子的场院里,就有了野兔的脚印,是夜里印上的。前面两只成斜横状,后面两只顺着,在一条线上对得很齐。这样的两组相距一尺多远,说明它走得挺悠闲挺慢,两尺左右,它走得快了。六七尺远,前后两对足拉得很开,它吃惊了在狂奔。脚印有时密密麻麻,说明野兔至少有五六只。脚印中蕴藏着太多神秘,不由得让人想要把那主角,请到前台来看看。孩子们的办法,是下套。我也做过许多套子,用的是细细的铁丝。但没套住过,当时遗憾,现在却不。
雪下大的时候,田野中的野鸡就集成帮儿。它们飞不高也跑不远,追赶急了,将头往雪中一插,顾头不顾尾,就以为安全,一哈腰即可捡来。一次,我去邻村的学校上学,曾见几十只,扑啦啦落在一棵杨树上,红红绿绿,树杈积雪直往下落。这当然也是诱惑,但我们却赶不上,得另谋出路。大些的孩子,托人从县城买来野鸡药,匀给我一些,于是将黄豆粒儿用扁锥子一点点掏空,填之以药,撒到田野里野鸡常出没处。没药到过,当时遗憾,现在却不。
小屯房舍,多是土坯和“拉合辫”造的,用土甚多。年深日久,屯南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坑,水往低处流,遂成一个泡。岸上栽有杨树、柳树。有水就有鱼,唼喋于水面,自然更诱人。哪儿去弄的钩?好在咱是多面手,从妈那儿要根针来,灯火上烧红,一揻就成。纳鞋底的麻绳当钓丝,柔柔的柳条当钓竿。不管烈日当头还是细雨如丝,钓兴不减。因钩上无倒须,要一咬钩立刻就起。别说,还真钓上过几条,小小的山胖头,也就是老头儿鱼,出水就烂,却极高兴。
造毽子,要下些功夫,不然使不住。造“盘”的毽子,用四枚铜钱合适。嘉庆、光绪倒没大关系,要紧的是方孔大小一致。要事先物色好了狗,柔软的尾毛起码要三寸,黄色为颜色。不拘谁家的,狗对孩子们都亲。不亲也没什么,人托人可以进皇宫,找与它熟的孩子,给块干糖行点儿贿,它就摇尾巴。拉不动了,也差不多到毛根了。削一硬木小方寨子,分开根毛,楔入钱孔。将无毛的一面切齐(只有菜刀)。后一道工序,把切齐的毛根,或用烧红的烙铁烙,或在灯火上燎,这样结实,不“散花”。这样制成的毽子,盘起来,节奏舒缓,毽子一上一下,画出的路线极优美,看上去像花瓣柔软的鲜花,缓缓开放。下来,又像鲜花神奇地合拢了,合拢成花蕾。
踢的毽子,用五六枚铜钱,速度快。毛也有用马鬃、马尾的,速度过快,我们说“太贼”,容易伤人,不喜欢。
结伴玩的游戏很多。下五道儿须有伴。地头道旁,寻一平坦硬实处,用玻璃碴儿或小石子画一方框,方框里横竖各画三道,棋盘成了。你折五小段树枝,我折五小段蒿秆,棋子就有了。对面席地而坐,布好棋子,一场鏖战就开始了。游戏规则有几条,主要一条是两个先走到一条线上,同在此线上的对方的孤子,则被吃掉。先失四子者败。互不服输,常常一连几盘。放猪的直到猪进庄稼地,小些的直到妈妈喊着乳名,要他回去吃饭,输棋的一方,一脚抹平那棋盘,跑着走开。这算斯文的玩法。冬天打雪仗,到结冰的泡子上打“出溜滑”,春天到壕塄上扣鸟,夏天在泡子里“打狗刨”,秋天在田野里烧毛豆,孤烟直上蓝天,豆香麻子香香飘四野。
吸引更多孩子的大场面,要算打马仗与踢毽子。打马仗,人分两伙。个大结实的,当马头。另两个,各将一只手搭在马头的肩上。战头就骑在这两只胳膊上。单打独斗,三战两胜为赢。所谓胜,就是把对方拉下马来。有时候也决战,双方各出三五队,来场混战。呐喊声、欢呼声,半个屯子都听得见,这种游戏,大约源于三国故事吧。
踢毽子,在冬天。因穿乌拉,可以踢得远,脚还不疼。冬天虽农闲,农家也有不少活计。所以这游戏,多在晴天晚饭前进行。一个人踢,一个人在三丈远处给他扔毽子,叫“拾毛的”。踢的人对面很远处,很多人散开站着,谁接着,就耀武扬威“上台”。如被拾毛的接着,那应与踢的人主仆易位。看来机会平等。接毽子的,人人眼盯着毽子,有的用帽兜子接,有的兔子般弹跳起来,一只手凌空一掠,轻巧抓住毽子。他赢得一片喝彩声。皇帝轮流做,就看谁抓住那飞如流星的毽子了。户户炊烟飘后,暮色苍茫,孩子们才各回各的窝儿。
上面说的,好像都是男孩子。旧时,乡间女孩子游戏少一些,有一种叫“扯拉拉尾(读雨)”,也就是今天的老鹰抓小鸡。还有叫唧唧灵跑马绳的,今天也有,城里没了。跳八圈,特别是“抓(读chuǎ)嘎拉哈”,城乡均已不见了。嘎拉哈是猪后腿上一活动骨头。四面的名字各名坑、肚、支、驴。把一些铜钱,穿起来成一串,叫码头。玩时,把码头抛起,手去抓坑、肚、支、驴中的一样的,再迅速去接码头。后,以嘎拉哈抓得多者为胜家。有的人家,嘎拉哈有一两百对,一年才杀一口年猪,一两百对,得攒几十年呢。冬天热炕上,适宜这游戏。姑娘、娘们儿的天真笑声,隔着糊纸的窗户,在院中也听得见。这似乎是满族女孩子的玩法。
忽发奇想,如那时的乡下孩子,看到现在的城里孩子,玩航模、电脑、游戏机,不以为是神仙中人呀?
2000年4月
春 饼
每年春分前后,母亲必要烙一顿春饼。到时候,一年清苦的餐桌上,会神奇地发生变化,出现春饼与许多好吃的菜肴。吃了饼,才觉得春天悄悄爬到心头上,心里痒痒的,热酥酥的,直想要到风雪里去喊去跳。
现在想来,这一顿迎接春天的饼,母亲差不多是要筹措一年的。准备时,都笑盈盈的,好像乐趣在这家务劳动本身,绝不透露准备春饼的一丝信息。比如三伏天麦子上场,扬场后,她总要拣上风头的,精心留起小半面袋来。上风头的,籽粒成实饱满,磨出面来有“筋性”。春节前家人磨面,必嘱咐单磨单装。秋天,“家雀蛋”豆角,现今叫油豆角,叶子刚一发黄,就顶着露水摘回来,阴干个一两天,开始剪豆角丝。旧时农妇讲究炕上一把剪子,地上一把铲子,母亲剪子功夫,屯子里出名,所以豆角丝也剪得格外巧。别人家,一剪子下去,剪成细条就好,摊开晾在盖帘上,干了收起就是。母亲却能让一条条的豆角条,颠颠倒倒地,连成一条长长的丝,晾在绳子上,微风来了,像飘动的淡绿色的流苏。晾时要拣背阴地儿,秋风一溜很见干,三两天收起时,翠绿。
接着是秋收土豆、腌好酸菜,把上好的大葱,阴干起来,与东邻西舍没大区别。东北农村天冷,家家养着的鸡,刚刚三场白露一场霜,早早就“歇张”,不下蛋了,春天“开张”也晚。到春分前后,不是鸡下蛋的时候,而吃春饼,一定要用鸡蛋酱,鸡蛋新,酱才鲜。母亲也有办法。煞冷时,挑那“舔活人”(下蛋勤)的三两只,移到厨房里养,开小灶,又不冷,开张下蛋早。如果过年杀了猪,猪头二月二前燎毛,刮得焦黄,烀好。从外面玩完回来,庭院里有燎毛子味,外屋里,锅内咕嘟嘟的,飘散着肉香,就知道那顿春饼,与自己拉近了距离。
生绿豆芽,对农家来说,也要十分经心才可成功。水勤投好办,难处在温度不易掌握,放炕头怕热,放炕梢怕冷。母亲半夜时也要起来看一看。
农家春饼,是饼卷菜。饼要烙得薄软筋道,面粉早已选好,水温凉多少得合适。农家平日里省油,菜里见不到几滴油花,唯有此时母亲舍得用油。饼烙得薄的诀窍,是三四个剂子蘸好油,拍在一起,擀成一张饼,烙熟揭开单放。用平时做饭的大锅烙饼的时候,母亲眉毛上挑,满面春风,饼翻来翻去,手显得很灵巧。菜呢,一般是炒豆芽、炒酸菜粉、炒土豆丝,主要是家熬干豆角丝加肉丝细粉。肉食是猪头肉。母亲说,熏肉味道更佳。佐料只两样,细葱丝和鸡蛋炸大酱。没这个佐料,就没了这个风味。
几盘菜摆在小小的桌子上,只是那颜色,在早春里就够诱人了。白的洁白,黄的娇黄,绿的葱绿。再加上豆角丝带来的秋香,就更诱人了。母亲自己却不吃,帮着这个夹菜,帮着那个卷饼,一如做各种准备时那样,笑盈盈的。
离开家出来做事,才知那饼叫荷叶饼。母亲去了,再不能烙来给我吃了。去过几次饭店,好吃是好吃,然而没了那风味。后来妻就学着做,久了,竟然所差无几。现在虽是早已进了城,妻每到春分,总是要亲手做一桌农家春饼。
菜 包 饭
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主食的习惯大不一样。大体上分,是南米北面。我的一位熟人,浙江籍。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水电系毕业,志愿到边疆艰苦地方工作,分配到镜泊湖水电站。不怕冷不怕苦,很快由技术员升到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就一样不适应,粮食定量供应中大米太少。几年后回家探母,白发老母说可苦了我儿了!他说就是“没饭吃”,他说的饭,老妈妈自然明白是指大米饭,于是顿顿给他做,不几日就见胖了。与这个例子相反的,是1976年春节前,我陪一位好友去上海治病。住南京路附近一家饭店,一住三个月。一天至少两顿米饭。那米细而长,瘦得像粒米骨头。做成了饭,沙沙棱棱的,粒粒离心离德,谁跟谁也“不搭界”。吃进去胃就觉磨得难受,却难得有顿馒头。回来后他好了,我却得了胃病,一二年才好转,却至今未去根儿。
其实,龙江这里的北方人,过去也不是总吃面。因为那时麦子产量不高,物以稀为贵,总吃面一年要饿半年肚子。主食是谷子。
过去黑龙江人,一天两顿要吃小米饭。为了调节口味,妇女们发明了菜包饭。菜包饭包的也是小米饭,是小米饭的一种吃法。小米来自谷子,所以那时农村谷子种得特多,秋天晴时放眼一望,满眼是金黄颜色,遇有微风会涌起谷浪,谷穗沉甸甸地弯垂下去,摇摇摆摆,便有千千万万光点摇来晃去。除了像别的庄稼一样三铲三耥,谷子春天苗出个一二寸高,要薅苗拔草。因是宽苗眼散播,须去掉多余的比较弱的小苗和谷莠子。苗和谷莠子、稗草长得差不多,不好分辨,要格外留心。这个活要“小工子”来干,所谓小工子就是妇女。手拿一小小扒锄子,蹲在垄沟里一步一步向前挪,比锄地的男人要累得多,工钱却只拿一半。谷子这作物累男人的时候也有,那就是割地。镰刀磨得风快,一刀拽下去,垄台子一呼扇,随后腾起一团轻微的浮尘,没力气是干不了的。
小米的吃法多种多样。如早晚吃,一般是熬粥。有干粮时稀溜溜儿的,一个粒跟一个粒跑也行。午间多是做干饭。捞干饭是米下锅“扒拉翅儿”(基本软透),就赶快用细柳条编的笊篱捞出,倒进一个瓦盆,锅里米汤舀出来另放,或直接喝或熬汤都可。锅内放清水,瓦盆坐进去,盖好锅加火,大铁锅咕咕嘟嘟响到飘香气,就好了。蒸的饭散散落落,肉肉头头,颤颤巍巍的。还有蒸的和焖的,原汤在内比较香,不知为什么女人们不大愿意这么做。小米上水磨,可以抡煎饼,也是在大锅里做,铁勺子舀满浆面,倾斜着沿热热的锅腰转一圈,一张煎饼就成了。小米子泡上,发了酸时上水磨,一个木桶里盛小灰(草木灰),用一块大纱布铺进去,倒进浆水,不久,就成了一块柔软的面坨子。锅里烧好开水,架上饸饹床子,就可压打卤饸饹吃了,光滑筋道。太费事,也就是大热天时吃个一两次。
所谓菜包饭,就是用新鲜白菜叶,包上捞小米饭。也叫打饭包。一般也是夏天吃。初春种的小白菜,到了夏天就叫“春不老”,要拣那没让“地狗子”(小虫)咬着的用。要有香菜、生菜、小葱、炸鸡蛋酱,用菜叶包起来一吃,菜饭的原味全变了,只觉得清香可口,齿颊生津。一般说来,这是女人们的专利,男人们吃得没有这样精致,我还是在孩子时,母亲给我包过几次,却至今不忘。
谷子古时叫粟、禾、谷,特好的一种叫粱。颜色红、橙、黄、白、紫、黑都有,让人想起太阳。地道土特产,原产我国北方。谷养了一代代的人,谷草养了一代代的马。《韩非子》说,“征赋钱粟,以实仓库”,《广雅》说,“粟,禄也”。延安时期,革命靠小米存活,后来也是靠“小米加步枪”发展,可见米小作用大啊。
豆 儿 酱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家乡巴彦一带,庄稼人日常饮食,常见离不开的,要算是豆儿酱了。人们大约看到了它的重要,看到了它在寻常岁月中的分量,所以在酱字前面加了一大字,叫大酱。就像在老爷前加个大,在土匪前加个大,在财主前加个大,在土豪前加个大一样,上了一个档次。不要说在酱中它要居首位,就是在每家每户的实际生活和对外形象树立中,起的作用也不能说不大。
那时乡村,交通不便,就是一个小铺子,十里八村也是没有的。即便有,也绝不卖大酱。这种酱家家自制,即便日子富裕些的人家,也不去买。为啥?怕人笑话不会过日子呀。再说,买来的吃着不合口味。一家的酱一个味儿,吃惯了自家的,忽然就换一种,总觉得不是味。也有公认哪一家的酱确是上品的。大酱出了名,这家主妇干净利落,心灵手巧,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也就传扬到南北二屯去了,这家是过日子人家的声誉,自然也就有了。说不定儿子娶媳妇姑娘找婆家,也有人上赶着。所以,家家户户,院子大小、利落不利落尽管不尽相同,但是里面必在窗前安放一两口酱缸,则是相同的。家里的主妇或走亲戚或办事,走时件嘱咐的,便是叫女儿照顾好酱缸。她们在家门前房后劳作,赶上一阵云彩一阵雨的,必要喊一句哎呀妈呀我酱缸还没盖呢,赶紧跑回家去。酱缸一般用几块砖垫起,三根钉进地里的木橛夹住固定。罩一顶秫秸篾子编的尖尖的“酱帽子”,以防雨淋和过分的日晒。谁家酱缸被牛马毛了撞翻,那可是一大新闻。如因吵嘴打架,酱缸被砸破,不仅仇火越结越大,全屯子也要记个十年八年的,说这事干得太“损”了。这说明,在这里大酱是何等的不可或缺。后来有些人进城吃商品粮,定量分配,“定量”一减再减,每年也还给几斤酱豆,也说明酱在我们这儿的重要性。
黑龙江是气温低的地方。四五月开化,九十月雪花飞回来,接着又上冻。可种、可吃青菜的时间太短。秋日贮起来的白菜、萝卜、土豆,冬天没过去就没了。尤其“春脖子”长的苦春头子,大酱就成了主要下饭菜了。然而一年四季,却都有蘸酱的菜。青贮菜断了的残冬时候,可以吃冻白菜、冻萝卜。入冻前拣那些青贮剩下的,随意放在背阴背风的角落,场雪一落,就严严实实盖住了。用时从雪里扒出,仍然红是红绿是绿。洗净切好,放进滚开的锅里一炸,就好蘸酱下饭了。皮点儿艮点儿,却有一种特殊的清香,这清香一尝出来,便会想起刚一上冻时的天气。
“三月三,苣荬菜钻天”,几场春风,几个响晴响晴的太阳天,山东叫苦菜、这儿叫苣荬菜的一种野菜,出来帮助苦人儿了。这野菜在黑油油的土地上刚一冒锥儿,就可以去挖。小臂上斜斜地挎一只细柳编的元宝筐,放一把旧镰刀头夹以木把自制的刀,小姑娘们小小子们,仨一群俩一伙,各自找好“窝子”,孩子们眼尖手灵脚快,不一会儿就一筐。时间一长,筐里的菜有些发蔫。清水洗净再浸泡一会儿,就茎白叶绿水灵灵支支棱棱的,苦味也淡了些。野菜接下来是婆婆丁、小根蒜、柳蒿芽,连灰菜、马钱子也能吃。不久,羊角葱下来了,嫩绿的小菠菜下来了,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乡亲们饭桌上菜就不愁了。不过,大部分是蘸酱吃,因此酱碗在桌上的位置,就如毂在轮日在天,是个中心。
酱的优劣区分,也像其他菜肴一样,在色味香上。那些早已登上大雅之堂的名菜,烧起来也许要许多技巧,但大多是现做现卖的。我们那里的豆儿酱,做起来却要一年时间。
秋天新黄豆刚下来,筛净簸好洗得纤尘不染,用净水发上。待豆子涨得恰到好处,下到大锅里烀。水多少要正好,多了酱泥稀易营养流失,少了则酱豆不烂不易成泥。烀得将好未好时,那豆香气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从锅盖缝里钻出来。这时候孩子们该稳不住神了,眼睛溜着锅,从锅台旁走来走去。锅一揭开,满屋都充满香味。母亲用长柄铁勺勺背,趁热将满锅黄嫩嫩的豆子“插”成豆泥。她好像刚刚看见孩子们围着锅看,便撩起围裙擦把额上鼻尖上的汗,变魔术一般找出不知何时珍藏的红糖,从锅里盛出一点儿豆泥拌一拌,说尝尝吧。红糖豆泥的美味,让苦孩子们大半辈子忘不掉。然后是看母亲灵巧的双手,把豆泥做成酱块子。六七寸长三寸厚的长方体。过小不易发酵,过大让人笑话说懒老婆。一块块整齐摆在面板上,放在阴凉通风处,绷了皮、表面一层硬了,就用草纸裹好,用块板吊在屋里不碍事的某处,让它慢慢地从内往外发酵。
到了来年天暖,把酱块取下,洗刷干净掰开晾晒,再把大粒盐以凉开水洗净,就好下酱了。除了利用日光加温,每天还要“打酱缸”,工具是桦木制的酱耙,手握的一端还系一小条红布,是图吉利的,就像盖房子上梁要系红布一样。用酱耙子每天把酱缸翻动一遍,要均匀要彻底。还要随时将沫子、黑点儿有碍观瞻之类的东西,细心地撇出。
过个两三个月,豆酱比较稠了,色泽变得橙黄,有香味弥漫,就是大功告成了。
讲究人家有两口酱缸,做成后封起口来,第二年用,表面一层,比母油还要好吃。酱缸还可以腌各种小菜。母亲用纱布缝几个小口袋,装小辣椒、小黄瓜在里面,还有烀熟了的小土豆,凑巧有肉也装条煮熟的肥猪肉。其绵长美味,远非寻常小菜可比。
现在人们生活有所改善,酱菜一般都买着吃了,成了小菜一碟,是煎炒烹炸的一个补充了。但人们有时上饭店还点一道蘸酱菜,也许是一种回味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