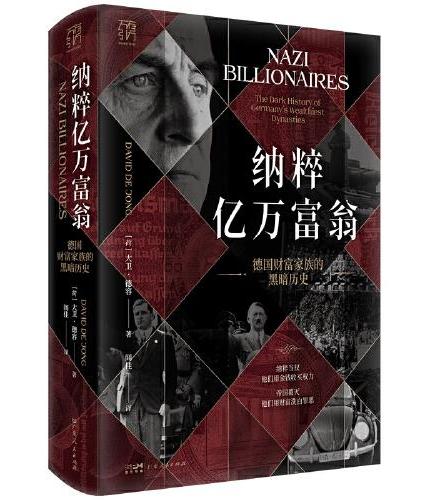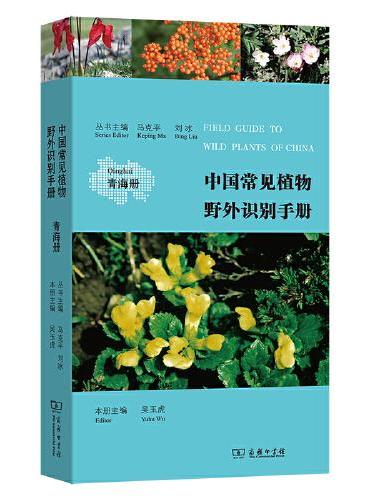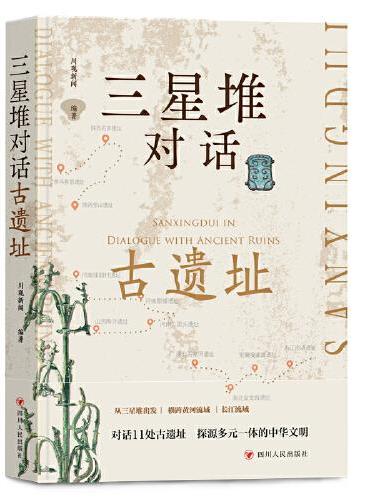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HK$
109.8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HK$
143.4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HK$
87.4
《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 售價:HK$
55.8
《
养育不好惹的小孩
》 售價:HK$
77.3
《
加加美高浩的手部绘画技法 II
》 售價:HK$
89.4
編輯推薦:
本书卖点
內容簡介:
在美国旧金山,年轻的桑宜成为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件的代理律师。和解是案子顺理成章的处理方式,但客户向寅却强势地坚持诉讼。就在桑宜试图了解向寅不肯和解的缘由时,向寅却解雇了桑宜。
關於作者:
微木,戊辰年生,江苏人。本科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后留学海外,先后于康奈尔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加州,从事诉讼法律业务。热爱文学,尤喜情感描摹、悬疑设计。《不落雪的第二乡》是她的出版作品,以诉讼律师所见奇事奇境为引子,以异乡人之困之惑为切入口,开启对人性曲折幽微的追索。
目錄
不落雪的第二乡·上部
內容試閱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