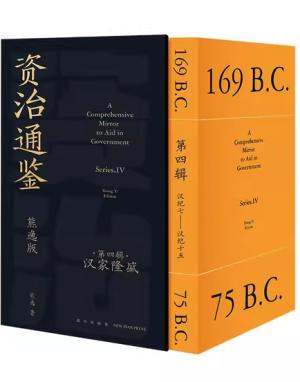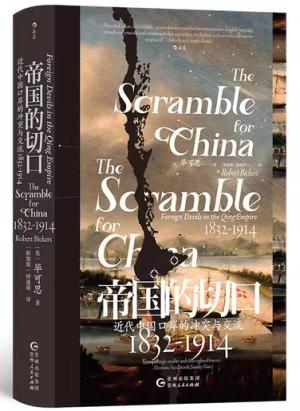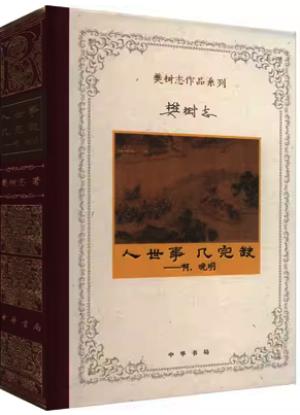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61.4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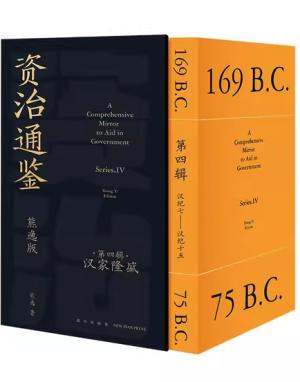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70.8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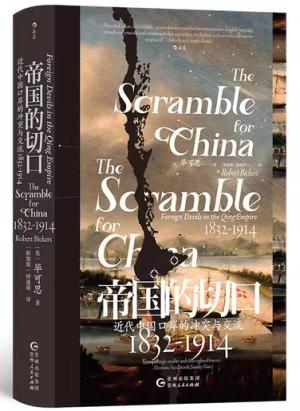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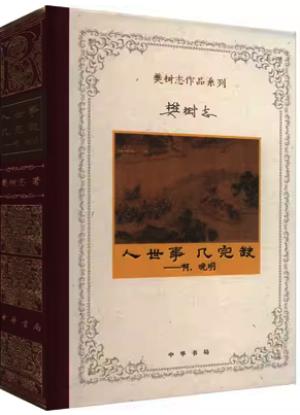
《
人世事,几完缺 —— 啊,晚明
》
售價:HK$
115.6
|
| 編輯推薦: |
★杰丝米妮·瓦德曾两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在该奖近百年历史上,仅有五人两度获奖,另外四人是威廉·福克纳、约翰·厄普代克、威廉·盖迪斯、菲利普·罗斯。
★怀着死亡的悲怆,怀乡的温情,生者的愧疚,作者以五位年轻亲友的接连离世和自己的成长经历,书写当代美国非裔族群的困境。在僵化的社会里,他们是没有出路的青年。
★在对往事的追思中,作者展现了在南北战争结束超过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种族主义如何通过经济和教育差异深度体制化,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黑人青年。
★入选《纽约时报》“50年来**的回忆录之一”。
|
| 內容簡介: |
|
四年时间,作者的五位亲友接连意外离世,他们的死看似毫无关联,却因身份和地点交织在一起。这些黑人青年生活在美国南方深处,代际贫困笼罩着他们的生命。在对往事的追思中,作者展现了在南北战争结束超过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种族主义如何通过经济和教育差异深度体制化,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黑人青年。怀乡的温情混杂生者的愧疚,作者最终回到故土,写下他们和自己的故事,让那些被冰冷的统计数字所遮蔽的鲜活面孔重新浮现。
|
| 關於作者: |
|
杰丝米妮·瓦德(Jesmyn Ward,1977— ),美国小说家。小说《拾骨》《唱吧!为安葬的魂灵》先后于2011年和2017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上仅有五人获此殊荣。2018年,瓦德入选《时代》周刊百大影响人物。 孙麟,大学讲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上海市外文学会会员。从事美国非裔文学与文化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多次前往美国、加拿大知名高校交流访学。
|
| 目錄:
|
序章
我们在沃尔夫镇
罗杰·埃里克·丹尼尔斯三世
我们出生了
德蒙·库克
我们受伤了
查尔斯·约瑟夫·马丁
我们在凝望
罗纳德·韦恩·利萨纳
我们在学会
乔舒亚·亚当·德都
我们在这里
致谢
|
| 內容試閱:
|
序章
每到周末,母亲便带上我们,从密西西比州沿海地带开去新奥尔良探望父亲,这时她总会说上一句“:把门锁好。”父亲在和母亲离婚前的最后一次分手后,搬去了新奥尔良,而我们仍住在密西西比州的迪莱尔。父亲在克雷森特城拥有的第一间房子是个一室户,面积不大,里面刷成了黄色,窗户上装了铁栅栏。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型的黑人街区什鲁斯伯里,这个街区一直延伸到堤道天桥的北面下方。房子的北边有个围着栅栏的工业场地,南边是条州际高架公路,路上汽车嗖嗖的飞驰声、砰通的落地声不绝于耳。我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既然是老大,我理所当然地支唤起弟弟乔舒亚、妹妹内里沙和沙兰,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表弟阿尔东;我让他们拿来父亲多余的床单和沙发垫,铺在客厅地板上,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休息了。父母当时睡在家中惟一的卧室里,他们曾试图和解,虽然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乔舒亚老是说房子里有鬼,晚上我们平躺在没有电视的客厅里,注视着铁栅栏的影子,偷偷地穿过墙壁,等待着它发生变化,等待着本不该在那儿的东西移动。
“有人死在这儿了。”乔希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他。
“爸爸跟我说的。”他回答道。
“你是想吓唬我们吧。”我嘴上这么对他说。喉咙里咽着句:这确实挺吓人的。
那差不多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正在上初中,上的是密西西比州一所圣公会私立学校,里面多是白人学生。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娃娃,我密西西比州的这些同学也都和我一样土里土气。我的同学称新奥尔良为“谋杀之都”。他们会讲些白人从车上拿下杂货时被枪杀的恐怖故事。这是团伙犯罪,他们会这么说,但只字未提那些残忍暴虐、丧尽天良的歹徒是黑人,我同学中有好几个都有种族主义倾向,却没说起这个,真让我感到吃惊。在学校里,每当我的同龄人谈起黑人,他们都会不时地朝我张望。我是靠奖学金维持学业的,能在这里上学完全是因为母亲给密西西比州沿岸一些有钱人家做帮佣,这些有钱人资助了我的学业。在我的中学时光中,大多数时候,我是学校里惟一的黑人女孩。每当我的同学说起黑人或新奥尔良时,他们尽量不去看我,但免不了还是看了我;这个时候,我会朝他们瞪过去,同时想起我所认识的新奥尔良人—父亲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
在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之中,我们最喜欢布基叔叔。他和他的兄弟们一生都住在我同学觉得最毛骨悚然的街区。布基叔叔长得最像爷爷,不过我对爷爷没什么印象了,因为他五十岁的时候就突发中风去世了。布基叔叔的胸脯像个圆筒,笑的时候会合上双眼。天热的时候,他会领着我们穿过什鲁斯伯里,朝空中的高速公路方向走去,最后来到角落里一座摇摇欲坠的盒式住房1 边,我记得那房子是栗色的。住在这里的女士从里屋拿出冰棍儿来卖。冰棍儿是糖液做的,热气中化得很快。叔叔仿佛是街区的花衣魔笛手,在去女士院子的路上给我们讲笑话,召集更多的孩子过来,领着我们走过融化的沥青路面。一旦我们的冰棍儿在他们的纸板杯里化成了糖浆,一旦我和乔舒亚舔去手上和胳膊上的糖水,布基叔叔就在街上和我们玩起游戏:用棒球规则来踢足球,玩橄榄球,打篮球。有时,橄榄球打到我们中某个人的嘴上,疼得我们嗷嗷直叫,嘴巴肿了起来,他却哈哈大笑,眼睛眯得像薄薄的便士。有时,他和父亲一起带着我们还有父亲的斗牛犬去高速公路下的公园。就在那儿,父亲让他的斗牛犬参加斗狗。高温下,看斗狗的或是诱导狗发狠的那些人同他们的动物一样浑身发黑、大汗淋漓。我和弟弟一直紧紧地挨着叔叔。汽车在头顶呼啸而过,动物们撕扯着对方,我们紧紧地抓住叔叔的前臂,往后退缩。接下来,交战的狗流着血,喘着气,一笑了之。于是,我们松开了紧握着叔叔的手,愉快地离开了这个阴影笼罩的世界,也避免了斗狗场外被狗扑上身来的危险。
“爸爸肯定没告诉过你们,有人死在这里了。”
“谁说哒?他说过。”乔舒亚说。
“可不是嘛。”阿尔东附和道。
上高中的时候,我无法将这些对新奥尔良的无稽之谈与现实情况对应起来,但我知道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真相。九十年代初去探望父亲的时候,父母虽然分居但仍处于婚姻状态,多年的相处让两人当时的关系仍十分融洽。他们坐在车前排座位上,谈论着枪杀、殴打和谋杀事件。他们用许多词语来描述新奥尔良的暴力。不过,我们在探望父亲时却一次也没见过。我们的耳边传来父亲房子旁的工业场地边的铁丝围栏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此刻,黑夜在无尽地延伸,我们听着弟弟讲鬼故事。
我们还知道另一个新奥尔良。我们挤进母亲的车中,车驶过散落在新奥尔良大街小巷的红砖房屋。这些房子是双层,有一个铁栅栏围起的下陷阳台,房子两旁的参天古树如驻守的哨兵,女人们在一旁指指点点、冥思苦想,黑皮肤的小孩在破损的人行道上玩耍,他们时而生气,时而高兴,时而又露出不快的神色。我注视着窗外的年轻男子,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头靠在一起窃窃私语,弯腰进了街角的店铺,这里出售夹着虾和牡蛎馅的波布瓦三明治1。不知道这些人在嘀咕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杀过人。晚上,我躺在父亲客厅的地板上,又问了乔舒亚。
“爸爸说这里怎么了?”
“他说有人给打死了。”乔舒亚回答。
“谁?”
“一个男的。”乔舒亚面朝天花板说。
沙兰缩到我旁边。“都给我闭嘴。”内里沙叫道。阿尔东叹了口气。
每周日我们从父亲这里回到迪莱尔时,我都感到非常沮丧。我觉得大家都不开心,就连母亲也是如此,虽然路途遥远,父亲多年来有出轨行为,她还是尽力挽回婚姻。母亲甚至考虑搬去她讨厌的地方—新奥尔良。我很想念父亲。我不想周一早上回到密西西比的学校上学,不想走过一个又一个玻璃门,最后来到开着荧光灯的大教室里和旧课桌前。
我的同学坐在课桌后,穿着有领衬衣和卡其短裤,摊开双腿,涂着蓝色的眼线。我不希望他们说完黑人的事儿之后就看我,也不想避开自己的眼睛。不然,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在打量他们,审视他们享有的特权,仿佛这是他们穿着的另一件衣服。回家的路上,我们驶过新奥尔良东部,穿过索维奇岛海湾,越过庞恰特雷恩湖浅吟低唱的灰色湖面,穿过斯莱德尔的广告牌群和公路边的带状商业区,最后进入密西西比地区。之后,我们驶入10 号州际公路,穿过斯滕尼斯航天中心的松树林,驶过圣路易湾和戴蒙德角,回到迪莱尔。一到那儿,我们就驶出了那条漫长的、坑坑洼洼的高速公路,开过被遮蔽的杜邦公司,它犹如松林墙后的斯滕尼斯,驶过火车铁轨,经过小块的田野和小型的沙地院子里一个个小木屋,浓荫覆盖着这些屋子的门廊。这儿,马静静地站在田野里,吃着草,乘着凉。山羊正啃着篱笆桩。
我们全家都从迪莱尔和帕斯克里斯琴小镇来,这两个镇均不属于新奥尔良。帕斯克里斯琴栖息在长滩边墨西哥湾的人造海滩旁,背靠圣路易湾,而迪莱尔紧挨着圣路易湾的背面,向四周蔓延开去,在内陆地区逐渐变得稀疏。炎热难耐的夏季里,大多数时候,两座小镇的街道都在昏昏欲睡,而在温度大部分时候徘徊在冰点的冬季也是如此。迪莱尔的夏季里,有时人群会在周日涌入县立公园,年轻人从车里出来打篮球、用车放音乐。春季时分,年长的人聚集在当地的棒球场,南方的黑人棒球联盟会来这里比赛。万圣节上,孩 子们走过街区或是坐在开过街区的皮卡车后,挨家挨户地玩 “给糖还是捣蛋”的游戏。诸圣日中,家家户户擦拭墓碑,清扫满是沙子的坟地,放上一盆又一盆的菊花,与逝者分享 食物。接下来,他们围在心爱之人的坟茔四周,拿出尼龙帆 布折叠椅,在一旁坐下,然后一直聊到晚上,点火赶走最后一拨秋季的蚊虫。这并非所谓的谋杀之都。
迪莱尔的大多数黑人,包括我家人在内,打从他们记事起就住在这里,很多家庭住的地方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些小型的盒式和A 字形房子是一批批建成的,最老的房子是我们曾祖父母辈在三十年代建的,后一批是我们祖父母辈在五十年代造的,最后一批是我们的父母在七八十年代雇用承包商修的。这些简朴的住宅,包括我们家在内,有两到三个卧室,房子后面是碎石泥车道、兔子笼和白葡萄园。住在这里的都是些穷苦但有自尊的工人阶层。迪莱尔没有公共住房,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前,帕斯克里斯琴的廉租房就是几栋小型的套楼公寓以及一些独户的住宅区,里面住着一些黑人和越南人。现在,也就是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的第七年,开发商在十五到二十英尺的桩子上造了些双卧室和三卧室的新房,公共住房就这么建起来了。住宅区里很快便住满了因暴风雨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或是从帕斯克里斯琴和迪莱尔来的、希望住在家乡的年轻人。但是有几年,卡特里娜飓风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因为它夷平了帕斯克里斯琴的大部分住宅,也毁了最靠近迪莱尔海湾的地方。也因为这个,成年人回迪莱尔变得更为艰难了。除此之外,还有难言之隐。
正如乔舒亚在我们孩提时代捉鬼时所说:有人死在这儿了。
从2000年到2004年,与我一起长大的五位黑人男性青年纷纷故去,而且都死得很惨,他们的死看上去毫无关联。首先是我弟弟乔舒亚,他死于2000 年10 月。接下来,2002年12 月, 罗纳德也没了。再接着,2004 年1 月,C. J. 去世。紧接着,2004 年2 月,德蒙亡故。最后是罗杰,他在 2004 年6 月也离开了我们。这份接二连三的死亡名单直观地揭示了残酷的现实,它让人无语。它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缄默。如果说对此发声是件难事,那只是轻描淡写;把这些说出来才是我迄今办成的难度最大的一件事。我笔下的鬼都曾是人,这一点我忘不了。我走在迪莱尔的大街上时,会觉得卡特里娜飓风后街上的人少了,这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人。自从他们纷纷离去,街道显得更加空荡荡。再也听不到弟弟和朋友们停在县立公园的车里放的音乐,唯一回荡在耳边的是我一个表亲养的鹦鹉发出的受虐的叫声。装鹦鹉的笼子非常小,鹦鹉的冠子差点碰到笼子顶部,它的尾巴擦着笼子底。鹦鹉大声尖叫,叫声传遍整个街区,仿佛是受伤的孩子发出的喊叫。有时,在那只鹦鹉厉声喊出它的愤怒和忧伤时,我对街区的平静大为惊讶。不知道为何寂静无声反而成了我们克制的愤怒之音和积聚的悲伤之声。我觉得这有问题,而我应该为这个故事发声。
跟你说了,这里有鬼,乔舒亚说。
这是我的故事,也是那些过世的年轻人的故事,这是我们家族的故事,也是我所在社区的故事,所以讲起来没那么容易。开头,我得说说我们小镇的故事和我所在街区的历史。然后,我会回顾一下那五位早逝的黑人男青年的情况:根据他们去世的时间,由近及远往回追溯,从罗杰到德蒙,然后到C. J.,再到罗纳德,最后到我弟弟。与此同时,我还得根据时间的发展往前推进叙述,所以在讲述我朋友和我弟弟生活、说话、身亡的几个章节之间,我会穿插介绍我的家族和我的成长历程。我希望,在我触及问题的要害之时,在我从过去来到现在和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思绪行程同我弟弟的死交汇之时,我能通过了解我们的生活以及我所在社区人们的生活,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死亡传染病发生的原因,更明确地认识到这里的种族主义、经济不平等、衰落的公共和个体责任是如何恶化,如何继续变糟,最后散布开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找到弟弟的死因,弄清楚自己为何会被这该死的破故事所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