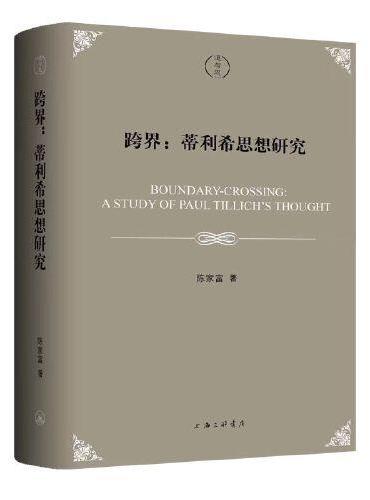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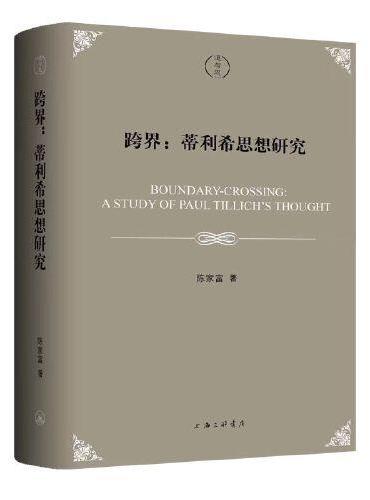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4.7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2.0

《
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
》
售價:HK$
201.6

《
养育男孩: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
小原流花道技法教程
》
售價:HK$
109.8

《
少女映像室 唯美人像摄影从入门到实战
》
售價:HK$
110.9

《
詹姆斯·伍德系列: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美国图书评论奖”入围作品 当代重要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文学中的笑与喜剧”的精湛研究)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潮流之外的中国著名女作家蒋韵
《我的内陆》荣登台湾尔雅书店畅销书榜
时代伤痕之于纯真少女;
历史名城之于市井小民。
她们这些平凡的少女,俗世中的少女,大时代中的少女。
是她们,使革命时代的街头有了卑微、坚韧、热情、永不会被灭绝的人间气息。
|
| 內容簡介: |
“月光之爱”选粹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系列,爱情是人类最美好、最神圣的情感,是文学最有魅力的叙述。在当代社会,爱情越来越不被人们珍惜,但唯有文学始终与爱情相伴。爱情在现实中被稀释,但它仍然是文学中最生动的一股清泉。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女性作家对爱情的书写,她们是爱情最真诚的守护人。
该书为“月光之爱”书系之一,是蒋韵著名代表作,曾获得台湾尔雅书城畅销书称号。
1966年,作者12岁,目睹了一场社会性的革命掀起万丈波澜。于是我们知道了T城有叫林萍、程美、老蒙娜、冀晓兰、陈枝等等,——纯洁无邪,命运神奇而跌宕的少女的存在。
无论社会怎样喧嚷、凌乱、颠覆,爱情依然是小城故事永恒的主题。这座北方著名的历史名城里,在主人公短暂同时也是漫长的少女成长史中,出现了他们:用生命捍卫尊严的白娘子,十二岁就去越南参战的少女林萍,“马路天使”一点红和早熟的少女鱼,失去家园的陆涛、吴光和老蒙娜,被逐出去的城市女儿冀晓兰??????。现代城市中苦涩的爱情;太原城的解放,一座城市的新生……
阅读的过程就是疼痛的过程。一次次阵痛,是荒诞年代对人精神的放逐,也是对生命个体、生命形态的抑制和限定。
|
| 關於作者: |
|
蒋韵,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以及小说集《现场逃逸》、《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等。曾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大红鹰优秀作品奖等一些文学奖项,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作品《心爱的树》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太原市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
|
| 目錄:
|
目录
引言……1
第一章 胜利逃亡……1
第二章 马路天使……37
第三章 驿站……73
第四章 伤心街巷……102 第五章 “花园”里的情和爱……144
第六章 沉默与辉煌……177
第七章 艳歌……201
后记 在哪里和你相遇……223
|
| 內容試閱:
|
1966年,从夏天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管束自由自在的野孩子。生活全改变了,好像是世界的末日,又好像是古往今来最盛大的狂欢节,这要看你属于什么颜色,红色还是黑色。
我家是黑色的,我想忘记这事实,于是我就逃到了街头。我对自己说,就当你是个孤儿好了。这样一来家里发生的那些倒霉的事情好像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到处游逛,看着热闹,有一天,我看见我同学的父亲戴着一只高高的痰盂游街,那样子真滑稽可笑。我觉得挺解气,因为那男同学平时总是欺负我,还用弹弓打破过我的头。我兴冲冲跟着人群,跑前跑后,快活得不得了。可是渐渐地我放慢了脚步,停下来。我眼前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倒霉同样屈辱的形象,那是父亲。泪水一下子涌上来,我想,要是我真是个孤儿该多好啊。
有一次路过一条小街,看见院子里在开批斗会。桌子上面摞桌子,叠罗汉似的,上面颤颤巍巍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三寸金莲似的小脚踩在摇摇欲坠的桌子筑成的宝塔尖上,浑身哆嗦。我一下子掉转了头,心里一阵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站在那宝塔尖上的是我的祖母。就是那一天,我下决心要离开我们这城市,我东撞西撞,来到了铁道旁。我像电影上演的那样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后来我走累了,太阳也要下山了,眼前的铁轨,像明亮辉煌的金蛇一样无声游动,我忽然害怕了。我想你有扒火车讨饭偷东西骗人做小流浪儿的勇气吗?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身旁驰过,煤烟迷了我的眼,还有什么东西“嗖”地打在我脸上,是从窗口飞出的一截苹果皮。清凉而湿润的苹果皮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和平的日子。列车驰过去了,看不见了。我掉转头,朝来的方向,朝我们城市的方向,朝我深深痛恨的地方,走去。那是我的家,我的城,我的厄运,我逃不掉。
现在想起来,那也许是我真正走进这城市的一个机会,走进它深藏不露的身体和内心。但是我错过了,我在危难的时刻和一个城市失之交臂。
我一向认识的城市,光明、单纯、来历清楚,具有“新世界”的意味,是时代的产儿。听听那些名字:五一广场、人民电影院、红旗剧场、解放大楼、青年路,这就是我生活的边界也是我辨认这座城市的坐标和灯塔。这样一些名字,切断了一个孩子通往城市深处的道路。也有一些中性的地名,比如,大南门、并州路,还有,上马街,其中有了时间的味道和可疑的气息,但是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宣传画中的孩子,还远远没有到达感受时间之美的年龄和年代。
还有想当然的误解,比如,我们城市最著名的那条大街--迎泽街,还有因为坐落在这著名的街上而被命名的迎泽宾馆、迎泽公园,一直被我想当然地理解成--迎接毛泽东的意思,或者是迎接他的恩泽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它是因为古城门迎泽门而得名。)这太简单了。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迎泽大街、迎泽宾馆、还有迎泽公园,这都是新中国的产物和成就,是新中国带给我们人民的恩情。在旧社会,到哪里去找这样宽阔的、光明耀眼的、在节日供鲜花和彩车通过的、简直可与骄傲的长安大街媲美的大街?而迎泽公园,当年不过是一个烂泥塘和一片荒凉的野坟场,我们年轻的父母当年都参与了把它改造成一个公园的义务劳动。他们唱着歌颂新中国的歌儿,快乐地抛洒汗水,把掘出来的一根根无名无姓的白骨意气风发嘎吧嘎吧踩在脚底。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迎泽宾馆。它由两座建筑物组成,它们分别被称为东楼和西楼。西楼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八角楼,以形状得名。东西两楼相互依恃,如亲人般你呼我应。在我小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楼,也就是八角楼只是一个废墟样的建筑工地。钢筋和混凝土浇铸出的地基高出地面不过一两米。无论从近处还是远处,完全看不出它未来辉煌的形状。有许多年,它荒芜着,沉寂着,以一个丑陋的不负责任的废墟形象伴随着我们这些孩子一天天长大成人。它使我们完美的迎泽大街有了某种残缺。大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苏修背信弃义的结果。
原来这八角楼是苏联专家帮我们设计帮我们施工的。可刚刚打下地基,中苏关系就彻底破裂了。苏联专家在某一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图纸悄然而去,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啃不动的“半截子工程”。它荒废在那里,风吹雨淋,渐渐被荒草掩盖,做了蟋蟀和老鼠的家园。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期,在中苏最为交恶的时刻,我们的城市拉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有一天,我十五岁的女儿问我什么叫大会战?这真使我有沧海桑田之感。)若干天之后,我们的八角楼终于拔地而起。那时,它是我们城市最高层的建筑,它也一度代表了我们这个城市新建筑的顶峰。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迎泽大街。它横贯了我们整个城市,连接了东西两山,(感觉上是这样。)在我童年时,站在我们的五一广场上,东山和西山是那样清晰,看上去离我们很近,它使我产生错觉,以为我随时可以去那里玩上一圈。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回到那样的时光之中:天很蓝,白云很柔软。没有那些碍眼的丑陋的高层建筑阻挡我们眺望的视线。这是唯一、唯一温情的时刻,让我硬不起心肠说这个城市的坏话。
在一个光明单纯的新世界里,偶尔会有一两个名字凸现出来,像界碑一样指向陈旧和斑驳的岁月流年。“柳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关于柳巷的传说,我还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那是一个温暖的传说。说的是元朝末年,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他派大将常遇春来我们太原打探军情,不想被元兵发现。元兵将常遇春追赶到一条巷子里,走投无路时,一个老大娘掩护了他,老大娘把他藏到了自家院子里柴房一类的地方,然后装聋作哑地打发走了追兵。常遇春得救了。大恩不言谢,他对大娘说,某月某日,让大娘在自家大门前插一根柳条为记。那个“某月某日”,就是朱元璋计划攻破我们城市的日子。大娘是个善良的老人,到了那一天,她让整整一条巷子里的人,人人在自家门前都插了柳条。明军破了城,烧杀抢掠,常遇春有令,凡门前有柳条者一律不许兵士骚扰。这就是常遇春报答老人救命之恩的方式,报答我们城市的方式。于是,那整整一条巷子,被门前纤弱的柳条庇护了下来,那一根根柳条,沐风栉雨,一天天,一年年,抽条长叶,长成了翠绿而漂亮的柳树,从此,那条巷子就被更名为“柳巷”。
在我少年时,柳巷已经没有多少棵柳树了,也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关于柳巷的来历,那个传说被新世界弄丢了。尽管如此,这个柳巷,它仍然有着某种可疑的的气味,它的繁华热闹、它的五光十色,似乎都是陈旧和沉厚的。听听那些商店的名字:
老香村:这是卖南北糕点和糖果的地方,卖南方风味的“南糖”、桂花牛皮糖和干桂元,也卖店里自制的“萨其玛”和著名的“闻喜煮饼”。“闻喜煮饼”是一种晋南的点心,用油和蜂蜜和面,白糖做馅,极甜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它。
六味斋:这是卖酱肉的地方。酱猪肝、猪心、肘花、大肚、小肚,还有包着薄薄一层蛋皮的鸡蛋卷。这里的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闻名遐迩。这八个字一直闪烁在它的牌匾上和橱窗里,也同样在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
华泰厚:这是做衣服的地方。里面堆着各种毛料、绸缎,有着樟脑的气味和阴暗的感觉。这不是我们爱去的地方,我们的母亲爱在那里出没。有时,她们穿上一条新裤子,哔叽的料子,笔管条直,那就是华泰厚的旗帜。她们是那么得意地等着人家来询问,哪儿做的?她们好嘹亮地回答:华泰厚!但是华泰厚和一个孩子的生活永远不沾边。
还有“老鼠窟窿”,是卖元宵的甜食店。这里的元宵,皮糯馅大,馅是桂花玫瑰什锦馅。除了元宵,这里还卖麻团和凉糕。其实,在属于我们的年代,这里的元宵好吃与否并不具备比较的意义,它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很多年里,它几乎是我们这个城市唯一一家卖元宵和江米甜食的地方。花二角钱吃一碗(八个)桂花元宵,汤随便添,那是我们身心俱陶醉的节日。
除此而外,还有:开明照相馆、开化寺商场、认一力饺子馆、一间楼、林香斋饭店……等等、等等。
只不过,1966年酷热的夏天,这些百年老店黑底金字的招牌,全都被革命扫荡一空,一夜之间,新桃换旧符。老香村变成了“立新食品店”、六味斋变成了“工农兵酱肉店”,还有一大串为民、利群、红卫……这样一些名字终于使一个可疑的老柳巷旧貌换新颜,也及时阻止了一个茫然徘徊的孩子在歧路上迷失。
也有幸存下来的名字,比如,长风剧场。这本来就是一个嵌在老柳巷中的新建筑。现在它安然无恙,庇护着我,给我安全感和有关和平生活的记忆。躲在它黑暗的肚子里是我为自己找到的最安全的场所。只要花五分钱,我就可疑走进昔日的生活,盘桓在那里,忘记外面那个正在翻天复地的世界。
电影院奇迹般开放着,演一些还未被宣判为毒草的电影。要不了多久,真正荒芜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很快将要沦入没有电影可看的沉寂岁月。预示这一时刻到来的丧钟就要敲响,此刻人心惶惶,里面几乎没什么观众,而放映的片子也杂乱无章,末世的气味在空旷的电影院里象雨云一样聚积。只有银幕闪闪发亮,它引诱着一个惶恐的企图从现实出逃的孩子象引诱着扑火的飞蛾。
忘记看了些什么电影。
只记住了一个。因为这电影有些奇怪。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中它似乎是一条漏网的鱼,一只从枪口下逃出的狐狸,它美丽的金红的大尾巴在白雪茫茫的荒原中一闪而逝。它还像一个从家乡逃跑的地主,躲避着土改和清算。总之它给我逃亡的印象。其实,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它的名字叫《斯维尔德洛夫》。
后来,在《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两部电影中我们将要认识的那个戴夹鼻眼镜、留黑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是这部影片的主角。这是一部革命的电影,可不知为什么留给我的是感伤的回忆。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在舞台上装扮成魔鬼的形象,用他俄罗斯辽阔又荒凉的歌喉唱道:
众人死在刀剑下,魔鬼一旁正欢笑,
众人死在刀剑下,魔鬼一旁正欢笑……
那歌声让人悲伤和流泪。
还有一个游乐场的镜头,一个杂耍班子的小丑叫着,“欢乐吧,欢乐吧,这是一个欢乐的年代!”这叫声也充满悲伤和灭亡的伤痛。
我不知道在革命的庙堂的历史和在俄罗斯人民的民间的历史中,斯维尔德洛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可我对他充满好感。我觉得他是一个深情的忧郁的革命者,还有些像诗人。他就这样温柔和朦胧地活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最后融入原野般苍茫温暖的背景。
看完《斯维尔德洛夫》的当天,我回到家里,听说了一件事。我家的一位朋友,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叔叔,他妻子在这个早晨服毒自杀了。她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她不愿揭发她的一位好友,但是人们威胁她,二十四小时之内如若她拒不揭发,革命群众就要对她采取行动。他们让她欣赏糊好的白帽子,足有一米多高,在1966年夏秋两季,这样的帽子扑天盖地,遍及每一个城市和街头。但是叔叔的妻子以死亡的方式断然拒绝了它。这是我知道的一个从羞辱中成功逃亡的例子。
叔叔的妻子,在人们的嘴里,是一个资产阶级娇小姐,来自北京,学医。在夏天总是穿漂亮的布拉吉,手指颀长,从她白如凝脂的颀长的手指上暴露出她血统的秘密。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用生命捍卫尊严的人。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她的亲人、朋友,大家都说她太脆弱。
也有不成功的逃跑。
比如,白娘子。她是我同学小五的母亲,也是我家的邻居。她并不姓白,可一院子的人无论老少背地里都这么叫她。白娘子,白娘子!抑扬顿挫。我知道白娘子是一条白蛇,可她和一条蛇有什么关系呢?我倒觉得她更像一只鸟,有着非同寻常的华丽的羽毛。她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却衣着讲究。她的丈夫赵佩璜是个名医,在遥远的年代里她有各式旗袍:棉的、绸的、软缎的、羽纱的和华贵的裘皮大衣,它们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她的日常生活。我六、七岁的时候还看到她穿湖蓝色的纱旗袍手摇檀香扇在树下乘凉的样子。可后来它们似乎消失了。它们的主人和所有的时代妇女一样,换上了朴素的制服。
但是1966年到来了。这些美丽的彩虹般的衣服终于在某一天重见天日,它们缭乱地堆在院子里,在阳光中散发出樟脑、楠木箱和死亡的动物毛皮的浓郁气味,供人们参观、批判、咀咒、或暗中欣赏。衣服的主人则满身血污和墨渍,跪在八月的骄阳和飞扬的尘土中向人民请罪。
一天早晨,我站在院子里刷牙。我正朝脚下粗壮的葵花杆上响亮地吐着漱口水,忽然觉得有人叫我。我回过头,看见了白娘子。她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她并没有叫我,她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那么是谁叫我呢?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困扰着我。我看她从我身边走过,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在这个早晨,她穿一件灰上衣,蓝布裤,这使她的背影看上去非常寒伧和平凡。
这个早晨,向日葵开始耷拉脑袋,它们结籽了,做了母亲。一些枯萎的黄花瓣像产妇的头发一样慢慢脱落,落在地上、阴沟里。这就是白娘子在最后的早晨看到的人间美景。
她就是在这天出了事。黄昏时我听到了这凶信。她跳湖自杀了,跳了公园的人工湖,就是我们的父母们多年前唱着歌儿亲手挖掘出来的湖泊。那湖有个动听的名字--迎泽湖。人们说白娘子的尸首已经打捞上来,泡得不成样子。人们用手比划着,说,头肿了有这么大。
不过人们并不怎么震惊。
我也不。
我照样吃我的晚饭,呼噜呼噜喝粥。喝着喝着,不知怎么就咽不下去了。我想,原来早上那一见,是我和白娘子阿姨此生最后的一面啊!
水淋淋的白娘子阿姨,躺在与我们院子仅一墙之隔的医院的太平间,那儿杂草丛生,青苔满地,是我所知道的最简陋荒凉肮脏的一个太平间。我等着哭声。以往,从那里传出的猝不及防的哭声常常惊扰我们的黑夜和黎明。可是没有,这一夜,风平浪静,没有人哭她。她有五个儿女,一个赛一个漂亮、帅气,包括我的同学小五。但是他们不哭她。
他们静悄悄地为她办了丧事。
后来听说那天她在湖边转悠了很久。她从藏经楼那里穿过桃杏林和长廊来到前湖,然后她走过石桥,又走过九曲木桥,在水榭那里坐了很久。一个卖爆米花的老太太最后看她朝后湖走去,后湖比较偏僻,几乎没有游人。
满湖飘着蝴蝶般金黄的落叶。
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她的尸体。漂了上来。肚子涨成了一面鼓,撑开了裤子,赤裸的肚皮在阳光下亮晶晶闪烁。这很奇怪,她本来希望自己消失和没有,可看上去她竟远比平时庞大,庞大和丑陋。卖爆米花的老太太最先看见了她,不由地放声尖叫。
后来听说给她穿衣服费了很多事。
先是给她换了一件蓝制服上衣,特别肥大的一件,是她丈夫赵先生的,可是仍然扣不住扣子,也就算了,到哪儿去找现成的衣服呢?但是她最小的女儿,十二岁的小五不答应,小五说,
“妈说走的时候要穿那件丝棉袄!”
她的话让人吓一大跳。
“什么?”
“妈说,走的时候穿那件丝棉袄。”
“哪件?”
“黑缎子的,在柜顶上的箱子里。”
小五搬来凳子,踩上去,开皮箱。她踮起脚尖儿,还是够不着箱盖。她大姐一把把她推下去,自己上去打开箱子,手一摸,触摸到了柔软的、冰凉的、水一样滑动的织物--原来它就在最上面。
她大姐站在凳子上哗地抖开了它。
绝美的、绝望的那种黑,上面洒满大朵大朵金色的牡丹,还有魂魄似的大蝴蝶,东一只、西一只,飞舞着,盘旋在花丛中,落在花瓣上,美艳惊人。还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安详之气和光明,不可触碰,遥不可及,好像那是天国的某个角落。
五个儿女都呆住了。
这光明的景象刺痛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涌出眼泪。
可是它太瘦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变形的庞大的身体塞进这瑰丽的牡丹园中去。没有奇迹,他们不知道拿这天国的花园怎么办。他们人人一身大汗,最后他们放弃了。大姐说,
“算了吧,还穿那件蓝制服吧。”
结果,这个女人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仍然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个她奋不顾身撇下亲人要逃离的,——冰冷残忍和恐惧的时代。她穿着这个时代的制服,也没有带别的换洗衣服。那个世界的人一眼就可从这扣不住扣子的男人的制服上辨认出她的来历。活着的人还有可能走出一个时代,而她却成为这个时代的永恒。
这没有被抄走的、奇迹般保存下来的黑绸缎丝棉袄从此成为赵家的一个谜和一块心病。小五的大姐在一些回忆的夜晚轻轻抚摸这光滑如水的漂亮的织物,心里想,小五怎么知道妈要穿这件棉袄?只不过,她从没把这句话问出口,小五也不说。
在街上有一天我碰到了林萍。对了她和那个歌星林萍同名。但我认识的这个林萍不会唱歌。她声音很沙哑,脸盘像向日葵一样又大又扁,可她的身体和四肢却出人意料地纤细柔软,像春天的植物一样饱含绿色新鲜的汁液,芳香四溢。她是我在少年宫艺术团认识的伙伴。我是合唱团一名最普通的团员,而她则是舞蹈队的主力。
我们的艺术团,有个十分俄罗斯化的名字:小红星艺术团。这让我想起苏联红军、克里姆林宫、还有女英雄古里娅。在那本叫做《古里娅的道路》的书中,幼小的古里娅每天晚上都要望着克里姆林宫宫顶上的红星才能入睡。
每逢节日,六一、十一、还有新年,就是我们演出的日子。或是来了什么贵宾。比如来自非洲或北京的什么客人。记得来过刚果朋友,忘了是刚果(金)还是刚果(布),是一些游击队员,在礼堂里为我们做了关于游击队和丛林的报告。报告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只听懂了三个字:毛泽东,于是全场欢声雷动。以为他是用汉语说了这个伟大的名字。还有电影演员于蓝,于蓝的到来使我们激动万分,一个电影演员,这简直是来自梦境的荣耀的使者啊!身披霞光、前额上缀着星星、一步一朵鲜花、不食人间烟火。何况这位演员还是江姐的扮演者,于是这激动就变成了双重的激动:梦境和革命理想的结合。
这样的日子,就是林萍闪耀的日子。
在开场的大合唱之后,我就变成了台下的观众。我坐在芸芸众生之中遥望林萍,她扁平的脸在梦境般的灯光下饱满起来,就像一朵花,在时光中静静地吸吮和孕育,然后在某一个早晨迎风怒放,花心里闪烁着最新鲜的朝露。她使我目乱神迷,我想,这个迷人的女孩儿是谁啊?这个女孩儿,她一会儿是手持红樱枪的儿童团员,一会儿是幸福的公社向阳花,再一会儿,她又变成了遥远的西贡街头卖花的穷孩子,她的生命是多么缤纷灿烂和丰富啊
|
|